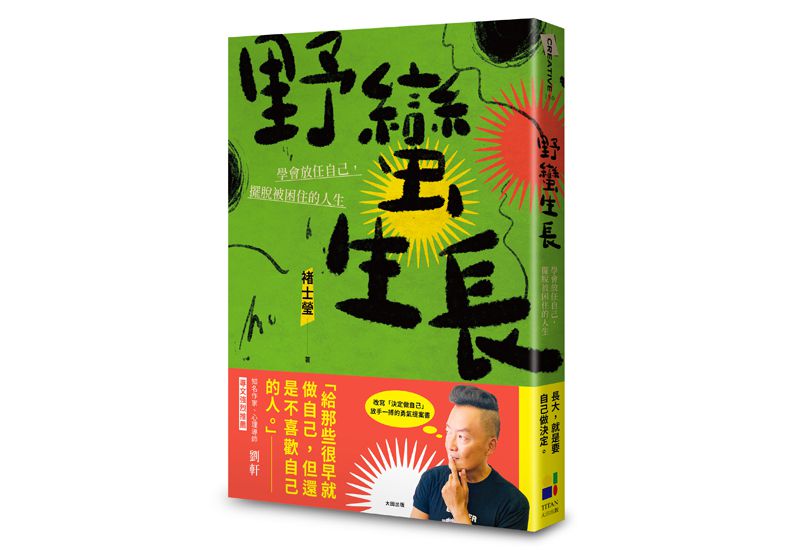對於忠於自我,許多人最大的迷思,就是以為必須「原創」才是自我。 那麼我問你,你喜歡上KTV唱歌嗎?你怎麼決定自己一首歌唱得好或是不好? 是唱不同的歌,聽起來都像原唱人,唯妙唯肖幾乎沒有分別?還是不管唱誰的歌,都要唱成自己的風格?
如果你有了答案,那麼我再問你:你看選秀歌唱節目嗎?你怎麼決定一個歌手一首歌唱得好或是不好?
你使用的是同樣的標準,還是你發現自己有著雙重標準?
有些人會說,他無法從兩個標準之間選擇,因為好不好聽是一種「沒法說出的感覺」。「感覺」表面上是很個人化的,每個人都有,但如果你是一個選秀節目台下的評審老師,你能夠用「沒法說出的感覺」來作為評判的標準嗎?一定不行吧!
這時就會發現,我們當然會對一個人唱歌唱得好不好,進行「質性的評量」,而質性的評量當然是有標準的:比如聲音的大小、條理、口齒清晰、台風是否大方。
同樣的標準,不只可以用來評判上台唱歌,也可以用來評判到台上做口頭報告的學生,而這些「聲音的大小、條理、口齒清晰、台風是否大方」的標準,實際上就是一種「模仿」,而不是「原創」。
當我們在學習任何一門技術時,引領我們的師傅、教練或是老師(mentor),往往會叮囑我們「先求像,才求特色」,或是「先求有、再求好」,因為特色是加分,模仿才是基礎。
因此要找到自己的聲音,就要從認真模仿開始。

很多人一聽到「模仿」兩個字,就充滿了不屑。但是在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你真的能夠原創任何一個從來沒有人有過的念頭,做出一件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嗎?
就算真的有,任何的原創都是好的、有價值的嗎?只是為了原創,發明了一個從來沒有人做過的殺人手法,真的有價值嗎?
「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獨創性,這就是我最自豪的地方。」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叫赤木明登的日本當代漆藝家,被德國國立美術館列為「日本現代漆器十二人」之一。他對於自己的驚人之語,提出這樣的解釋:
大部分人都很看重自己作品的獨創性,然而我對此毫無興趣。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仿製品」……從同一個形狀裡,選取最美的一根線條,就是我的「仿製」。
比如很多人喜歡上蔣勳的課,他的聲音說出的,是他自己的內容,還是別人的內容?
蔣勳說的素材是早已經存在的美術史、佛經,但是他選擇「別人的內容」,用「詮釋」來「再創造」,正是選取美學中最美的那一根線條。所以,我們會說蔣勳主要是「模仿」別人的聲音,還是「原創」自己的聲音?
另外有趣的是,如果你聽過年輕時的蔣勳,跟現在的蔣勳,不考慮年齡因素的話,他的聲音難道沒有改變嗎?蔣勳有沒有經過模仿,才變成今天的聲音?
即使說的內容不變,初衷不變,但是蔣勳的聲音,隨著時間變得更「歷練」,這個歷練來自於自己的生命經驗。
一個沒有生活歷練的人,是沒有自己的聲音的。因此我會說,一個有歷練的聲音,不是模仿,而是原創。
關於自己的聲音,奧修在《叛逆者》(The Rebel)裡面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
小孩的〔聲音〕是很強的,但隨著成長的過程他慢慢地變弱了,而父母、老師、社會……的聲音卻愈來愈大聲。現在,如果要找回自己的聲音,你必須穿越這夥人的雜音。
直接往內看:這是誰的聲音?有時是你爸爸的聲音,有時是媽媽、爺爺或老師的聲音,這些聲音都不一樣。不過就有一種聲音你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自己的聲音。它一直以來總是被蓋在底下。人們總告訴你說:聽年長者的話,聽牧師、老師的話。從來沒有人告訴你:聽自己的話。
「你自己的聲音是如此沉默微弱,而這群人的聲音卻蒙蓋在你之上,幾乎不可能找到你自己的聲音。首先,你必須先擺脫所有的雜音,回到寧靜,和平、沉靜與清澈的品質。唯有如此它才會出現,而且你會很驚訝你竟然也有自己的聲音。它像是潛流般,一直藏在那裡。」
找到自己的聲音以後,「變成自己」的生命拼圖,基本上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