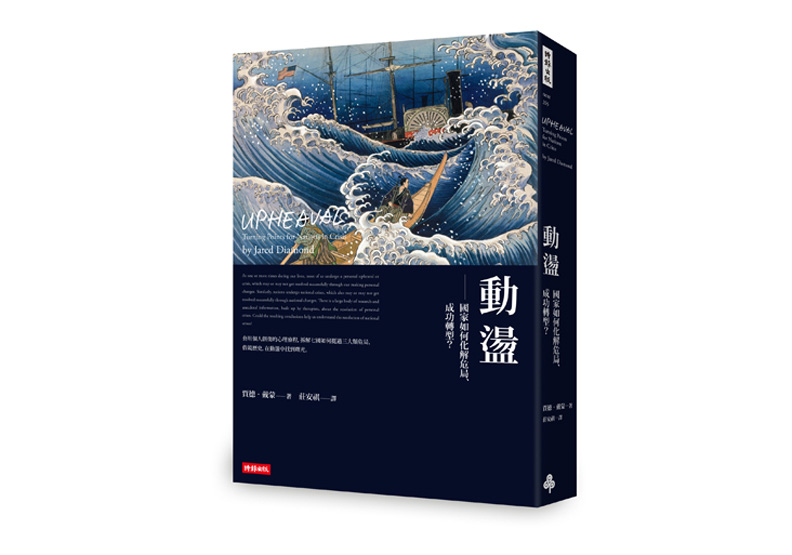日本以身為世上種族最單一、人口最多的富裕國家而自豪。它不歡迎移民,任何打算移民日本的人都得面對重重難關,即使有人移民成功,也難以取得日本國籍。從國家總人口的百分比來看,移民及其子女占澳洲人口的28%,加拿大的21%,瑞典的16%和美國的14%,但僅占日本的1.9%。對於尋求庇護的難民,瑞典接受92%,德國接受70%,加拿大接受48%,但日本只接受0.2%。(例如2013年和2014年,日本僅分別接受6和11名難民。)外籍勞工占美國勞動力的15%,德國的9%,但僅占日本的1.3%。日本確實接納臨時外國勞工(稱為「客工」(guest worker)),他們因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能(例如造船工人或2020年東京奧運的建築工人),而取得一至三年的工作簽證。但這類外國人很難取得日本的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身分。
二次大戰前和二次大戰這期間,韓國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是日本近年來唯一一次接受數百萬的大批韓國移民。然而這些韓國人中,許多或大多數都是作為進口的奴工而非自願移民。譬如不是很多人知道,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廣島時,10%的罹難者是在當地工作的韓國勞工。
最近幾位日本內閣部長呼籲增加移民。例如,地方創生擔當大臣石破茂(Shigeru Ishiba)說:「曾經,日本本地人移居到南北美,設法與當地人融合,同時保有身為日本人的驕傲。……當我們的人民在海外這麼做時,沒有道理對來日本的外國人說『不』。」秘魯曾有過日裔總統,美國也有過日裔參議員、國會議員和大學校長。但日本政府目前並未重新討論反對移民的政策。
政府的反對態度,也反映在日本人民於許多民意調查中所表達對移民的負面觀感,日本人的觀點和其他富裕國家的觀點恰好成極端。反對增加外國居民人數的日本人比例為63%;72%的人認為移民會使犯罪率提高;80%的人否定移民會引進新思想,改進社會,不同於57%─75%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和澳洲人認為移民會增進社會。反過來說,只有極少數日本人(0.5%)認為移民是日本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反之,高達15%的美國人、法國人,瑞典人和英國人則如此認為。
要澄清的一點是:我並非指稱日本人抵制移民是「錯誤」,且應該改變。在每一個國家,移民衍生問題的同時也帶來利益。每個國家都需要權衡這些利弊,擬定自己的移民政策。日本長久以來處於孤立,歷史上沒有過移民,又是單一種族的國家,因此高度重視其種族同質性也就不足為奇,而美國是種族多元的國家,幾乎所有的公民都是近代移民的後代,沒有種族同質性需要去珍視。日本的困境在於,它忍受著其他國家可以透過移民來緩解的公認問題,但日本尚未尋求出如何不訴諸移民的解決方案。

這些問題中最大問題是與上面討論相關的,包括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負擔,即人數愈來愈少的年輕健康勞工,納稅作為健康問題日益嚴重,數量日漸增多的退休人士之退休基金和醫療保健費用的經濟來源。儘管美國、加拿大、澳洲和西歐也和日本一樣,面對出生率下降和本土人口老齡化,但這些國家藉由容許大量年輕移民勞工來緩解這些問題。日本無法以聘用更多受過教育但未在職的媽媽,來消減勞動力的下降,因為在日本,美國在職媽媽聘雇大量移民婦女協助育兒的情況幾乎好不到。在美國,大量的移民男女填補了照顧老年人和醫院護士及其他醫院員工的工作,這在日本也不存在。(在我書寫本文時,才剛從一位身患絕症的日本親戚,可怕的死亡經歷中復原,一般認為在她住院期間,家人理當提供她三餐,為她清洗貼身衣物。)
從授予日本發明家的大量專利來看,日本在創新方面相當活躍,日本人擔心的是,相較於在研發上投入的大量資金,日本人的突破創新不如預期,這反映在獲頒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數量較少。大部分美國諾貝爾獎得主不是第一代移民,就是他們的後代。然而與日本人口問題一樣,日本科學家中,罕見移民及其子孫。如果考量到願意冒險和嘗試全新事物的意願,是接納移民和達到最高程度創新的先決條件,對於移民和諾貝爾獎的關連就不致有所訝異。
短期內,日本並不願意藉由移民來解決這些問題。長遠來看,日本人是否會繼續忍受這些問題的困擾,或願意藉著改變移民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又或找出移民外的其他解決方案,還不得而知。假使日本確實決定重新評估接納移民的可能,或許加拿大的政策會是適合日本的模式,根據對加拿大的潛在價值,對移民申請者進行評估。
──
移民問題外,另一個被忽略的重大問題是二戰時,日本之於中、韓兩國的行徑對現今它與這兩國關係的影響。二戰期間與之前,日本對其他亞洲國家人民的作為令人髮指,特別是中、韓兩國。早在1941年12月7日「正式」宣戰前,日本已於1937年展開全面侵華,殺害了數百萬中國人,方式野蠻,例如捆綁中國囚犯作刺刀練習,以加強日本士兵的意志,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間,在南京屠殺了數十萬中國百姓,並為了報復1942年4月美國空襲東京(Doolittle Raid,由杜立德中校策畫,故名杜立德空襲),而殺死了其他許多人。儘管今天日本境內一概否認這些屠殺,但是當時的檔案皆被完整保留下來,不只中國人和外國觀察家有記錄,日本士兵本身也拍下照片。(在史詠(Shi Young)和尹集鈞( James Yin)的《南京大屠殺:歷史照片中的見證》(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1999年出版)一書中,即收有400多張這樣的照片。)日本於1910年兼併韓國,在35年的占領期間強迫韓國學校使用日語而非韓語,迫使大批韓國和其他國籍的婦女作為日本軍中妓院的慰安婦,並強制大批韓國男子擔任日本軍隊的奴工。

因此當今的中、韓兩國遍布仇日情結。在中、韓兩國人眼裡,日本對其戰時暴行並沒有充分承認、道歉或表示懊悔。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而南、北韓的人口總數也超過日本的一半。中共和北韓都擁有核武。中國和兩韓都有配備精良的大型軍隊,而美國人制訂的日本憲法加上日本盛行的和平主義,使得今天日本的武裝部隊微不足道。北韓不時試射飛彈飛越日本領空,展示輕易到達日本的能力。而日本又與中國和南韓為了無人居住的小島起了領土紛爭,這些島嶼本身雖無價值,卻因各島領海內的漁獲、天然氣和礦產資源而變得重要。在我看來,這些事情長遠下來對日本是很大的危險。
擔任新加坡總理數十年,對日本、中國、韓國及其領導人都很熟悉,同時也是敏銳觀察家的李光耀,從亞洲人的角度看日本對待二次大戰的觀點,他的看法是:「和德國人不同,日本人並沒有宣洩並去除他們體制內的毒素。他們沒有教導他們的年輕人:二戰時他們做了什麼錯事。橋本龍太郎(1996至98年擔任日本首相)在二戰結束52週年(1997年)時曾表達「最深切的遺憾」,1997年9月訪問北京期間也表示「深深的悔恨」。然而,他並沒有如中、韓兩國人民所期望的以日本領導人身分致歉。我不懂為什麼日本人如此不願承認過去的錯誤,為此道歉,接受現實往前走。出於某些原因,他們不願道歉。道歉等於承認做錯事,表達遺憾或懊悔,就只是他們目前的主觀感受。他們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韓國、菲律賓人、荷蘭人以及其他婦女在戰時被綁架或遭逼迫成為日本士兵的「慰安婦」(性奴隸的委婉說法);也否認對中、韓、蒙古、俄羅斯和其他滿洲國的囚犯進行殘酷的活體生物實驗。上述事件,唯有從他們自己的記錄中看到無可辯駁的證據後,他們才會不情願地承認。這引發人們對日本未來意圖的懷疑。日本眼前的態度是未來表現的跡象。如果他們對自己的過去感到羞恥,就比較不會重蹈覆轍。」
每年,我在洛杉磯加大的教學課程都有日本留學生,他們向我談起他們在日本受的學校教育,以及他們來到加州的體驗。他們告訴我,日本學校的歷史課很少談到二戰(「因為這場戰爭在幾千年的日本歷史中僅占了幾年」),很少或根本沒有提到日本作為侵略者的角色,強調日本是受害者(兩顆原子彈造成約12萬日本民眾死亡),因而無需對數百萬其他民族及數百萬日本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負責,並指責美國以某種手法欺騙日本發動戰爭。(平心而論,韓、中和美國的教科書對於二次大戰都有各自偏袒的表述。)我的日本學生加入洛杉磯的亞洲學生協會後,認識了韓國和中國學生,首次聽聞日本的戰時行徑至今仍讓其他國家的學生深感憤慨時,大受震撼。
同時,我的另一些日本學生和其他日本人則指出,日本政壇人物已多次道歉,並反問:「難道日本道歉得還不夠多嗎?」答案是:不夠,因為這些道歉聽來很牽強,難以信服,且參雜最低化日本的責任或全然否認的言論。說得更詳細點就是,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在面對它們近代史之遺禍時的相反作法,並質疑為什麼德國的作法很大程度上說服了它的前敵人,而日本的作法沒有說服它的主要受害者中國和韓國。第六章曾說明德國領導人表達悔恨和負責的多種方式,並教導德國學童正視他們國家的作為。如果日本有類似德國的回應,中、韓兩國可能會相信日本的誠意:例如,日本總理訪問南京時,在中國民眾面前下跪,並請求原諒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殺;如果日本各地都有博物館和紀念碑及前戰俘營,展示照片,詳細描述日本戰時的暴行;如果日本學童經常被帶到日本的這些地點,以及日本以外,如南京,山打根,巴丹和塞班等地進行校外教學;如果日本投入更多心力描繪戰時的非日本受害者,而不是日本的受害者。在日本,這些行動全都不存在遑論想像,然而在德國卻是廣泛實行。在日本能做到這些前,中國人和韓國人都不會相信日本照本宣科的道歉,且會繼續憎恨日本。只要中、韓全副武裝,而日本又無力自衛,日本就會持續暴露在巨大的危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