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明要比歐洲文明進步。歐洲的印刷術、造紙術、火藥、羅盤針和運河的水閘,皆是直接或間接從中國傳來。然而,世上第一波穩健的經濟發展首度發生在歐洲,工業革命繼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現代的標記,如代議政體和人權觀念,也是發軔於歐洲。歐洲是怎麼一回事?
1480年,中國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險和貿易,繼續從事貿易的商人被視為走私犯罪,皇帝會派軍隊破壞他們的居處,燒毀他們的船隻。但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曾經濫用或自許有這樣的威權,畢竟宣布如此閉關自守的律令代價高昂,沒有一個國王負擔得起。在歐洲,當國王的總是強敵環伺,而中國皇帝的君權無人能比,這是他們擁有的優勢——或者說是陷阱。歐洲國家之間相互為敵,是它們向海外擴張的一股推助力量。
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再也不曾出現一個統領整片疆土的強大力量。想像一下羅馬曾被某個單一勢力征服,就像中國被滿族、印度被蒙兀兒人、中東被鄂圖曼人土耳其征服那樣。藉由征服,這些異族搖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羅馬的征服者卻是數個不同且互相敵對的日耳曼蠻族。這些蠻族從來就沒當過什麼主人,與其說他們征服了羅馬帝國,不如說他們在踏上這個帝國土地後,發現它正在自己的腳下融化。他們毫無治理固定國邦的經驗,連羅馬賴以維生的徵稅機制都維繫不住。由此,他們顛覆了普世政府的一個通則:治理轄下的國家卻課不了稅。
不是所有東西都歸國王所有
歐洲的歷史演進泰半從奠基的這一刻起便已註定。政府對人民毫無掌控能力,它們必須殫思竭慮,才可能爭取到人民的服從。它們若想擴張勢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維護治安作為回報,它們不能像亞洲和中東不計其數的帝國及王國那樣,光靠收稅機制和進貢就能運轉。
數百年來,這些國王最大的威脅,是他們最有權勢的下屬——有地的貴族階級。這些權臣最後終於俯首,但因為已在自己的領土上雄霸夠久,早就為自己也為他們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到私有財產的保障。「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屬於國王」,是歐洲自由和繁榮的基石。
為了讓貴族俯首稱臣,國王對城市裡的商賈、貿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賴,一來他得靠這些人提供貸款和人力才能維繫官僚體系,二來這些人的財富可以課稅。歐洲君主的徵稅細水長流、手法溫和,以免殺死了下金蛋的雞母;亞洲國家的統治者比較獨裁,徵收苛捐雜稅之餘,手頭拮据時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貨品沒收充公。
歐洲君主低調謹慎是不得已的,因為在這個群雄環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壓太過,可能轉而投靠敵營。在此情況下,他們重視經濟發展和新興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為,雖然這些科技主要用於戰事,但和現代殊無不同的是,這些國防花費可能帶來重大回收。除了謹言慎行之外,他們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身負的義務,因此比較不會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樣的場景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比歐洲常見得多。
這些歐洲君王降伏舊日貴族後,隨即成為一個活躍的新興階級——城市裡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當年這些君主勢單力薄,曾經允許各個城鎮自治,而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也變得更加舉足輕重。相較於自擁大軍、躲在城堡裡防禦自己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脅性。然而,無論貴族多難應付,他們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裡,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反觀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根本毋須國王的存在,長遠來看,對於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更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逐漸增添權勢——只有在英國,君王猶在國會的馴服下,這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留存下來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們商量國事。即使是專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國,國王的命令也不是無遠弗屆、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和特別交易。法國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分的迷你三級會議卻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於1780年代推動的稅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當時法王試圖變革失敗,被迫重新召開國家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議會政府得到啟發,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義大利,從來不曾有哪個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皇帝和教宗長年為權力明爭暗鬥。在這個地區,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儼然多個獨立小國,是歐洲權力分散的一個極端例證。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個歐洲也因這兩場運動脫胎換骨。
權力分散、遺產多元
歐洲在政治上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個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一直被稱為基督宗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不分國界、屹立於所有土地上的組織。教會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國政,但國王雖然肩負護衛基督信仰的義務,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教會唯命是從、有求必應。教會與國家之間總是關係緊繃,最突顯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宗和皇帝之間的劍拔弩張,而這又是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宗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一些學者將《聖經》和古學術編織於一,製造出一套頭頭是道的神學思維。
但教會也有罩門,它的聖典對教會本身的結構隻字未提——教會其實是個以羅馬統治為範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羅馬學術是異教徒的作品。藉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在中國,權力是極其明確的集中在皇帝手裡,以儒家為尊的精英文化對君權統治也支持有加。無論是個人修為或待人處世,中國人莫不以儒家思想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統治者不管有沒有正當性都得熟讀四書五經,而你得通過儒家經典考試才能當上國家官員。
反觀歐洲,權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個大拼盤,與君權統治之間的繫帶並不牢固。中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們的聰明從來不會脫軌失控,縱有奇思異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紛擾。歐洲社會的開放則是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智識生活百家爭鳴,皆是基於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是壞,從來沒有一個單一強權掌控過它、型塑過它。它多元的歷史遺產因此能被充分發掘、延伸,如希臘的數學觀念就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從而建立起科技創新的一個新基礎。
經濟歷史學家拋出一個問題,問歐洲何以在工業化方面跑第一,就彷彿其他社會跟歐洲在同一個軌道上並行,結果率先達陣的是歐洲。派翠西亞.克隆,也就是本書的諸多靈感來源,卻是這樣問:「歐洲究竟是跑了第一?還是怪物一個?」在她看來,歐洲無庸置疑,不折不扣是個「怪物」。
伴隨工業化的自由與威脅
因歐洲是由眾多國家組成,故彼此之間衝突不斷。20世紀歐洲國家打了兩場慘烈的戰爭,士兵與人民慘遭屠殺的人數創下新高。二戰期間,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統治下的納粹德國,試圖有計畫的滅絕歐洲猶太人,這是歐洲史上最恐怖的事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本書先前介紹過的兩股力量正是其元凶:起源於德國的民族主義,以及始於英國的工業化。
民族主義強化了人民對於國家的依戀,以及為它奮戰與犧牲性命的意志,同時激勵沒有國家的人努力建國,成為中歐與東歐國家的重大衝突來源,使得這些國家開始在歐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工業化則使人們離開鄉下,進入社會同質性更高的城市,促使人口快速成長,擁擠程度前所未見。大家學會閱讀,透過學校與報紙了解社會,而報紙是由蒸汽驅動的機器大量印製,成本非常低。20世紀的人也開始聽廣播與看電影,而希特勒就是廣播界出身,也算是新型態的電影明星。正當舊時的社會束縛放寬、教會變得不再重要,國家認同感也成為學校的重點教育,並透過新媒體傳播,幫助大家團結一心。民族主義就像宗教的替代品,讓每個人在永恆的共同體中,都有安身立命之處。他們不再是「基督教國家的基督徒」,而是「法國的法國人」或「德國的德國人」;國歌、國旗、民族英雄、神聖的時刻與地點,都是為了讓人更依附這種新信仰。
如果民族主義是為了戰爭而生,那麼工業化就是讓戰爭更加惡化,新的鋼鐵廠開始能夠生產更大、更多、更具破壞力的武器。槍枝原本是手工製作,工匠必須確保所有可動零件皆可拼合;但隨著更準確的器械問世,所有零件都可以製造得完全一致,這也讓工廠能夠大量且快速的生產它們。事實上,槍枝就是史上第一個透過此法生產的產品,比汽車還早了60年。
自此,歐洲民間出現了全新的大規模現象——大量生產、群眾社會、大屠殺。
工業化替歐洲社會帶來了新的內部威脅。農民經常造反,卻也輕易被平定。新工業城中的工人,無論工作或生活都更加緊密相依;他們學會讀寫,也就能了解自己被什麼力量控制,於是成立組織來持續抵抗。透過這種方式,他們主張自己想過更好的生活,並對社會脈動發聲。
工人發起抗議活動,要求政治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所有男性皆可投票」。他們組織工會對抗老闆,要求更好的薪資與待遇,甚至組成政黨,目標是消滅老闆與商業利益,讓工業為了工人的福祉而運作——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主軸。或者,他們發現和平手段無法改變任何事情,覺得心灰意冷,於是策劃革命、擺脫老闆,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度。這些共產主義革命家在歐洲並沒有成功太久;但他們確實在俄羅斯成功過,因他們統治俄羅斯而產生的恐懼感,在歐洲激起一股強大的力量。民族主義者痛恨共產主義者,因為共產主義者主張工人不該為自己的國家而戰;他們說,各國的工人應該合作對抗老闆,以及保護老闆的政府。
拜工業化所賜,中產階級、商人、銀行家、製造商與其麾下的專業人士,地位都水漲船高。他們是存在已久的階級,並在貿易與工業開始成長之際,成為重要的勢力。專制的君主遂利用這股勢力的財富,並僱請他們為自己效力。在19至20世紀之間,這股勢力是自由派政策的最大推手——包括代議政府、法治、個人權利與自由,而這個自由包括媒體與集會的自由,以及商業營利的自由。所有政策都是直接對抗君主與貴族的統治。但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又不希望將權利交給人民,由此可知,他們並非民主主義者。對於大眾的需求,他們該支持或反對到什麼程度?這是個持續存在的兩難。而工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該接受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領導,一起對抗特權階級?或者工人會慘遭利用與背叛?
這些力量如何展現於19世紀歐洲的三大國家,就是我們首先要審視的主題。工業化真的是革命的導火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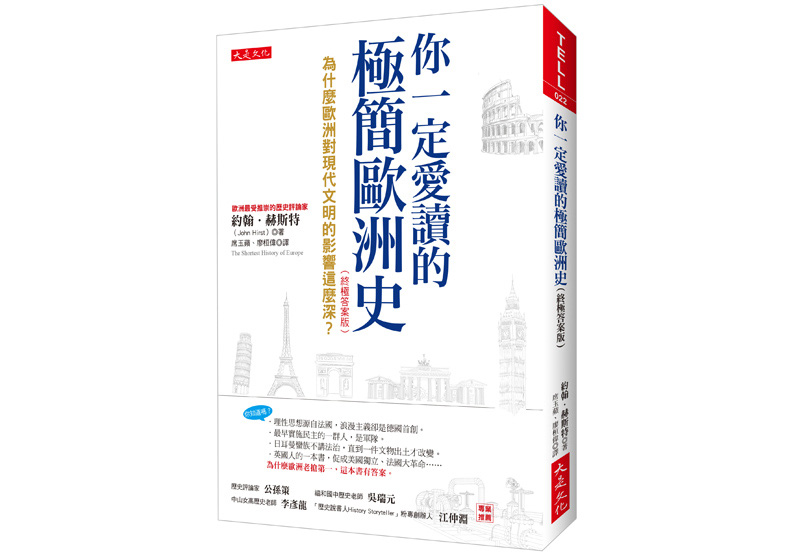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終極答案版):為什麼歐洲對現代文明的影響這麼深?》一書,約翰.赫斯特著,席玉蘋、廖桓偉譯,大是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