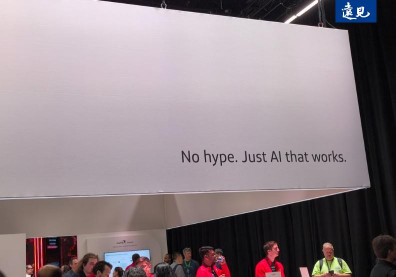那人踏在世紀的扉頁上,跫音橐橐作響。走過兩次大戰,目睹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叫囂對峙,足跡遍及南歐、拉丁美洲,終身以猶太知識分子自居,一生與二十世紀纏繞糾葛的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在完成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後,終於「自我解禁」,以史筆回憶這個讓他又愛又恨的二十世紀。
親身走過大半個世紀,霍布斯邦史觀中的二十世紀,長度比其他史家認定的還要短得多。為期七十七年的二十世紀,始於一次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終於蘇維埃年代終結的一九九一年。與漫長的十九世紀相比,霍布斯邦為這個他生存的年代下了個宣判:短促的世紀,極端的年代。
老史家聚積的觀感、偏見與反思
以十九世紀為主要研究範圍的霍布斯邦不諱言,他是以「參與性的觀察者」,而非學者的身分,撰寫這部上下兩冊的二十世紀歷史。這本史書聚積了他對世事的觀感與偏見(無怪乎始終保持共產黨籍的他認為,二十世紀是在共產主義崩盤時結束),也以過來人的角度反思一樁樁歷史事件造成的跨世衝擊。
和其他回顧二十世紀歷史的書籍不同的是,本書在每一章的開頭大量引用本世紀的學者、政治人物的談話,回溯他們對這個世紀的看法。他們眼中的二十世紀,多半能反映作者的觀察,正如音樂家梅紐因(Y. Menuhin)所說:「它(二十世紀)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在這個短命的世紀中,人類共同經歷了古帝國與舊強權的消失、式微;兩次死傷超過數千萬的世界大戰與無數次戰爭(至今仍持續上演);地球生態危機;世界人口暴增(從世紀之初的十六億到現在的五十九億)。樓起樓塌,種種衝突都在極端的年代中浮光掠影似地重演一番。
兼具知性與感性的霍布斯邦,以舉重若輕的筆調,刻畫沈重的歷史暗影。他從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國總統密特朗突然造訪戰火中的塞拉耶佛開始寫起,鳥瞰這個悲喜交集的世紀。沒有人想到密特朗為什麼要挑這一天去,但霍布斯邦以史家的敏感與敏銳記憶,解讀了這次造訪的特殊意涵:七十八年前的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就是在這裡遇刺身亡,催折本世紀歷史的一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
歷史的記憶,如今已然死去。垂垂老矣的霍布斯邦感嘆,二十世紀末期的人,與過去的歷史完全割裂斷絕,心中只有永遠的現在,與眾人共同的過去缺乏有機的聯繫。這點不只西方獨然,否則在亞洲也不會只有老一輩的政治家,才會年年要求日本正視戰爭期間的侵略行為。
代與代的連結崩裂,歷史不再被尊重
在詮釋歷史方面,霍布斯邦捨棄編年式的寫法,改將這七十七年劃分為三階段——大災難時期(一九一四—一九四五)、黃金年代(一九四五—一九七三)與解體分散危機重重的年代(一九七三—一九九一),分章詳述各階段的重要里程碑。他從戰爭、經濟、國際政治、自由主義、藝術、冷戰、文化革命一直寫到科技革命,洋洋灑灑,一氣呵成,流露「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的才情。
將二十世紀定在蘇聯帝國落幕之際結束,除了信仰上的堅持外,霍布斯邦更認為蘇聯解體不只是一段歷史的終結,更是由石器時代開始的七、八千年人類歷史的告終。因為漫長的農牧年月在此時總算落幕,全球經濟體登上主宰的舞台。
在他的歸納中,二十世紀有三個最重要的轉變。首先是這個世界再也不以歐洲為中心。在本世紀初,歐洲仍是西方文明的霸主,至少掌握地球陸地四分之一的土地、五分之一的人口。二次大戰結束後,受兩次大戰蹂躪的歐洲逐漸衰敗,帝國日落,歐洲各國人口也日漸稀少,出現負成長。反之,霸位易手新大陸,這個世紀竟是美國的世紀,是一頁看她興起、看她稱雄的歷史。
第二個巨變是世界逐漸演變為一個單一的運作單位,舊有以領土國家政治為界定的國家經濟,讓路給跨國性的地球村。經濟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瓦解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盛行的世界觀。
讓老史家霍布斯邦最擔憂的是第三種變遷,即舊有人際關係模式解體,代與代之間的連結隨之崩裂。社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中心,過往的歷史不再被尊重。「這是一個過去已經在其中失去地位的世界——甚至包括眼前的過去,」霍布斯邦不無嘆息地說。
跟世紀末這些社會、經濟、文化大變動相比,二十世紀為期最長的戰爭——「資本」「共產」主義兩方的對抗歷史,就顯得狹小許多。他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議題是冷戰的形成、自由主義的垮台,以及法西斯的威脅,其他所有的事件都可以包羅在這三個議題裡。霍布斯邦利用多元的觀點,書寫了資、共雙方拉鋸之下的世界歷史。他的敘史筆法也不採用英雄的史觀,而是以剖析社會現象及其影響為主。
漸進與驟變同時滲透人類經驗
另一方面,正如霍布斯邦所言,這個世紀是一個漸進與驟變同時滲透人類經驗的世紀,他以極長的篇幅探討本世紀的科學演變,稱許本世紀的科學成就是人類意識的偉大表現。他表示,自然科學在二十世紀無孔不入,本世紀對科學的倚賴也是前所未見,科學家已經成為社會的精英階級。不論科學發明多麼艱澀難懂,一旦發展出來,就立即轉往實際用途,因而改變了人類的思維運作法則。
最後霍布斯邦在「邁向新千年」這一章裡,言之諄諄地預警未來的危機。他深信世界經濟必然繼續成長,但是國家之間的貧富不均將日益深化,經濟變動產生的社會衝擊將繼續騷擾著新世紀。更重要的是,人類信奉了將近三百年的理念,在此刻由根開始撼動傾頹。自十八世紀初期出現的「現代」擊敗「古代」以來,人類對於理性、人性的假定——這些各種現代社會賴以建立的理念,一一陷入莫大危機。
儘管掙脫不了歐洲中心觀點的束縛,霍布斯邦仍企圖以宏觀世界政治、微觀各社會現象的視野,呈現這個短促如走馬燈的世紀。就如他自己所述,這本書除了有學者的專業研究之外,還有他個人自傳的意味。《極端的年代》是一個活在當代的史學家,集畢生的研究功力及豐富的生命經驗所完成的當代活史書。
(蕭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