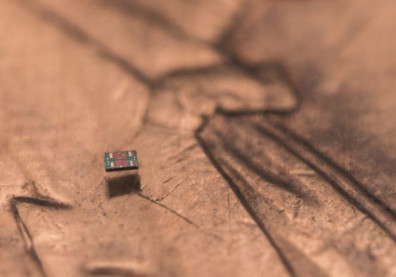在一個公園裡,一位爸爸蹲下來跟孩子說:「我跟你說過很多次了耶」,他的語氣非常溫和,像是在說一個遠在天邊的故事:「你不能這樣做,這東西是別人的。如果你再繼續這樣,還是我就先帶你回家?」
相較於爸爸前半段「說故事」時的沉默,面對這個「問句」,孩子很快就有了反應:「我不要回家!」
爸爸還是一派溫和理性:「那你就不能那樣做啊,知道了嗎?」
孩子:「知道了。」
假溝通真強迫
在某些人還在猶豫「怎麼正確打小孩」的現在,有些大人已經開始考慮不用打罵作為教育的手段,而是試圖採取其他的方式來對應教育現場的問題或困境;比方說上面例子裡的爸爸,正試圖跟孩子「溝通」,或者說是「講理」,讓小孩願意接受大人的「建議」。
然而,有些大人可能會發現,這種「講理」的方法時常只有非常短暫的效用。有些教養專家認為這是「說法」的問題,比方說把「老娘叫你從桌子上下來」改成「請你從桌子上下來」,或者進一步改成「你從桌子上下來就可以吃糖糖喔」「你把作業寫完就可以玩玩具喔」,就可以改變溝通的品質或成效。
但真的有照著教養專家的建議使用這些句子的父母,也可能會發現這些句子的「有效期限」非常短暫,很快地小孩就不再接受這些說法,回到一開始「講不聽」的模式之中。以上面這個例子來說,小孩可能在爸爸一個轉身之後,就立刻去做了那件他曾經答應爸爸不要去做(或要去做)的事情。有些人會因此轉而相信「小孩果然是不能講理的」。
「你要吃大便口味的咖哩,還是咖哩口味的大便?」在許多的教育現場裡,大人以為這種被自己設定過範圍的「討論」便是理性溝通,但其內涵卻是某種程度上「假溝通真強迫」的權力運作。
如果最後小孩無論如何都要聽大人的,「講理」或「溝通」就不是一種「試圖互相了解,並且經由彼此妥協來尋求共識」的過程,而是大人表現「優雅理性」的一種強迫的「形式」,那麼小孩就可能會開始發展各種辯解的技巧,以期在「講理的競技場」中擊敗大人。
只要實際統計一下,從結果看來,在大人跟小孩的「溝通」裡有多少比例「最後仍然是聽大人的」,又有多少比例「最後大人願意聽小孩的」,就能得到一個非常客觀的數字,來檢驗大人跟小孩的「溝通」究竟有沒有淪落為「形式上的講理」。
不強迫也不放縱
在一個工作坊裡,有媽媽問到「如果小孩不去做那些他應該做的事,那該怎麼辦?」我反問:「他覺得那件事情是他應該做的嗎?」
媽媽:「嗯,像是刷牙,或者繫安全帶,我花了很多時間跟他解釋,確定他了解這些事情的重要性了,但他還是不願意去做。我該怎麼辦?我可以強迫他嗎?可是不強迫他,難道要眼睜睜看著他蛀牙嗎?不坐安全座椅我也不能接受。」
假使我們不要「講理形式的強迫」,難道要放任小孩蛀牙、過敏、近視、營養不良、睡不好、冒著被甩出車外的風險嗎?這是我在親職教育現場時常被問到的「考古題」之一。
大多數情況下,若有一個「旁人」要在缺乏資訊或欠缺考慮的情況下,做出傷害自己身體的行為時,無論他是不是我們的小孩,我們都會傾向於「暫停」他的行為,為他補充資訊或請他詳細考慮。這種程度的「干預」,我們大概不至於會覺得是對旁人「強迫」;同樣地,我認為我們也可以在小孩「缺乏資訊或欠缺考慮的情況下,做出將要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之前,試著「暫停」小孩的行動,為小孩補充資訊或請他詳細考慮。
在「不強迫」與「放縱」之外,我們至少可以做出「補充資訊」與「邀請孩子再想想」這兩件事。這就是「不強迫小孩」又「不放縱小孩」的可能性。
但這種程度的「干預」並不保證孩子會按照我們的期望去做或不做某件事,這對教育現場的大人來說恐怕還是不夠的;對照顧者或教育者來說,在現場有許多「不得不在意的事」,比方說「安全」和「健康」,讓大人「很想要強迫小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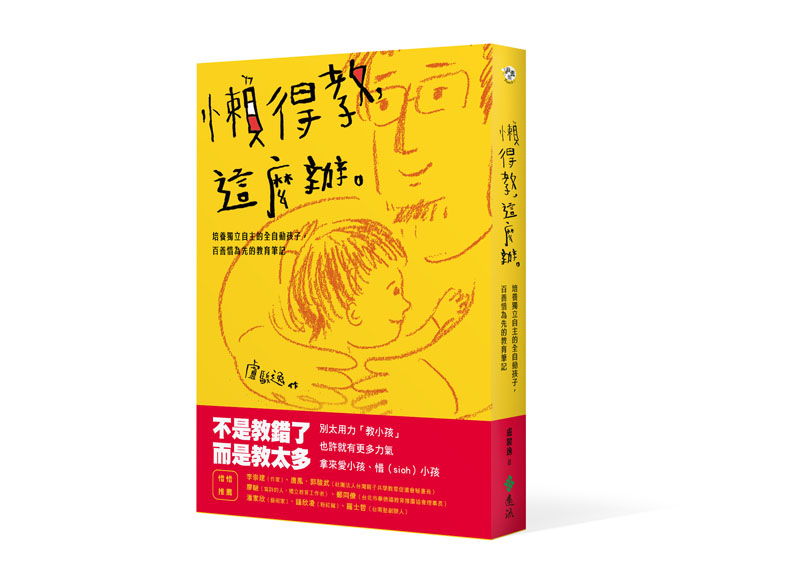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懶得教,這麼辦》一書,盧駿逸著,遠流出版。
本文節錄自:《懶得教,這麼辦》一書,盧駿逸著,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