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放學後帶著女兒和兒子去吃飯。一個心情不太好的日子,照慣例得要來杯珍珠奶茶,平衡自己的心情。
天氣很冷,天空又開始飄起細雨,接過店員遞過來的珍珠奶茶後,我立刻想要鑽回車上。兒子跟在我身後,迅速地回到車邊,我轉身一看,卻看到女兒還在飲料店櫃檯前發呆,呼喚她的同時,店員也提醒她母親和弟弟已離去。她急忙坐上車,垮下了臉,開始氣呼呼地碎唸:「你怎麼可以不等我?你怎麼可以不叫我?」
我心裡有點冤枉,告訴她:「媽媽怎麼可能不等你呢?我剛剛不是看到你還沒來,就叫你了嗎?」她仍然難以平復,像張口就壞掉的收音機,反覆播放著相同的走音旋律。車廂裡的我們,碰撞出一股難以言喻的、窒礙的氣氛。
我突然想起女兒小時候的經驗。
她有一個忙碌的爸爸,和一個在念博士班又懷孕的媽媽。她兩歲那年,因為我們實在忙不過來,只好將她暫時送回南部阿嬤家「託養」。卻又正逢阿嬤更年期身心失調,當阿嬤身體狀況不太好時,女兒又會被送到兩個小姑家輪流照看。
想到這裡,我似乎懂得了她情緒背後的不安,於是閉上了嘴,用聆聽來接住她的抱怨。她的碎唸聲卻逐漸轉小,留下窗外沙沙的風雨聲。
你看過有人弄丟他的頭頭、手手和腳腳嗎?
到家後,我停好車。女兒卻遲遲沒有要下車的模樣,小聲猶豫地說了句:「我就是怕被你弄丟嘛!」我轉頭看著她,對她說:「我知道。所以我打算等下好好地聽你說這件事。」她似乎有點滿意地跳下車。
進到家門,我喚女兒來坐在腿上,看著她的眼睛,問她有沒有想對我說什麼?她又說了一次:「我就是怕被你弄丟嘛!」
依照我的理解,當某人反覆提起某些重複的語句、重複的關鍵字時,通常是背後還有一些卡住的情緒沒能表達,尤其對年紀小的孩子而言,常常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提醒別人關注他的情緒,以修通某些潛藏內在的不安。
於是,我突然對「弄丟」兩字有了一些聯想,我想起自己是個時常會將手機和皮包忘在餐廳的糊塗媽媽。我試著問女兒:「你是覺得媽媽會像弄丟手機和皮包一樣,把你弄丟嗎?」沒想到,女兒聽我這麼說,還真的點點頭,給我相當肯定的答案!(真是好樣的,原來女兒覺得,她在我心中的地位,跟手機和皮包是一樣的……)
我頓時有點語塞,想了想後,又問她:「你有看過有人弄丟他的頭頭嗎?」她搖搖頭。
「你有看過有人弄丟他的手手嗎?」她又搖搖頭。
「對媽媽來說,你就跟媽媽的頭頭和手手一樣。」她專注地看著我。
「你剛出生的時候,身上有一條臍帶把我們連著,雖然那條臍帶已經被剪掉了,但在媽媽心中,那條臍帶還連著我們。所以對媽媽來說,你就跟我的頭頭、手手和腳腳一樣重要。」她突然靠上來抱著我。
「你有看過有人弄丟他的頭頭、手手和腳腳嗎?」
她搖搖頭,又哭又笑。
接住了她,也接住了自己
我倒是想起自己小時候,時常感覺到被「弄丟」的經驗。
在大賣場裡,我多次弄丟了媽媽的手,在陌生的環境和人群中,一個人焦急地流著眼淚。長大以後,這種感覺逐漸擴大成人際和伴侶關係中的不安。
好幾次,在分析中,治療師不厭其煩地用聆聽「接住」了這種感覺。我非常感謝他(們),從來沒有用什麼詭異的名詞來隨便定義我,於是突然有一天,我發現自己身上開始有了這種「接住」別人的能力。
有些時候能接住所愛的人,更多的時候能感受到自己被伴侶穩穩地接著,不知不覺長出更多力量,「接住」更多案主,陪伴他們和我一起成長。在接住和被接住的過程中,我們好像慢慢地把弄丟的自己找回來了。
就像我和女兒相互擁抱的那一刻,看似我接住了她,卻更像是我也接住了自己,接住了那個年幼焦急且慌張的自己。
這種感覺讓我對人性抱持無比正向的希望:倘若我們覺得自己的人生總是遇人不淑,找不到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人,那麼我們更要學著去接住別人。
或許,這就是老天幫我們打開的另外一扇懂得自我悅納的大門。
==================================
【關鍵字效應】
某些重要經驗發生時,過去的心結會透過重複性的語言,在經驗當中展現。覺察人我之間,某些共同存在的心結,將有助於營造具有滋養性的關係。
在心理諮商的實務訓練中,諮商師總會敏感於當事人會談時重複出現的主題。這裡提到的「關鍵字效應」,即是以心理諮商的精神,探討我們如何透過情緒性的行為,來辨識他人和自我的內在,有著什麼樣共通的、還未被解決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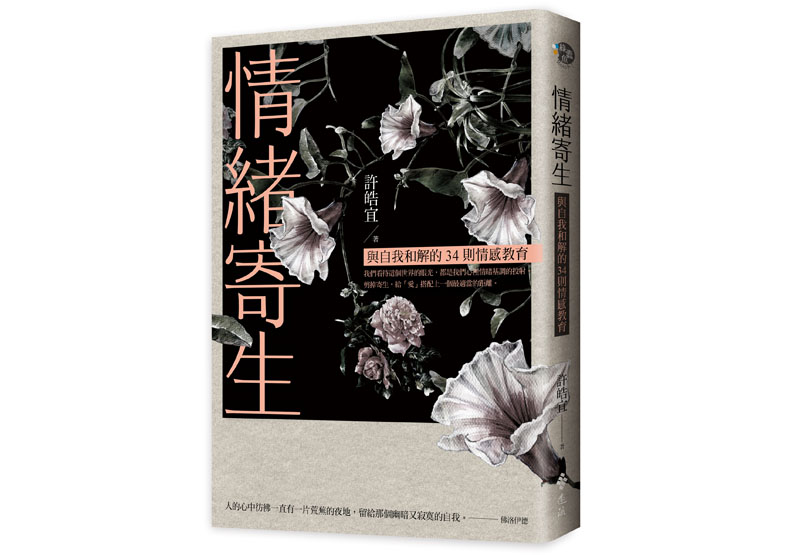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情緒寄生:與自我和解的34則情感教育》一書,許皓宜著,遠流出版。
本文節錄自:《情緒寄生:與自我和解的34則情感教育》一書,許皓宜著,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