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問理智層面的自己,家中最容易涉入我私領域的人是誰?顯然我會回答,是媽媽。但若避開理智,問問感受層面的我?最容易踩進我地雷的,卻是爸爸。
我父親的原生家庭,人丁興旺,光我阿嬤一個人生的孩子,就幾乎可以組成一支足球隊。我沒有看過他們當年生活的景況,但對我這個沒有手足的人而言,光想到一個家裡有二十隻孩子的腳丫子在那裡蹦蹦跳跳,我的頭都疼起來了,心裡實在無法想像,父親當年是怎麼在家庭的夾縫中生存的?
還好,父親依然個性積極地長大,在那個升學十分艱難的年代,他跟著前面兩個哥哥的腳步,考上當地最好的初中,誰知高中聯考失利,讓他開始偏離大家想像中一路頂尖的菁英生活。
父親的手有一截淺淺的斷指,我小時候偷偷問過母親那背後的故事,腦海中卻總是記得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有一說,那是父親求學時去工廠打工,不小心被機器截掉的?還有一說,則是父親曾經墮入黑道,為了退出江湖,只好斷指謝罪?
說也奇怪,明明前一個才是事實,我卻常常記成是黑道的那個版本,彷彿一定要這種充滿浪漫的際遇,才符合我心目中父親的英雄形象。
父親的「第一志願情結」,不知不覺地落到我心上,只是上了國中以後,課業越來越難,我不只讀得辛苦,有些科目還覺得無聊,成績一階一階地往下掉。
眼看高中聯考就要到了,父親看我只玩社團不思振作,便問我:「台南一中音樂班好像有收女生,要不要去考考看?」這個突來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慌,心裡想著:倘若連我也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父親會不會受到比我更大的創傷?
真抱歉,身為一個青少年,我的解讀只能是如此而已。
當我在生涯中掙扎時,父親也在他自己的職涯中碰撞;當他在職場中大放光亮時,我從碩士班畢業考上博士班;當他面對職涯的瓶頸時,我也正在低落;當他商場上退休後又突然轉入教職,我也回到台北來任教。我們的生涯像兩條在無意識中同起同落的平行線,我看著他的影子,也追隨他的影子。
我期望他能理解我一路走來的辛苦,但當我在工作上感到不開心,沮喪地說好想離職時,他對我說:「你至少要撐到當教授。」當他發現我仍繼續沮喪時,他沒有安慰我,反而丟了好幾個徵才訊息給我。
我和父親相處不多,但他的回應總能讓我氣上半天。我知道他想告訴我的是:加油。但或許我更期待他說的是:不要再加油了。
我想,這世上有很多父母不能明白,不用加油的語言,才是一種真正的加油。
陌生與疏離,讓彼此一不小心,就會刺傷對方
日本頹廢派作家太宰治曾經說,他這一輩子都在為服務別人而活;或許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也一樣為了服務父母而活。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寧願死,也不想面對父母失望的眼光?因為從那種失望的眼神中所折射回來的,是一個不夠好的自己,不完美的我。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幸好有這些成長經驗,我第一次讀《諮商概論》,就每句話都看得懂;幸好有對成長經驗的體悟,我當心理師,當的得心應手。心理諮商,成了我活下去的救贖。
我想,每個人都是在磨難中活下去後,才找到新的救贖。
父親即將屆齡退休,我以為他這次會好好規劃自己的退休生活,但他仍忙著幫自己安排新的工作機會。看著他坐在電腦前認真打字的背影,我突然理解,他對待我的方式,其實也是他對待自己的。我感受到退休的男人們,面對老後如果沒有了期待,沒有了舞台,剩下的或許會是無止盡的恐慌。他們需要子女的陪伴,但是前半生已經習慣的陌生與疏離,又讓彼此一不小心,就會刺傷對方。
我想起著名的刺蝟故事:一對相愛的刺蝟在寒風中,想要靠在一起取暖,可是當牠們靠得太近,就會被對方身上的刺弄傷,牠們只好不斷地挪移位置,調整彼此的距離,一下前進、一下後退,直到找到一個既能相互取暖,又能不刺傷彼此的位置,才能真正停下來歇息。
我們和我們的父母,是否也正在調整彼此的位置和距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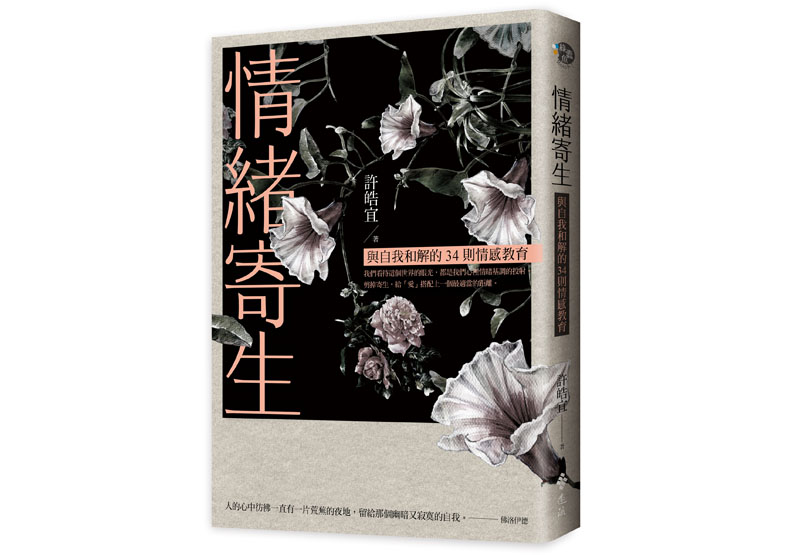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情緒寄生:與自我和解的34則情感教育》一書,許皓宜著,遠流出版。
本文節錄自:《情緒寄生:與自我和解的34則情感教育》一書,許皓宜著,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