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臺北市中山女高國文科張輝誠老師多年來觀察、歸納得出的「學思達」教育方式,以及二○一六年底的「學思達亞洲年會」,讓臺灣瞬間變成華人教育圈的矚目焦點,成為亞洲教育改革的領頭羊。這股由臺灣教育圈率先開啟的分享風,自從輝誠老師開放教室觀課以來,已有愈來愈多教師紛紛敞開雙臂,以正面態度迎向這股學習浪潮。從文史科到數理科,再到藝文科,學思達正以百變女郎之姿進入教室,促成一場史無前例的教育翻轉。
那麼,學思達到底是什麼?
何謂學思達?
從八股文的科舉考試制度開始,華人圈從來不缺乏痛苦的填鴨式教育,但隨著歷史轉輪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儘管傳統方式早已落伍,家長、學生、教師三方卻無法同時放手、做出調整,即使眾人大聲疾呼,這幾年教育現場仍無多大改變。
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視為「解方」的,正是學思達。
學思達常常以有趣的提問來引起學生動機,課程內容則仰賴三大關鍵:「知識點拆解」、「學思達講義」與「課堂經營」,就讓我們以實例來說明。
任何知識都能「拆」
新北市中和國中的孫菊君老師教的是常被忽略的美術課,目前國中美術科大致上是國一打基本功、國二觸類旁通、國三進行議題討論。以國一的「素描」為例,很多本身是練家子的美術老師在基本講解與示範以後,就讓學生連續畫上好幾個星期。但往往會畫的孩子就是會畫,不會畫的還是不會。
菊君老師決定改變這種現況,將素描拆解為「如何觀察」、「如何產生輪廓線」、「如何正確透視」、「光影」、「明暗調子」、「立體感」與「空間」,每一主題都採用讓學生分組自學、互相討論並幫助彼此的方式來學習,進入下一個階段前,她也會確定整組學生都嘗試畫出最基本的要求。
有人或許會問:「學生沒有藝術天分,為什麼還要學這些?」菊君老師認為,這種說法把藝術看得太扁、太狹隘了。為什麼臺灣的城市很醜?原因就出在美學教育並未落實。她覺得每個孩子都有潛力,或許一位不太有藝術天分的學生,長大後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或政府領導人,美學教育有可能讓他成為藝術的消費者或支持者,我們也才有可能共同製造出美的事物、讓臺灣變得更美麗。
為了體現這個概念,菊君老師為打完底子的國二學生帶進「視覺資訊圖表」 (infographic)課程。她相信每一位學生都學得會「萬物基本型」,也都能利用它來創作。這些圖文搭配、畫面平衡的概念,在他們長大、出社會以後,也會對企業簡報甚至是店面擺設有所助益。
面對擁有更深層思考能力的國三學生,菊君老師則帶入性別、反戰等議題,這些需要討論以後才能進行創作的課程內容,使用學思達教學法更是相得益彰。看著孩子們一雙雙發亮的眼睛,也讓她更加相信,藝術可以改變世界。
看見教師實力的講義
在學思達裡,講義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講義是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關鍵所在,只有當學生覺得有趣又有挑戰性時,由內而生的自學第一步才會隨之開啟。許多學思達老師都提過編講義到三更半夜的往事,因為除了以課本為本,還得蒐集無數書籍、資料,才能將內容改寫與整理成具邏輯性、符合學生閱讀程度的講義。
講義裡一定會搭配精心挑選或設計過的題目,學生則會以類似「學習共同體」 的方式分組(四人為一組,每組皆有學習程度不一的學生),在講義與題目的引導之下,彼此激盪思考,完成自學第二步。
以臺東高中化學科羅勝吉老師的課堂為例,學生在他精心設計的講義引導下,很自動地在讀完講義以後,針對其中一、兩個引導式問題,拿起課本尋找答案—所謂的「自學」正是如此。他更表示,講義的功用就像在學生心裡搭鷹架,除了單向地由教師一磚一瓦興築,更需要透過提出一個個好問題,勾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一同加入構築的過程。
在勝吉老師的設計裡,講義內的「好問題」包含了吸引式問題、主要問題與具體問題這三種,分別發揮「吸引學生注意、引起學習動機」、「帶著學生探究『大概念』」、「知識的建構」的功用。講義裡還要提供充足的資訊,讓學生得以在教室內就能自學,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也可在自學時間結束後,與同組同學討論、共同找答案。
最後一步,學生會以隨機方式上臺分享「表達」。今日的學思達已經發展出海螺計分法、撲克牌計分法,帶入競賽的概念,以鼓勵學習效果佳的孩子主動教導同組的同學,因為「學生教學生」的效果往往比老師教學生更好。這些方式也都已經過實驗證實,的確能讓孩子們學得更好。此時,教師的角色早已從授課的主角變成了負責引導的配角,將學習的權力交還給學生。
如此一整堂課下來,教師將透過觀察學生撰寫講義的答案、學生起身講解、師生彼此間的問答,確認學生們的學習狀況,最終進入統整階段,完善整個單元的學習。
勝吉老師說,學生一旦適應了學思達的自學節奏,在閱讀比聽講更有效率之下, 學得其實更快,這也非常符合新課綱在考題上以「大量閱讀」為出發的理念,希望能改善過去學生一看到題目就反射性作答的考試機器現象。而勝吉老師的一大目標,就是讓孩子明明在學習、準備考試,卻以為自己在玩。
不同科的教師於班上實驗一段時間後同樣證明,去蕪存菁的講義不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思考能力,也讓成績有所提升。或許,正是這種不迴避考試,但嘗試隱身考試壓力的方式,讓學思達能被普遍遭到分數綁架的亞洲國家教師們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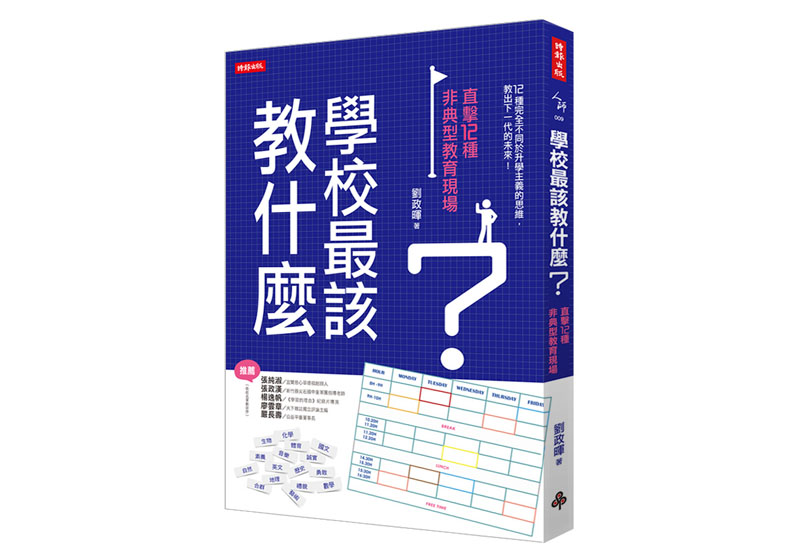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學校最該教什麼?直擊12種非典型教育現場》一書,劉政暉著,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