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來臨?
上帝怎麼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的子民身上?這是每當燃燒的灰煙刺痛我們雙眼、嗆住喉嚨時,我們一直在問的問題。對於我們立下的約,對於我們終將戰勝那些試圖滅絕我們的人的「應許」,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尋找答案,從來也沒有停止過。翻開那些精美的印刷品!有一點關於義人的文字嗎?這樣的情況不是一直在延續嗎?犯罪!邪惡!相互仇恨、自我毀滅,這就是現實!是該做一次全面清理的時候了!你沒有聽過先知的預言嗎?別說無人警告過你。我們在此重申,吾輩為人;但嚴格說來,我們在歷史上是否真的不曾走上邪路,一直恪守禁食律法和安息日習俗呢?看一看大衛和他那聲色犬馬的宮廷,看一看所羅門和他那妻妾成群的虛榮吧。他們可沒被踩在屍堆裡,不是嗎?讓我們先喘口氣,好嗎?喂—那些在安息日肩負背袋四處流浪的同胞們,歇歇腳,來點不分趾、不反芻的動物肉怎麼樣?耶路撒冷焚毀了,很多人被燒死了?你說的這是實話嗎?能不能再說一遍?
如此這般的問題,是問不完的。若耶和華是一切,特別是猶太歷史的主人,怎麼總是有這麼多的麻煩(tsurus)呢?
第二聖殿時期及其被焚毀時的猶太人,對這些問題的確有個答案。該答案是非正統、非權威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聖經》經文,但也不是由一些不相關的怪人所創作的。我們從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五年間在昆蘭洞穴中發現的八百五十件奇異手稿中找到了這個答案。這些手稿包括十五件不同的《禧年書》抄本殘片、七件《以諾書》(即《創世記》偽典,對猶太人﹝在創世時﹞如何與何時接受《律法書》作了完全不同的記述)抄本殘片,以及其他許多與《聖經》完全一 致或略有不同的經文殘片。在這些書卷中,除了《以斯帖記》和《尼希米記》(鑒於《尼希米記》對於《妥拉》歷史記述的極端重要性,其缺失讓人感到更加奇怪),幾乎包括了《希伯來聖經》正典中的所有書卷。其中發現的《以賽亞書》堪稱完本,同時還發現大量的《以賽亞書》、《詩篇》和《申命記》抄本,這或許是為了表明這幾部書對當地「社團」來說是最重要的。這些書卷大部分用希伯來文寫成,有一部《約伯記》附有亞蘭譯文(targum),而《哈巴谷書》和《以賽亞書》等書卷還附有評注(pesharim)。在這些希伯來文書卷中,有些與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和幾乎一千年後由拉比,西元九世紀末發布的《馬所拉文本》(補加了注音)有明顯的差異。
事實證明,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發現的「昆蘭古卷」中,還包括許多所謂的《次經》:《多俾亞書》、《便西拉智訓》、《友弟德傳》,以及兩篇激動人心的歷史記述,即兩卷《馬加比書》、《塞拉赫》,當地社團禁欲苦修生活中的日常遵守的《生活規則》、《感恩聖歌》和《讚美詩》的連禱詞全文。最引人注目的是還有一些《聖經》經文,大多寫於西元前三世紀和前二世紀。在它們於荒漠洞穴裡被發現之前,人們只是聽說(知道的人並不多)有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發現的用「猶太—衣索比亞」音節語言(Ge’ez)寫成的衣索比亞手稿中有這類經文(靠音節本身連接成句是非常令人驚異的)。這些早出五百年的希伯來經文的發現,完全改變了我們的故事脈絡,因為這樣的思路無法與當前有關東非一神教的敘事相吻合,而只能追溯到猶太教形成的本土。正是在這些深奧難解但又引人入勝的書卷中,似乎可以找到「世界上是否存在邪惡」這個問題的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從文學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答案:你沉浸在一個猶太故事中,但這故事似乎更接近其他古老的異邦宗教,更接近具有波斯拜火教特色的善良與邪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二元戰爭,更像是一個諾斯底(Gnostic)(註一)文本。如果這樣的文本大量地流傳下來(沒有理由認為只有少量存世),那麼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拉比們將其從虛構的「偽經」記憶中刪除。因為從表面上來看,要說猶太人曾經同時讀過(更不用說曾經相信)以「立約」為主體的《聖經》中具有權威性的故事和《禧年書》、《以諾一書》(包括《看守天使書》、《巨人書》)以及《創世記》偽典,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這些另類的經文中,唯一的上帝在天空中並不孤獨,他身邊圍繞著一群天使,但祂又不能完全控制祂們。這些天使中有好天使,聽從《聖經》中提到的米迦勒(Michael)指揮;也有敢於違抗上帝命令的壞天使,只服從彼列(Belial)的調遣。彼列的名字在這些書卷中比比皆是,例如,在一首文學非常優美的偽經《感恩聖歌》中就提到:「至於我,我的嘴不能說話,(我的胳膊)被撕了下來,我的腳深陷泥潭。我的眼被魔鬼的異象弄瞎了,我的耳被血腥的哭喊聲震聾了。我的心,被這些惡作劇弄亂了,因為彼列露出了他(邪惡的)面孔。」因為這些壞天使公然抗命(尤其是他們不能接受被造的人以上帝的模樣出現),他們被逐出天庭,作為「天空之子」—在《以諾一書》中作為更不吉祥的「看守天使」—被遣送到凡間。他們在凡間與女性人類結合,生下了許多畸形巨人,即拿非利人(Nephilim)。這群惡魔在大地上橫行無忌,上帝卻賭氣地躲在由一群光明天使簇擁的豪華天庭裡,任其自生自滅。以諾是第一個會說話的人,他從大地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親眼目睹了恐怖和災難,報告說邪惡正在大地上肆虐。於是上帝用洪水消滅了巨人,但惡魔的靈魂卻逃脫了。這些惡靈仍受追擊,但與上帝對抗的惡魔首領莫斯提馬(Mastema)(註二)卻成功地說服上帝,只把十分之九的惡靈打入了地獄。被釋放的十分之一惡靈,足以在大地上製造更多的禍患和痛苦。
不同於《聖經》經文的另類記載還有很多,在《創世記次經》中尤其如此。其中不僅說以色列人是在創世時接受了耶和華的約,而且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雅歌》描寫她容易興奮―如此勾起一位埃及法老的欲望,以至於被他拐跑了,並給他當了兩年的妻子。亞伯拉罕之所以能夠逃過一劫,是因為他聲稱她是他的妹妹。
不僅如此,這些書卷還演繹出了一些奇異而怪誕的秘聞軼事。瑪土撒拉(Methuselah)的兒子拉麥(Lamech)懷疑他的一個兒子實際上不是他的後代。奇怪的是,這並不是因為他在一百八十二歲的壯年才有了這個兒子,而是因為他擔心他的妻子巴特以諾(Bathenosh)可能是與一個看守天使,即邪惡的「天空之子」有染而受孕。「她非常動情地哭著對我說:『噢,我的主……還記得做愛時那飄飄欲仙的感覺和我熾烈的反應吧?』」實際上這是在向他保證,他們夫妻之間的性高潮,確保了那個長大後叫挪亞的種確實是他本人的。但拉麥仍然不信,甚至還跑到年邁的瑪土撒拉那裡去求證。
「天空之子」竄入《聖經》敘事而弄亂情節。他們的王子和首領莫斯提馬策劃了用以撒獻祭的陰謀,得到了上帝認可,而摩西則從一群代表上帝的天使那裡(再一次)接受了律法。這就使人產生了這樣的印象,不是上帝主動放棄了他的創世權,而是經過一代又一代人之後,善良和邪惡力量一直在爭奪他的最高統治權。因此,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在預示著「世界末日」(令人驚異的是,此卷在所發現的羊皮卷中篇幅最長,仔細計算的羊皮紙長度竟達二十八英尺,堪比《荷馬史詩》)到來的最後決戰中,光明之子必將戰勝「黑暗之子」。「到基提人(即羅馬人)敗亡的那一天,在以色列人的上帝面前將發生混戰和恐怖的屠殺,因為這是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確定的毀滅『黑暗之子』的日子。」但這場混戰竟持續了三十三年!
這些有關猶太人及其世界的另類故事的作者和讀者多離奇古怪。顯然,這些羊皮書卷上的文字完全自《聖經》正典中消失,而其發現只不過是一個偶然的奇蹟。關於「昆蘭古卷」,學者之間的論戰一直在持續著。一方以吉撒.韋爾梅斯(Geza Vermes)為代表,他一直認為,昆蘭團體是道道地地的艾賽尼派;而另一方的代表人物諾曼.科布(Norman Golb)則認為,這批手稿內容的多樣性和宏大規模表明,他們在匆忙之中把豐富的耶路撒冷圖書館藏書從被圍的城裡搬了過來。儘管我一直不同意科布的觀點,但他的說法實際上也不是捕風捉影。昆蘭距離西面的耶路撒冷只有三十五英里,在南面的馬察達要塞被占領之後,這一地區基本上在奮銳黨控制之下。人們普遍認為,在長達數代人的時間裡,昆蘭一直被這個奉行禁欲主義的「團體」占據。所以,從外部帶進來這些「死海古卷」的可能性是有的。因為這些書卷形式多樣、構成複雜(畢竟是不同的作者,甚至不同的文字寫成),其中既有艾賽尼派的日常生活準則和條例,也有《聖經》正典的各種抄本,還有一些屬於《次經》、《偽經》以及其他神秘的經文。
對於有關這些書卷所要求的猶太虔誠的猜測,真正令人激動的判斷並不在於這些書卷是艾賽尼派的作品,還是從耶路撒冷搬過來的一批更豐富的藏品,而在於如下的事實:這些猶太人,是把關於其祖先故事的兩種尖銳對立的版本(既有權威的也有非權威的,既有嚴格的一神論也有神秘的二元論)放在一起閱讀的。有些書卷(如<聖殿卷>)不僅重新改寫了《委拉》中關於獻祭和潔清的條例,而且增加了更新版的規則。例如,無論是壁虎、沙虎還是「大蜥蜴」、變色龍,一概不能食用。這部書卷甚至還構想了一座規模更宏大、裝飾更豪華的聖殿。這些來源於《妥拉》和非《委拉》經文的融合形式,從而開始了一個可能性,使猶太人的學習和虔誠比後來的《聖經》正典和《塔木德》所容許的,在形式上更多樣、組織上更鬆散、調適上更自由、更具神話風格、更受神秘動機驅動、以及更具日光傾向。猶太文化元素也都回來了,比如神話傳說中的荒涼海岸、古代後期的咒語巫術(根據同時出土的數千個巴比倫咒術碗可以推斷),從邊緣的神秘知識到主流的猶太宗教實踐和故事,一應俱全。
有些書卷囉唆得使人昏昏欲睡,有時也令人抓狂。例如,<戰爭卷>作為反抗羅馬人的軍事手冊,其實並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其中只是許多的篇幅詳細而精確地,描述了在光明之子的作戰陣列中的號角、旗幟,甚至武器上必須刻什麼內容。「在他們的長矛尖上,他們要寫上『上帝力量的長矛光輝閃耀』……在第二梯隊的標槍上,他們要寫上『上帝震怒,槍頭帶血,染紅敵人的屍體』。」我們還要為敵人寫投降書!敵人不會是向我們的囉唆投降吧!他們精細地制定了拋光的銅盾牌尺寸,而長矛頭「要由一個工藝匠人用錚亮的白鐵打成,在正中間,要用純金做上兩枝穀穗指向矛尖」。如果「最後決戰」的勝負僅僅是由「文字」武器的豪華程度來決定的話,那麼對光明之子來說就太輕鬆了。
戰場上從來不會有這樣輕鬆的事。但「戰爭卷」中記載的「拿起武器」這種激動人心的召喚及其戰無不勝的必勝信念,事實上卻是一種共同的文化。只不過死海岸邊的這個分離主義者團體,表現得更為強烈而已。因為在當時,即使像提多那樣的全面滅絕行動也被認為不過是「萬軍之耶和華」及其立約子民的最後勝利的序曲罷了。希望永遠不會破滅,自由(這個詞就鑄在下一代起義軍的硬幣上)將隨著彌賽亞的降臨很快到來,聖殿將再次得以重建。「萬軍之耶和華」將縱馬行空,衛護他的子民。但在結束之前,一切仍在繼續。
在短短的六十年裡,發生了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猶太人揭竿而起反抗羅馬人的起義。這兩次起義震驚了整個帝國,派出大量軍隊進行鎮壓。更令人難以忘記的是發生於西元一一五年至一一七年圖拉真(Trajan)統治時期的第一次起義。這次起義的戰火燃遍了地中海沿岸的猶太人散居點,從昔蘭尼加開始,席捲埃及,在亞歷山大達到高潮(這個偉大的猶太社區也因此而滅絕),甚至還波及敘利亞城市安提阿和大馬士革。這次起義,我們只能相信約瑟福斯當時寫下的文字。但這次起義中的某些觀念,存在非正統的「昆蘭古卷」中,這些起義者似乎擁有某些散播彌賽亞式狂熱的訊息。他們熾烈地相信,末日即將來臨,光明之子終將戰勝黑暗之子,救世主上帝將在廣袤的戰場上為他的子孫而戰鬥。當然,我們是從像卡西烏斯.狄奧和狄奧多羅斯.西庫魯斯(Diodorus Siculus)這樣的羅馬人的記述中,才知道這次暴動的規模、武力的殘酷和屠殺的恐怖,以及當時羅馬人對這些猶太城市燒殺搶掠的場面,因為提多對耶路撒冷的所作所為也是如此。
你吃驚也好,不吃驚也罷,西元七○年的戰爭創傷之後,當他們的兄弟姊妹正在利比亞、埃及和敘利亞遭到屠殺時,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一直沒有行動。但是在西元一三二年前後,猶太地曾爆發了一場大起義。根據卡西烏斯.狄奧的記載,這場起義曾迫使羅馬人動用了五萬人的軍隊,花了三年時間進行鎮壓。誇張點來說,這次起義的規模無疑使羅馬人大吃一驚。當事態似乎難以控制時,皇帝哈德良(Hadrian)還一度御駕親征,而演說家弗朗托(Fronto)曾經將這場第二次猶太戰爭與和羅馬人在北不列顛人潮濕多霧的北方進行的漫長、艱難的戰爭相提並論。
就連約瑟福斯也不知道這次起義的大概情況,他既沒有提到其如何發生,也沒有寫出直接原因。儘管幾乎可以肯定,哈德良在耶路撒冷破壞最嚴重的廢墟上建造了一座被他稱為愛利亞卡彼托利納(Aelia Capitolina)(註三)的新城是一次最大的挑釁行動。雖然曾經有人認為,這是結果而不是原因,但西元一三○至一三一年發行的鑄幣上,用這個新的羅馬名字取代了被焚毀的耶路撒冷,這個事實充分表明這的確是一個主要原因。這次起義的領袖西門.巴.科西巴(Simon bar Kosiba)自詡為彌賽亞,也就是「昆蘭古卷」中記載的彌賽亞強烈渴望(更不用說當時剛剛興起了一個真正的彌賽亞基督宗教)。這種期待讓巴.科西巴的宣稱發揮影響力,尤其吸引像拉比阿奇巴(Akiba)這樣的法利賽人投入反抗大業,成為繼西門之後最著名的殉難者。
正是拉比阿奇巴借用了《民數記》(24:17)的預言:「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並賦予起義軍領袖一個更適合彌賽亞的亞蘭名字「西門.巴.科赫巴(Kochba),意為『星之子』」,從而使起義軍成為正義之師。但巴.科赫巴也自稱﹁納西﹂(nasi),意為王子,以便迎合人們對彌賽亞的預言和渴望―與哈斯蒙尼家族完全不同―一位真正的猶太人救世主必須是大衛家族的後裔(據說拿撒勒人耶穌也是如此)。他是一個恪守安息日習俗的猶太人,並且把自己當作這個神聖民族的新一代大衛家族的領袖。儘管二十世紀六○年代曾在猶大沙漠的洞穴裡發現了一批起義軍領袖的來往書信,但相對於反抗羅馬人的第一次戰爭,我們對這次起義的進程所知甚少。從這些信件可以看出,他實際上是一個冷酷的游擊隊首領,擁有完備的指揮系統,他把占領的領土劃分為七個指揮區,而每個區又細分為一些小行政區,並逐級收稅資助起義軍。比純粹的山寨起義更具有革命性的是,他在實施必要的懲罰時表現得冷酷無情,因為若不如此,他將很難堅持下來。他親自簽署一些簡短、直接而措辭強硬的信件,用語簡潔有力,從而給人一種強烈的神賜魅力感,兩千年後我們仍然有所感。但是,他在硬幣上鑄的銘文「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願望,因為從這批硬幣的發行範圍來看,他顯然從來沒有進過這座城市。然而,與兩代人之前發生的那場偉大戰爭相比,這次起義更多地顯示出一種為「猶太自由」(這個目的也鑄在硬幣上)而戰的意識。顯然,這次發行的硬幣是對提多曾經鑄造的著名羅馬幣,幣面上有位被遺棄在一棵棕櫚樹下哭泣的「猶地亞卡普塔」(Judaea Capta)(註四)所做的挑釁回應。
眼淚仍然在繼續流淌。巴.科赫巴起義的鼎盛期是西元一三三年前後, 但也只不過占領了猶大地和撒瑪利亞,而他的首府就設在比塔爾(Betar)要塞。耶路撒冷和加利利似乎仍受控於羅馬人。最後,羅馬人明智地打起了消耗戰,成功地將起義軍逼回了死海岸邊那些荒涼的山洞裡,而上面提到的書信,正是在這裡發現的。在最後的歲月裡,起義軍食物和物資緊缺,越來越陷入絕望的境地(那些信件就是在這幾年寫下的),直至西元一三五年不知所終。隨著起義軍的滅亡,猶大地也重新落入羅馬人手中,哈德良在去世之前,將其命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省」(Syria Palestina)。
即使你不是約哈南.本.撒該的門徒,難道就能完全迴避這段歷史嗎?在猶大地沙漠地區的一個山洞裡發現了三十具遺骸,在他們中間,人們找到了一封信。可以想像,在箭如飛蝗的戰場上,或許這寫信的人當時就只是想寫一封信,也或許只是為了記錄買賣上的一點什麼。她的名字叫巴巴塔(Babatha),來自約旦河對岸、死海東南角上的納巴提亞(Nabatea),距離玫瑰紅色的偉大城市佩特拉(Petra)不遠的,一個叫莫耶撒(Maorza)的小村莊。從種族上看,巴巴塔是以土買人,但這個民族早在兩個多世紀前就皈依了猶太教,當她為第一任丈夫生下兒子時,這個兒子就在羅馬人的律法文書中被特別地認定為猶太人。
對她來說,棗椰樹就是她的全部世界,也是她的全部財富。正如每個在這地方吃過這種果實的人能夠告訴你的那樣,這種果實的新鮮多汁、甘甜如蜜,是其他水果比不上的美味。看著她的信,你就此進入死海邊的過往時光。巴巴塔從她父親那裡繼承了一個小棗椰園,當她和第一任丈夫耶穌(耶穌之名如此普遍!)結婚後,她的棗椰園便不斷擴大。西元一二四年,她成了寡婦;一二五年,她和另一個叫猶達尼斯(Judanes)的果農再婚,但猶達尼斯已經有一個妻子,名叫米利暗(Miriam),而且他們還有個女兒,名字相當美麗,叫撒羅姆澤恩(Shelamzion)。《妥拉》律法禁止一夫多妻,但由於猶達尼斯在死海西岸的隱基底(Ein Gedi)還有一處棗椰園(巴巴塔有時也住在這個地方),所以猶達尼斯完全有可能在兩個地方成家立業。
無論如何,巴巴塔都完全能夠自己養活自己。西元一二八年, 她慷慨地借給她的丈夫三百個銀幣(denarii),以便他能為自己的女兒撒羅姆澤恩出嫁準備像樣的嫁妝,但條件是只要她願意,她可以隨時要求歸還這筆錢。當猶達尼斯去世後,由於巴巴塔擔心在要求還錢時可能會有麻煩,於是便趕快占據了隱基底的棗椰園作為抵押品。這讓他的第一個妻子米利暗很不高興。她到羅馬法庭起訴要求歸還原主,並且她還有一張王牌:她通過一個時任起義軍隱基底要塞指揮官,叫耶赫納塔(Yehonatan)的親戚或朋友,與巴.科赫巴的新起義軍建立了聯繫。
隨著巴巴塔和她拼命積累並且僥倖保留下來的財富慘遭厄運,歷史似乎也突然終止了。她毅然離開老家趕往隱基底,準備出庭為自己辯護,但在途中卻遭遇了一場猛烈的沙塵暴。為躲避羅馬人,巴巴塔跑進了納里耳赫貝耳(Nahal Hever)的山洞裡(羅馬士兵就坐在洞口上面的懸崖上)。她非常清楚,就算命中注定這是一個悲慘的結局,那她抓住這一紙律法文書仍然有用。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使她僥倖活下來,那麼這張文書將使她作為那片寶貴的棗椰園的女主人,行使自己的權利。然而,某個「天空之子」捉弄了她的命運,她死在那裡,與那些來自隱基底的富有的猶太人,一起倒在了他們的鏡子、梳子和小小的黑色油膏罐中間。
關於巴.科赫巴起義這猶太人反抗情緒的最後爆發,遺留可講的資料實在不多,僅剩那些硬幣可說上一說。儘管它們大多面值不高,但古幣研究者仍然熱心收藏,有些人甚至還趨之若鶩。這些錢幣通常帶有一種哀婉的美,因為它們代表著某些曾失落之物:特別是那帶柱廊的聖殿,還有猶太人每逢住棚節帶進聖殿的四樣植物枝葉。在其中一枚銀幣上,鑄造的圖案融合了聖殿的記憶、彌賽亞的救贖和為追求解放向全世界喊出的第一句革命口號。在曾於城牆上吹響的號角周圍,環繞著這樣一句刻意用古希伯來字符寫成、與《聖經》第一次成書相聯繫的口號:「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其他硬幣的正面都刻著棗椰樹(tamar),寓意「多枝燭臺」,這是猶太意象中使用最多的標誌物之一。棗椰樹代表著上帝對與他立約的子民應許的豐饒,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
棗椰樹還有另一種象徵意義。對於埃及人及其後繼文化來說,棗椰樹是一種永遠不會枯朽、不斷發出新芽的樹,新葉取代那些已經枯萎的老葉,老葉在飄落之前一直頑強地掛在樹幹上。如有可能,你可以親自去看一看,這種樹在以色列和埃及隨處可見。至少從這種意義上說,棗椰樹是不朽的,因而成為救贖和復活的象徵。這也正是受祭司環繞,虔誠「假彌賽亞」西門選擇棗椰樹作為硬幣圖案的另一個原因。
另一群彌賽亞信徒也是這麼想的,他們對復活情有獨鍾。這也是為什麼,當基督教的十字架圖象首次出現時,用的是棗椰樹的圖案。
註一:又稱靈知派。指的是在不同團體、宗教中有同一信念,此信念源自史前時代,後來傳播至各地。
註二:又作「Mansemat」,希伯來文意為「惡意」。在《尤倍書》偽典中,他是看守天使首領之一,最初和彼列一同來到凡間,曾因對凡人女子有所留戀而受到懲罰。在挪亞洪水時期,統領留在大地中被洪水滅絕的惡靈。當年上帝要將墮天使丟入地獄時,他向上帝求情,上帝才留下了十分之一的墮天使在凡間,從而為凡間帶來了誘惑、告發、刑罰等罪過。傳說當時在埃及和摩西鬥法的魔術師就是繼承了他的魔力。
註三:「Aelia」指哈德良治下的非猶太省,源於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語舊稱「Illya’」,而「Capitolina」意為「獻給主神朱比特」。西元一三○年,羅馬皇帝決定在被羅馬人於七○年焚毀的聖殿原址上開建這座新城,並且朱比特神殿就建在原猶太聖殿的正前面,這一舉動被認為是巴.科赫巴起義的主要誘因。
註四:「猶地亞卡普塔」是羅馬皇帝維斯巴辛在他的兒子提多在第一次猶太戰爭中攻陷耶路撒冷並焚毀聖殿後發行的紀念幣,分金、銀、銅三類,共四十八種。其中有一枚硬幣的反面刻有一個女人坐在一棵棕櫚樹下哭泣的圖案,周圍的文字是「IVDEACAPTA」,意為「征服猶地亞」。故這批出土的硬幣在考古史上被稱為「猶地亞卡普塔硬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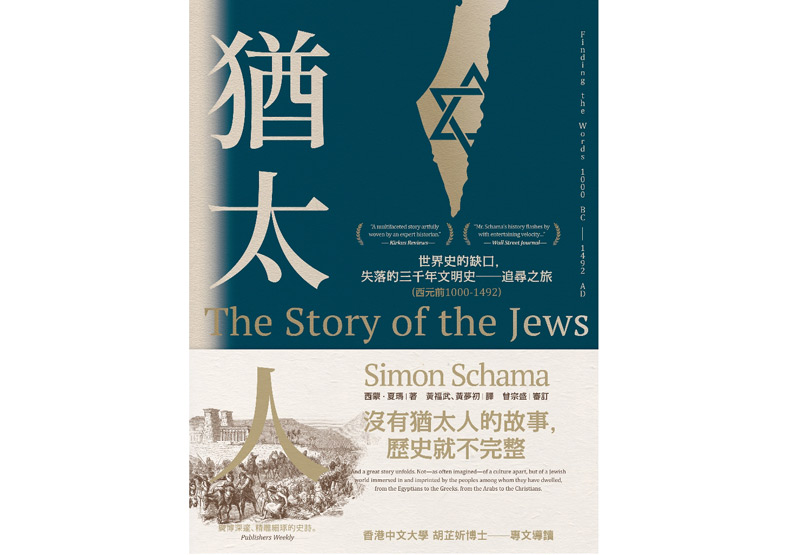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猶太人》一書,西蒙‧夏瑪(Simon Schama)著,黃福武、黃夢初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