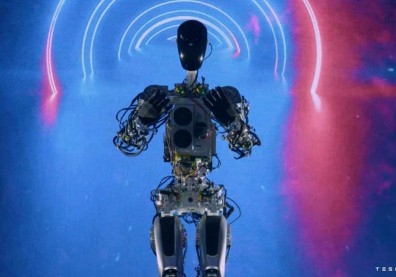每年暑假,是學校「招兵買馬」、補足教學人力的時候,但近年有意從事教職者卻持續滑落,「師培生跳船潮」掀起輿論對台灣教育體系的憂慮。由於職涯沒有保障,近七成儲備教師選擇不走上講台,但深挖下去,數據顯示出來的是台灣合格教師早已「供過於求」,整個師培系統,已到了轉型的關鍵十字路口。
相關數據指出,全台每年有數千人取得教師證,卻沒有足夠的教職崗位供應,具備資格和能力的教師,成為了現實中的「流浪教師」,教職不再是民眾眼中的高社經地位職業。即便順利「上岸」,新的考驗接著湧現,薪資待遇不足、行政兼職繁重、學生家長的壓力與投訴……,腹背受敵,基層教職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拉鋸,也在教室與制度的夾縫中掙扎。
教師證取得穩定,任教率卻逐年下滑
教育部資料顯示,民國102年自112年,每年取得教師證的人數約在4000至5700人之間,其中108年達到高峰(5729人),而近三年則維持在4600至4900人左右;以112年為例,僅4852人取得教師證,
同樣以112年為例,在取得教師證的人當中,任教率(即實際進入學校任教的比例)從102年的近七成,10年內下滑超過10個百分點,一路下滑至112年的60.1%,創下十年最低。顯示即使證照取得穩定,進入校園任教的意願與實際機會卻逐年減少。
師資培育核定數高,卻面臨「培而未用」困境?
觀察「師資培育核定名額」,即「具備教師資格者」的人數,近十年則維持高檔,109學年度更突破萬人,儘管隨後兩年人數略減,但112學年度仍有9,119人獲得教師資格,仍比十年前的8千餘人多。當核定數維持高檔,教師任教率卻持續下滑,顯示台灣的師資體系,正面臨嚴重的「培而未用」問題。
少子化浪潮,持證卻難上岸
民眾黨立委劉書彬觀察,師資「供過於求」的問題並非新現象,數據顯示,台灣的流浪教師「存量」早已非常高。累積自民國83年至今,全台共有22萬6194人領有教師資格證,但實際任教率僅66.99%,換算下來,約1/3、逾7萬人就是所謂的「流浪教師」。她指出,這些人明明有拿到教師證,但苦於某些原因無法成為正職,「對於有志者是挺傷心且打擊很大。」
具教師資格者的人數持續增加,但未來生源卻不斷下滑。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國小一入學生,112年約19萬多人,但5年後的117年,就銳減至14萬7302人,少了約1/4、5萬人,勢必將對教育體系產生長期衝擊。
這樣的結果,便是學校對教師的需求同步萎縮,即便有教師退休或離職(出缺),學校也會選擇「遇缺不補」,不再補足這些正式教師的職位,近一步加劇「培而未用」困境。
由於正式教師職位被凍結或不予補足,但學校仍有教學人力需求,學校被迫轉而大量聘用「代理教師」來填補空缺,這種情況使得代理教師的比例居高不下。數據顯示,民國112年,光是公立學校代理教師比例約為12.13%,而這還沒算上私立學校的狀況,職涯沒保障,成為師培生跳船潮表象。
偏遠地區教師荒,誘因低為關鍵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表示,儘管數據顯示教師儲備量充足,但實際教育現場的感受,卻是嚴重的人力不足。他強調,會產生這種矛盾,原因在於這些帳面上的儲備教師不一定願意真正投入教職;即使願意投入,也常受限於地理區位考量,例如偏好在住家附近工作,導致偏鄉或特定地區的師資更加稀缺。特別是代理教師,由於職涯保障差,更加不願意跨區域至偏遠地區任教。
其實為了平衡都市與偏鄉間的教育資源,政府目前已有相關政策資助公費生,要求這些「準教師」取得資格後,必須最少在偏鄉等地區服務6年。但數據顯示,儘管政策立意良善,但誘因不足,這些公費生在期滿後往往就離開偏鄉,導致偏鄉地區的教職人力流動率過高。
劉書彬就批評,公費制度派任制度僵化、缺乏配套,「這樣的綁約設計,沒有考量個人意願,也沒有宿舍或交通補貼,人到了現場還得身兼多職,一旦有機會,當然會想離開。」
侯俊良表示,面臨行政工作量增加、濫訴變多、職業尊榮感下降,以及潛在的投訴風險等問題,這些因素共同營造了不佳的工作環境,使得許多老師,包括年長的退休教師和因環境不佳而離職的教師,加速了人才流失。
宏觀數據顯示,台灣教師供過於求狀況嚴重,不僅存量高,每年增量也超高,顯示整體師培系統已到轉型關鍵點;而從微觀層面,教職現場待遇不佳,加劇師培生的跳船潮,雙重壓力,讓台灣教育體系緊鈴大響,亟待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