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需單單一次受到他們注意,我們就能期待抓住他們的心和靈魂。」
艾立克.史密特
谷歌執行董事長
二○一一年六月
洛思阿圖斯(Los Altos)是加州數一數二最富裕的地方。這個有谷歌總部坐落於其高處山景城的上流住宅市鎮,擁有種滿巨杉與杏樹的寬闊道路,還有一間無法上網的學校。四分之三的學生家長都是谷歌、雅虎、蘋果或是惠普的員工。在矽谷的這處核心地帶,在大數據的地盤上,華德福(Waldorf)學校當局不准校內四年級以下的學童碰觸智慧型手機、iPad或是電腦螢幕。數位界那些善於思考的人小心翼翼保護自己的後代,不讓他們接觸自己為別人小孩設計出來的產品。就舉推特的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為例,與其送給自己的小孩iPad,他寧可為他們購買幾百本紙本書籍。在蘋果創辦人史蒂夫.賈伯斯家裡,當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的時候,絕對不能拿出iPhone或是iPad。為蘋果前任老闆撰寫傳記的作家在《紐約時報》上披露:「每天晚上,史蒂夫要求一家人在廚房的大桌前用餐,並且談論書籍、歷史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話題。從來不曾有人拿出iPad或電腦。孩子們看起來都沒有依賴這類設備的樣子。」最近,兒童精神科醫師、兒科醫師、心理學家、教師與正音科醫師藉諸報端聯合呼籲大眾「讓小孩遠離平板電腦」。他們比較那些經常上網與不常上網的小孩之後,列舉一系列不良的影響。當平板電腦成為刺激作用的主要工具,它會「令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惡化、造成語言發展遲緩、妨礙因果原理與時間觀念的建立、損害運動機能發展、阻礙社會化的進程」。科學研究指出:長時間暴露於螢幕之前會對認知功能的發展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法國國家健康暨醫學研究院(Inserm)神經科學部研究主任米歇爾.戴穆赫傑(Michel Desmurget)也證實了這一點。
研究人員的憂慮並未阻止一心想要擴張蘋果勢力的史蒂夫.賈伯斯,在自己死前仍不忘責成公司的銷售團隊對小學施壓,以便他們的學生人手一台取代紙本書籍、用以直接閱讀資料的iPad。該公司打的如意算盤是:把學校當作其產品出路的橋頭堡,先讓學童儘早熟悉此一工具,以便未來自己也成為購買者。面對其他平板電腦製造商的競爭,蘋果為坐穩在學校中的地位,也不惜對那神聖不可侵犯的使用規則做出讓步,允許學童在為自己的iPad增加內容時,不需每次都先輸入識別碼。數位電子書的市場是一條驚人的礦脈,因為平板電腦賣出之後還能繼續撈錢。在賣出一億七千萬台iPad之後,蘋果還有豐厚利潤繼續進帳,因為讀者每次下載一本書就得再付費。此外,與閱讀時間相關的資訊也能拿來賣錢。電子書裡其實布滿了會監視你閱讀習慣的軟體。因此,二○一四年十二月,平板電腦Kobo的製造商(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電子書的業者以及法國法雅客的合作對象)在仔細分析二千一百萬用戶的資料庫後宣布:購買作者艾立克.澤穆爾(Eric Zemmour)最新一本書的讀者當中,僅有百分之七點三的人從頭到尾讀完,另外,下載前任法國總統歐蘭德前伴侶瓦萊麗.崔威勒(Valérie Trierweiler)作品的讀者中,有三分之一沒有讀完全書。有關讀者選書與閱讀習慣等方面,大數據公司都取得了寶貴的資訊,並且將其轉賣給想進一步鎖定顧客群的出版商與廣告商。法國兩個主要吃到飽的電子書下載網站,便是因為蒐集與閱讀有關的資料而獲得充分的資金,例如YouBoox就向出版商推薦一個可以登入搜尋其客戶特徵資料的網站。
電子書出現後,不僅令書籍的物質特性消失,並且以繁多的超文本連結使作品「增長」、使它「更豐富」、使它「活力充沛」。但是閱讀活動本身反倒被如此多的聲音、影像以及各種註解等附加元素干擾。大數據公司的目的只有一個:延長客戶們連網的時間,那可是「最能獲利的」時間。沉浸在紙本書籍中的讀者乃是遙不可及的,因為沒連上網,所以無法提供任何資料,也就引不起任何生意上的興趣。美國評論家、《網路讓我們變笨?》一書的作者尼可拉.卡爾(Nicholas Carr)即揭發道:「網路企業最不鼓勵人家慢慢地、悠閒地或是聚精會神地閱讀。他們在商言商,巴不得你漫不經心瀏覽就好了。」數位世界的讀者通常是流連網路成痴的人。他像一隻發了瘋的蜜蜂,自我強迫似的一味採蜜,不停地從此一主題跳到彼一主題。他的想法支離破碎,思考行為有如陣陣痙攣。哲學家羅傑─坡爾.德洛瓦(Roger-Pol Droit)警告道:「你的心思反覆處於連結與斷開的過程,屬性彼此不相干的知識領域時時在此雜沓交疊,而且你離不開螢幕、電子信件與五花八門的誘惑,凡此種種都有可能深刻改變你思考與感覺的方式。」最近有人發現:閱讀電子書和紙本書時,人腦受激化的區域並不相同。這證明電子書對我們思想架構的影響多麼透徹。閱讀電子書的人較不容易接受書中的信息,而且其理解力也會受到影響。加拿大亞伯達大學的研究人員曾做過一個深具啟發性的實驗,他們讓兩組受測對象閱讀同一篇小說,結果閱讀「加料」文本的那組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承認自己跟不上故事的發展,而另外那組只有百分之十的比例。加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派翠西亞.格林費爾德(Patricia Greenfield)是兒童發展議題的專家。她明確指出:網際網路的使用越來越普遍,這將會「弱化我們吸收高深知識、進行歸納以及產生批判力、想像力、反省力的本領」。她並非唯一一位憂心忡忡的科學家。加州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蓋瑞.斯莫勒(Gary Small)警告:「數位科技目前的大爆發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以及溝通方式,而且還讓我們的大腦快速、徹底地變質。」有史以來,從不曾有哪種科技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造成我們感知系統如此大的混亂。
但這正中大數據公司下懷,因為人腦渴求被外界所刺激,所以很容易就淪為獵物。在舊石器時代,「離散」(dispersion)是族群得以延續的條件。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提高警覺能讓遠古人類從環境聲響中察覺危險,進而及早採取措施。這種游移不定的注意力能讓他們盡可能接受最多的警示:一個細微聲響、一股新的氣味或是一個可疑動作。若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固定的目標上太久,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有一項著名的實驗「隱形的黑猩猩」(Gorille invisible)向世人證明了:當我們的大腦專注在唯一一項任務時,它對於周遭其餘東西便視而不見。在該項研究中,科學家要求受試者觀看一支籃球比賽的錄影帶,並請他們精確計算穿白球衣的隊員彼此傳球的次數。在那過程之中,竟有一半受試者沒注意到有一位假扮成黑猩猩的球員大剌剌搥著胸穿越籃球場。
人腦既已習慣以接受數位的刺激為樂,就會不斷要求更多。一如農產食品加工業者知道如何迎合我們嗜食肥膩以及糖、鹽的天性,生產出可以讓我們從超市一車車推走的、多於合理需求的食物,數位企業也懂得利用我們大腦非得毫無節制啄食資訊不可的特性。手機上不斷湧入的資訊誘惑造成不自然的刺激,並使我們喪失自制能力,那是一種數位催眠。我們的注意力經常被一大堆通常是雞毛蒜皮的事吸引住,以致我們再也無法集中精神,就像拼圖遊戲散落的拼板。我們喪失思考與集中注意的能力。麻薩諸塞州塔夫茨(Tufts)大學發展心理學教授瑪麗安娜.伍爾芙(Maryanne Wolf)憂心指出:「我們無法走回頭路,我們回不去數位年代之前的那個年代。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還沒理解自己的『認知庫』(répertoire cognitif)到底因此丟失或是獲得什麼時,便貿然地再往前衝。」深度閱讀的習慣漸漸喪失了。閱讀普魯斯特或是托爾斯泰成為一種自我挑戰,因為這對我們有如蝴蝶東停停西停停的大腦來說,簡直是太艱苦的鍛鍊。賽德希克.畢亞吉尼(Cédric Biagini)所寫的《數位掌控:網際網路以及新科技如何殖民我們的生活》(L’Emprise numérique. Comment Internet et l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ont colonisé nos vies)一書是目前針對大數據公司所創造之世界最成功的批判。他斷言道:「書籍置身網路以及不斷湧來的資訊與誘惑之外,也許是最後幾個反抗根據地其中的一個。」這位評論家解釋:「此刻,紙本書籍更能以其直線性(linéarité)以及有限性(finitude)成為一個擊垮速度崇拜的利器,能讓人類在混亂之中維持協調一致。」如今,人們已不再推敲字詞的深刻涵義,只是留在淺面,像打水漂似的點到為止。網路變成一種將現實加以簡化的機器,簡化對象包括語言在內。原意為「擴音器」的推特(Tweeter)可說是上述毛病最驚人的徵候了:須將思想壓縮在一百四十個字母以下。今天,小學生畢業後,有些人(大部分是上網成痴)只能勉強拿五百個單詞湊合著用。大數據公司那一班操縱木偶的人除了導致語言貧瘠化之外,也不忘縮減語意的多樣性,將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予以簡單化、標準化。扼殺批判精神之後,他們也就不擔心人們對於系統的質疑。
學校本來應是進行思考的無法上網空間,也是個播下批判精神種子的對抗場所,如今卻成了大數據公司的好夥伴。法國教育部長娜嘉.瓦羅─貝爾卡桑(Najat Vallaud-Belkacem)義無反顧地一頭栽進她那所謂「以平板電腦發展數位教育」的計畫裡。在初期三年的階段之中,預計挹注十億歐元於這一場數位的大躍進,讓五年級所有班級配備平板電腦,以便達成「讓法國成為數位教育領頭羊」的目標。教師團體並未出現太多抗議聲浪,因為他們希望能藉此重新吸引課堂上學童較長時間的注意,畢竟這是學習過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像哲學家艾力克.薩丁提醒大家的,教育事業最緊要的就是「提供一種有益的隔離形式」,而紙本書籍正好滿足此一需求。他說明:「就物質面而言,紙本書籍本身是一個封閉性物品,但是卻對知識與想像的一切經驗開放。它將處於一定距離之外的『他性』(altérité)呈現給讀者。它要求讀者全神貫注,而這種態度對思考反省以及知識熟成都是不可或缺的。」《資料運算處理程式管控下的生活》(La Vie algorithmique)一書的作者沉痛指出:「政治力受數位工業遊說的壓力越來越大。」接下來便是「電子教師」的階段。從今以後,「磨課師自學課程」(Moocs,亦即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之縮寫)將與傳統學校一較長短。這種同時可供幾百萬人聽講的線上「講述教學課」(cours magistraux)將使教師無用武之地。作為創造力與知性對話來源的「人」,如今要被填鴨式的教學以及自動化的知識測驗取代。學校教出來的不再是公民,而是被數位經濟優化的個體,而這些個體充其量只是會批判的消費者而已。
我們在此引述歷史學家兼法蘭西公學(Collège de France)教授馬克.福瑪侯立(Marc Fumaroli)的說法:大數據公司意圖「將人類閉鎖在那功利的、可操縱的量化天地裡。」整個世界全陷溺在即時的片刻中,而這些接續而來的片刻則一概獻給了消費。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在經歷不同的時間經驗,可是我們生活的此時此刻確實很不一樣。這就是發明「現在性」(présentisme)一詞、世界傑出古希臘專家的歷史學家法蘭索瓦.阿爾托(François Hartog)所了解的:「因為當今這個『現在』只願意在自己的視界中開展,只求自我完足。然而,從某角度審視,『現在』其實包含了過去的一切與未來的一切,且這都是『現在』所需要的。『現在』其實具有『永恆』(éternel)或乾脆說具有『重複不斷發生』(perpétuel)的特徵。」在當今這個時間的樊籠裡,唯一的視界只剩下此時此刻。這代表什麼都沒有。尼采用兩句話就總結了:「所謂『此時此刻』就是:剛剛還在,然後,唉呀,瞬間就遠離了。在它之前是空無,在它之後亦是空無。」線性的時間消失了。網路世界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大數據公司可以說終結了「歷史發明者」希羅多德的歷史觀。希氏在兩千五百年前寫下人類第一部歷史記述,不僅只描寫事件,而且就像羅傑─坡爾.德洛瓦所言:「回頭追溯造成目前結果的起因。」希羅多德據說為西方文化注入「延續」的概念,那也是一種「同舟共濟」的理想:我們非但是前代人的繼承者,也必須對後代人負責任。我們對未來世代那種休戚與共的情感一旦消失,未來人類面臨氣候巨變時將付出昂貴的代價。
時間軸一旦被摧毀,歷史的參考點一旦被擦掉,我們將會招致混亂狀態,而且沒能力為事件分出輕重、大小等級。如果被剝奪了時間深度,我們每個人都將生活在扁平的世界裡。在那當中,一切都處於相同的基準,一切價值均等。既然當局在歷史教學方面已逐漸以主題式取代編年式的呈現,則提供上述問題解藥的絕對不是學校。不但「歷史」已經無足輕重,就連「故事」(récit)本身亦已崩解。大數據公司也殺掉荷馬。這位古希臘詩人寫出《伊里亞德》與《奧德賽》這兩本在西方世界具奠基地位的故事。這些具普世價值的文本旨在教導世人成為公民,並且建構個體以及社群,可以說是生活學校。在網路那一個無邊無際而且浮動的空間裡,時間之神柯羅諾斯的箭全然不具意義。故事沒有開展,只以不耐煩的狂亂啃食自己。
人類陷於迷茫困惑,在時間中或在空間中都一樣。當我們寄出一封電子郵件時,我們並不在乎對方人在哪裡,收不收得到信才是重點。從今以後,就讓手機或汽車的衛星導航系統告訴我們身在何方、要去哪裡、走哪條路。每個月都有十億人口仰賴谷歌地圖指引方向。誰不曾有過如下的經驗:放任衛星導航系統引領自己,到達目的地之後卻完全沒辦法在地圖上精確指出地點?我們已將引導我們、指揮我們的任務託付給大數據公司了。我們的大腦由於將某些任務「外包」出去,它的功能便退化了。我們的記憶力因為越來越依賴外部協助,所以和方向感一樣,都有退化現象。有一項著名的研究指出:倫敦的計程車司機由於必須牢記整張城市地圖、背熟所有大街小巷名稱,因此核磁共振儀顯示他們的海馬迴(Hippocampe) 特別肥厚。我們毫無節制地使用導航系統將會實質改變自己的大腦迴路。在地圖產品計畫報廢(Obsolescence programée) 的策略下,史上最早之地理學家埃拉托斯特尼(Ératosthène) 與托勒密(Ptolémée) 的遺緒已然消失殆盡。在數千年之間,地圖繪製術以及編年史幫助我們建構思想。一旦兩盞明燈熄滅,我們將越來越難掌握環繞在我們身邊的世界。
一旦我們不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們也將不再知道自己往哪裡去。也罷,大數據公司會代替我們弄清這些事情。我們的神經系統運行起來比數位網路慢上四百萬倍。谷歌公司的共同創辦人賴瑞.佩吉說過:「人類的大腦好比一部過時的電腦,它需要一個更快的處理器與容量更大的記憶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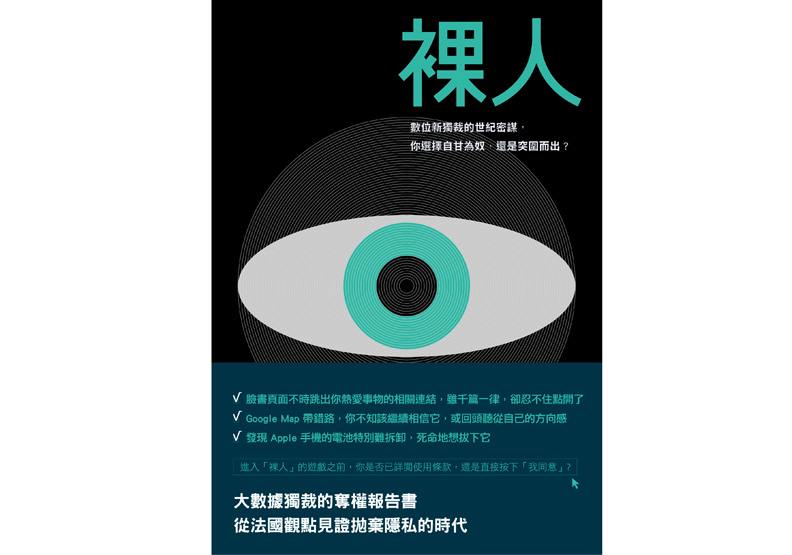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裸人:數位新獨裁的世紀密謀,你選擇自甘為奴,還是突圍而出?》一書,馬克.莒甘(Marc Dugain)、克里斯多夫.拉貝(Christophe Labbé)著,翁德明譯,麥田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