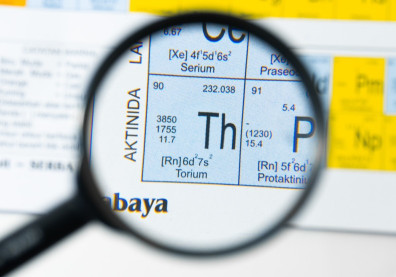非防禦性溝通
妳的母親可能直到現在仍讓妳壓力很大,而且她的手段五花八門,包括:誘騙、挑剔、威脅、哭泣、嘆氣、讓妳感到內疚/低人一等、遇到任何不滿就以「不要對妳媽回嘴」恫嚇,或者告訴妳不聽話會招致嚴重後果。妳勢必因此成為自我辯解的專家,成天在想辦法否認自己的錯誤、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為自己找出各種藉口或理由,或者直接道歉。但妳沒有意識到的是,每次只要以類似方式回應母親,即便妳以為有在保護自己,其實都只是被迫採取防禦姿態──而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極大。自我保護是一種避免受傷的機制,但採取守勢其實是一種軟弱,往往還伴隨過度害怕面對質疑與批判的問題,甚至因此永遠無法和他人採取平等立場溝通。
以下是一些採取守勢的人常會說的話:
—我才沒有。
—不,我沒有。
—妳怎麼能這樣說我?
—妳為什麼總是……?
—妳為什麼不能講理地做出一些改變?
—那實在太瘋狂了。
—我從沒說過那種話/做過那種事。
—我這麼做只是因為……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要……
—但妳答應過了……
這些防禦性語言內埋藏了各種焦慮、擔憂、恐懼及大量的脆弱情緒。
防禦性語言是妳的敵人。每次只要採取守勢,妳就等於給了母親進攻機會,也代表願意被捲入「指控/防禦」的無效迴圈中。妳等於自動退到角落,邀請她繼續對妳施壓。妳因為採取守勢,顯得既脆弱又虛弱──而實情也的確如此。
但妳可以打破這個迴圈,而且可以用一種看似神奇的方式輕易達成目標:改變妳所習慣的措辭。
雪倫:反抗母親的辱罵與批評
雪倫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目前在一家診所擔任櫃檯人員,最近她因為跟愛挑剔的自戀的母親起了衝突,感到極度恐慌,所以前來尋求我的幫助。(我們在第二章〈嚴重自戀的母親〉討論過她的故事。)自從寫信給母親之後,她比較懂得正面看待自我,但和母親之間,仍處於一觸即發的緊繃狀態。
雪倫說:「她又來了,蘇珊。之前莫娜阿姨過生日,我去和她及我母親共進午餐。我愛莫娜阿姨,再加上兩人很久沒見面,所以花了點時間了解彼此的近況。她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還來不及開口,我媽就插嘴。『慘斃了,』她說:『她現在在一個醫生的辦公室工作,而且是櫃檯人員。』那種語氣好像我是收垃圾的還是怎樣。然後她又說:『那麼多書都白念了呀!』接著發出一串悲劇女王的苦笑聲,『她真是我的小失敗鬼。』」
我問雪倫如何回應母親。
她說:「妳一定會為我感到驕傲,蘇珊。我有維護自己的立場。『我才不是失敗者,』我告訴她,『我以自己為傲!我喜歡我的工作,喜歡我服務的對象。我的工作讓我很愉快。妳為什麼就不能為我開心呢?我本來就不想要一份高壓的工作。為什麼妳總得羞辱我?』她總算安靜了一陣子,但最後還是忍不住回嘴。『好吧,親愛的,』她說:『我知道妳對這件事很敏感,但妳得振作起來,我不可能永遠當那張在危機時接住妳的救生網。』講得好像她有當過我的救生網一樣。我氣壞了,但幸好莫娜阿姨立刻改變話題,我媽也沒繼續追究。」
我問她,對這段對話有什麼感覺。
「感覺不是很好,老實說……我確實有維護自己的立場,本來以為事後感覺會很好。確實,當下感覺不錯,但對話結束後,我的感覺還是很糟。真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向雪倫解釋,母親的輕視與汙辱評論(「她真是我的小失敗鬼。」)揭開了她的舊傷:妳就是不夠好。於是,她腦中立刻本能地啟動熟悉的辯解迴圈。她的直覺就是保護自己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
「問題是,」我告訴她,「妳用來保護自己的策略無法終止迴圈,反而使情況惡化。這些反應看似理所當然,但每當妳試圖合理化自己的作為,或老是追問『為什麼』,例如:『為什麼妳總得羞辱我?』其實都是在為母親進行彈藥補給,最後幾乎無從避免地感覺自己渺小、受辱、不夠好,而且就算大吼回去也沒幫助。」
我進一步解釋,一旦她採取守勢,母親就能掌控兩人的對話節奏及話題。因此,雪倫的防禦等於邀請母親做出更多批評、攻擊的行動。一旦雪倫受到攻擊,並因此沮喪,就更可能出現無效的退化行為。「我知道妳沒生小孩,但一定看過小孩吵架,」我告訴她,「比如一個人說:『妳作弊!』另一個人說:『我沒有!』這場對話就會像乒乓球賽一樣來來回回:『沒有!』『就有!』『沒有!』『就有!』妳跟母親進行的就是這種類似五歲小孩的吵架,結果當然也沒什麼不同。」
我建議先進行角色扮演練習。角色扮演是我多年來使用的諮商技巧之一,不但能為人有效形塑新的行為模式,同時可以精準找出問題的關鍵核心。
我說:「現在,請妳假裝是妳的母親,我假裝是妳。讓我為妳示範一些更好的回應方式,而且學起來很容易,不但至少能暫時停止對方的挑剔攻擊,也能給妳重整心情的機會。就從母親最常找妳麻煩的一些話開始好了,我希望妳盡量模仿她的口氣。」
雪倫(扮演自己的母親):「我真不懂,妳怎麼能放著商管碩士學位不管,跑去接電話跟整理檔案?但反正妳從來都不聽我的話。要是妳懂得聽話,就不會這麼讓人失望了。」
我(扮演雪倫):「我知道妳的意思了。」
雪倫(沉默了一陣子):「真的嗎?就這樣?我不知道該怎麼接下去。」
我:「就是這樣。妳媽也會不知道該回答什麼。一旦妳不再採取守勢,她就找不太到攻擊的地方。讓我們再試一次。」
雪倫(扮演自己的母親):「我真不想這樣說,但妳讓我們好失望。我想妳永遠都只能是個小失敗鬼吧。」
我(扮演雪倫):「我不接受妳對我的定義。」
雪倫說:「只要這樣說就可以了嗎?感覺結束得好……突兀。我不該多說些什麼嗎?」
我說:「不,這樣說就行。簡單一句話就夠了。不要試圖補充或修飾,也不要覺得有義務填補之後的沉默。一開始可能有點尷尬,但多練習幾次就沒問題了。」
我給了雪倫一張「非防禦性回應」的清單,請她熟讀後,找一位朋友練習。
非防禦性回應練習
當妳練習時,請在腦中想像母親最常用來批評或壓迫妳的話,接著從清單中找出適合回應的項目,獨自練習到能夠自在、流暢地應答為止。一開始可能有點刻意,畢竟大家對話時常仰賴習以為常的直覺,但我向妳保證,練習的結果絕對會令妳驚喜。
非防禦性回應如下:
—真的嗎?
—原來如此。
—我理解了。
—真有意思。
—那是妳自己選的。
—我知道妳的意思了。
—妳可以有妳的意見。
—很遺憾妳為此感到不開心。
—我們等妳冷靜一點再來討論。
—大吼和威脅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我不討論這個話題。
—不是我選擇要討論這件事的。
—讓人內疚及裝可憐不再有用了。
—我知道妳不開心。
—這件事沒得討論。
這些回應的功能就像裁判一樣,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率足以暫停紛爭,阻止衝突繼續擴大。當然,妳不需要對好相處的人使出這項技巧,但只要遭受胡亂指責、霸凌、攻擊或批評時,這就是一項必要武器。
我告訴雪倫,只要使用一次非防禦性回應,她的恐慌發作問題一定會大幅緩解,因為有了武器,就不會再感覺情緒如此赤裸而脆弱。
下一次會面時,她的實測回報確實證明她有了自己的防護罩。
「我媽發現我沒有一如往常地開始自我辯解時,顯得很慌亂。之前在練習回應時,我覺得很蠢,但在需要時有所準備的感覺實在很好。有了這些回覆範本,我覺得身邊彷彿圍繞著護城河,她再也碰不到我。真的有幫助。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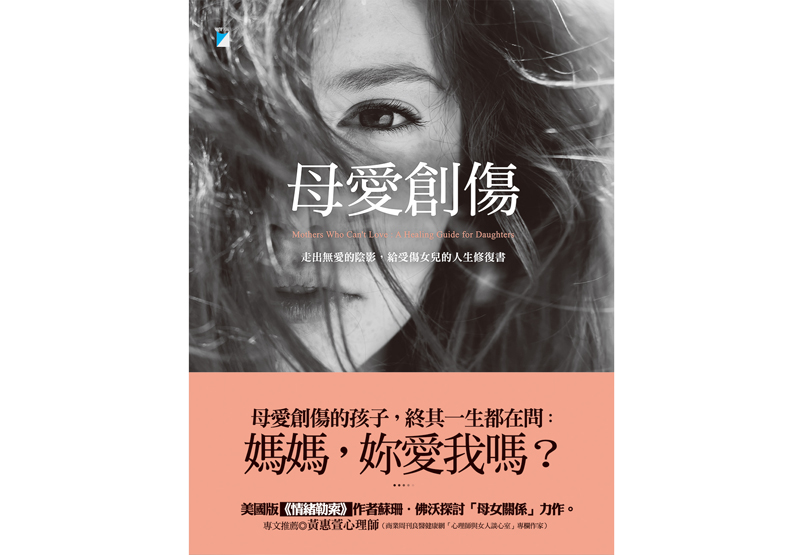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母愛創傷:走出無愛的陰影,給受傷女兒的人生修復書》一書,蘇珊‧佛沃(Susan Forward)、唐娜‧費瑟(Donna Frazier Glynn)著,葉佳怡譯,寶瓶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