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英國,我常以為自己絕不會迷路,也不會在這個寧靜祥和但處處人跡的國度裡找到任何不為人知的地方。儘管如此,還是老有人在威爾斯山區走丟、在湖區凍死,或是失足墜海;而且許多鄉下地方即使並不荒涼,看起來卻像是蠻荒之地。正是這項溫馴的特質,使得英國不僅讓人捨不得離開,而且通常也很難恣意而行。天氣好的時候,從英國東南方可以看到法國海岸,然而英國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更不只是英格蘭而已。它有邊界,四周環繞著冰冷的海洋。隨著時間流逝,英國對我而言似乎變得更大,而不是變小了,有些地方幾乎到不了;儘管在那十八年裡,我從未忘記,我是置身在一座島嶼上。
英國文學的博大精深,或許堪稱世界之最;它讓嗜書如命的外國人──那正是以前的我,也是現在的我──得以對英國的樣貌有個清晰的概念,不論是君主制度的複雜權力關係、如迷宮般的城市、壯觀多樣的海岸線、容易讓人誤以為具有民間風味的小村莊,或是像東方社會一樣繁縟的社會規範和儀節。至於它的四季之美,光是春季就有一整座圖書館的文學作品在詠嘆它;這些作品有助於人們度過冬天的陰暗和不確定性,進而領略春天之美。
讓我歡喜讓我痛苦的英國
我不能說我到英國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充分領略英國文學之美。我放棄新加坡教職來到英國是因為,一九七一年英國鄉間有一棟房子每個星期只要相當於十美元的租金就可以租得。我是在多塞特郡(註一)西部的靠海不遠處找到這間小屋。作為一名自由作家,有老婆和兩個孩子,我可以住在一個不會感覺到經濟壓力的可愛之地。所以,雖然是撿便宜貨的心態,而非湯瑪斯.哈代的作品帶領我到那個村子,但無可避免地,從這些草根性強的村民中,我發現了哈代作品的真諦。他對庶民、農莊、山丘、野花、村落,甚至殘酷形式的描述,依舊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是我的功課。我決定忠於自己的體驗。
當倫敦人說「北方」的時候,指的是曼徹斯特或紐卡素;但對我而言,北方永遠意味著蘇格蘭,因為我清楚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島。分成好幾個區的英國有許多奇奇怪怪的事,其中之一是,最北邊竟然有個郡叫南地(Sutherland)──當然,這是維京人的觀點;因為對他們而言,那個地區就位在他們的南邊。我搭火車時,從來就搞不清火車所穿越的是威爾斯、康瓦爾或是蘇格蘭地區;對我而言,它只是經過許許多多的站,而且一站比一站小。對於英國種族之間的衝突──不論是故意挑逗和不公平的待遇、長期的侵略或是不滿情緒──我向來抱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這是我在烏干達觀察巴干達族和阿喬利族之間的紛爭所得到的經驗。
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從多塞特搬到了倫敦,不過流浪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作為一名外國人,我發誓絕不客死異鄉、被人葬在教堂墓園黝黑低垂的紫杉樹下。有朝一日,我將離開。但我絕沒想到我會形單影隻地離開,如同當初抵達時兩袖清風、無足輕重般。我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抵達英國,一九九○年一月十九日離開。那段期間是我記憶中最快樂也是最悲傷的一段歲月,我經歷過幾近狂喜的喜悅,也經歷過瀕臨絕望的痛苦。
我知道我並不屬於這兒──在英國,沒有任何一個外國人可以融入這個社會──我也沒有這個意願。無論如何,我很喜歡這種成為外國人和隱姓埋名的經驗,就像電影〈天降財神〉(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中,流落地球的火星人看起來與常人無異般。對我而言,這個狀態象徵了作家的兩難;然而在這個人人都具備讀寫能力、都喜歡上圖書館的島上,當作家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由於作家獨特的金錢觀,作家在美國是個異類,但在英國則不然。
我在英國必須繳稅,卻無法投票;所以我對英國政黨缺乏歸屬感,也從不支持任何政黨,甚至不覺得自己是英國居民。我的房子坐落在倫敦南邊、在英國這個島上。雖然形體上,我常覺得不自在或是社交生活貧乏,然而卻比來英國之前或之後思想更自由、更受到重視。我在英國從未有過賓至如歸之感,然而我也從未感覺自己不受歡迎。望著街頭熙來攘往的人群,我常想,這是你們的家而非我的家。我常祈求,不要讓我死在這兒。
在英國待了十一年之後,我變得愈來愈焦躁不安。為了蒐集更多撰寫這座島嶼的經驗,我開始以徒步、搭火車、坐公車和乘船的方式展開環島之旅。當筆調輕鬆、內容詼諧的《到英國的理由:濱海王國之旅》(The Kingdom by the Sea)一書問世時,各種評論紛至沓來──英國跑文學路線的記者並施展他們毫無惡意的毒功──然而各界的大驚小怪意味著我的書受到認真看待,我也不例外,因為我還住在那兒。美國的英國迷所不了解的是,雖然英國人願意傾聽島上幾乎任何人的意見,但大體來說,如果那個作家不住在英國,他們對他(她)的意見也就興趣缺缺。當我離開英國、不再成為英國居民時,我同時也失去了挑剔英國的權利。
某日,我列出一份所有喜愛英國事物的清單,其中包括:麵包、魚、雲彩、啤酒、鄉村酒吧、濃縮奶油、花園、蘋果、報紙、羊毛衣、廣播節目、公園、印度餐廳、業餘表演、皇家郵政、火車以及耐心和謙恭有禮的人民。
「對所有可愛事物再看最後一眼/無時無刻」,住在英國時,我經常這樣喃喃自語。我喜歡在威爾斯海邊泛舟、從倫敦騎腳踏車到布萊頓、到南丘(South Downs)踏青、在皇家音樂大廳(註二)聆聽交響樂、到牛津和劍橋探視兩個兒子。多幸運啊!我心想。我在這裡安家落戶,如今已開花結果。
離開之後,回首往事,我發現英國那段歲月對我造成極大程度的影響,但並非如我原先所想像的那樣。我立志要勤儉持家,而且與儉樸的人比鄰而居使得我並未失去勤儉的習慣。我體驗到艱難的路帶給我豐富的收穫。我開始珍惜困厄、沮喪和艱苦的時光,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我開始領略困境的真諦。我所指的並不是,好比說,我曾經走過的從格爾木到拉薩、穿越西藏高原的那條漫長和艱困的路,而是我走了十八年的倫敦南環公路;這條路令人沮喪的程度可說是難以形容;然而,有誰會對這感興趣呢?困境可以是一個生動的話題,但沒有人想聽討厭的事。
英國的風景絕美,但它可也是冷酷嚴峻的──它並非醜陋或景觀險惡,而是那種一望無際的單調景致似乎一點一滴地啃噬著我的靈魂。哈德遜菲爾德的住宅區令人痛心地被一條高速公路攔腰穿過;我的孩子在小學校園裡和所有其他小朋友一樣,面色蒼白;公車站永遠像擠沙丁魚般,更可悲的是,它雖擁擠卻井然有序;海水退潮時泰晤士河某些河段呈現出單調荒涼的景致;以及再也沒有比卡福鎮(Catford)細雨霏霏的冬日午後更淒涼的景致了──褐色的天空、灰色的磚瓦和黑色街道。不過我從不認為它一無可取──那是一種真實、一個機會,而且我的不安使我對外界的觀察更加敏銳,給了我寫作的題材。後來,我搬離了那個地方,結束了這本關於英國的書。
註一:多塞特郡(Dorset):英格蘭南部一郡。
註二:皇家音樂大廳(Royal Festival Hall):倫敦南岸藝術中心的主體建築,為慶祝全英藝術節而建;六月起每天中午有免費的爵士樂和古典樂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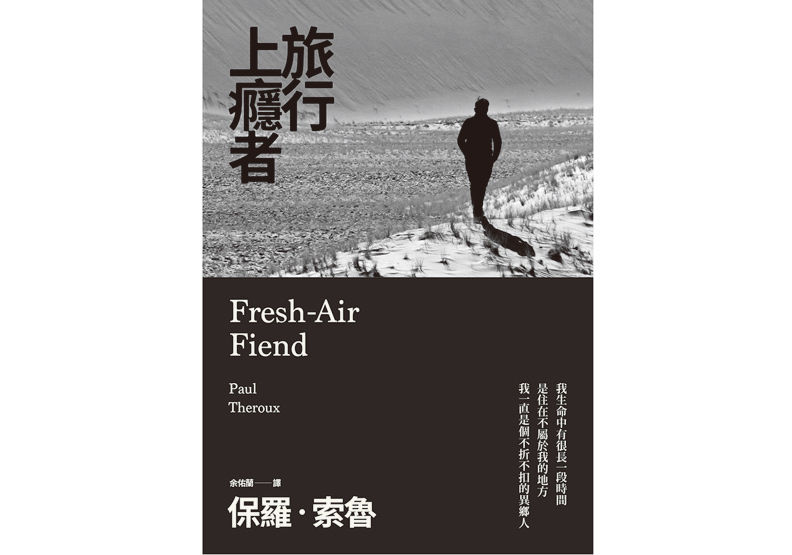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旅行上癮者》一書,保羅.索魯(Paul Theroux)著,余佑蘭譯,馬可孛羅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