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進展
在美國,大家覺得個人自由的最大敵人是國家。就這方面來說,美國人那樣想確實是有道理的。歷史充分證明了,國家可用來壓迫,甚至完全破壞個人自由。畢竟,過去幾十年間,美國的最大敵人是蘇聯,蘇聯當局往往連人民生活中最隱私的細節也掌握不放。美國有些人評論北歐的成就時,把芬蘭等國貶抑成「社會主義保姆國家」,他們的說法表達出一種真實的恐懼,擔心人民可能會變成溫順的羔羊,日益受到政府的影響和掌控。
不過,每當我聽到美國人把芬蘭稱為社會主義國家時,總覺得時光好像瞬間回到一九五○年代。我這一代和老一輩的芬蘭人都很清楚社會主義是怎麼回事,更遑論共產主義了。畢竟,我們成長的過程中,蘇聯就緊挨在隔壁。二十世紀,芬蘭曾為了保障自由、獨立及自由市場體系,而與社會主義打了三次殘酷的戰爭。
以下是一點歷史背景:在二十世紀初以前,芬蘭一直是由瑞典和俄羅斯交替統治,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共產革命推翻俄國沙皇時,芬蘭獲得獨立。但芬蘭國內馬上陷入激烈的鬥爭,工人階級認同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理念,對抗保守的資本家。在短暫但激烈的內戰中,自由市場派勝出,徹底擊敗了社會主義者的反動。
二十年後,蘇聯威脅到芬蘭的獨立時,芬蘭再次擊退了社會主義,保全了自由和獨立,但芬蘭也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近五分之一的芬蘭國民上戰場對抗蘇聯,還有更多人是以醫護人員和支援的角色參戰。總計,芬蘭共三百七十萬人口中,有九萬三千人在戰爭中喪生(註一)。
我們芬蘭人所瞭解的社會主義是這樣的:政府控制生產,禁止人民擁有財產,不准有私人工廠、公司或商店,也沒有自由市場。沒有人可以累積個人財富,只有一個政黨,幾乎沒有個人自由和言論自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其實只差一步,馬克思定義的共產主義是:政府或國家皆可拋。
把當代的北歐社會視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很荒謬的想法。有些保守派的批評者喜歡說,歐巴馬那種自由派的美國領導者是社會主義者,那種說法實在太可笑了。事實上,芬蘭人很快就對這種刻板印象嗤之以鼻。二十世紀期間,芬蘭為了對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犧牲的人數,跟美國為了對抗共產主義而參與韓戰和越戰所犧牲的人數差不多(美國在那兩次激戰中犧牲了約十六分之一的人口)(註二)。過去七十幾年來北歐國家的經驗顯示,即使是美國這樣一個已經非常堅持自由的國家,可能也能從北歐獲得一些有關自由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啟示。
事實上,如果二十一世紀國家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從人民身上剝奪更多的權力,而是為了進一步推廣自由和獨立的現代價值觀,為人民最完善的個人自由奠定基礎,那會是什麼樣子呢?如今的北歐社會契約就是由這種對個人主義的特殊堅持界定的。從北歐地區在全球各種調查上的排名,不止生活品質方面,還有經濟活力方面,可以清楚看到採行這種方式的結果。
我離開芬蘭、移居美國時所放棄的種種優勢,諸如公共醫療照護、平價托兒服務、真正的育嬰福利、優質免費的教育,納稅人資助的老人住所,甚至配偶單獨課稅等等,並不是政府為了讓我們變成依賴國家德政的奴隸而發放的禮物。北歐體制的設計,是刻意把現代生活的具體挑戰納入考量,讓人民盡可能在生活和財務上達到獨立。這其實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體制恰恰相反。這也是為什麼在北歐國家呼籲人民團結一致,並不像一般所想的那麼高尚的原因。
特雷葛告訴我:「瑞典人喜歡把自己想成非常無私、總是做好事的人。」其實同樣的說法也可以套用在芬蘭人或其他北歐人身上。不過,促使瑞典人和其他北歐人支持北歐體制的真正動機,其實不是利他主義,而是利己主義,沒有人是那樣無私忘我的。北歐社會提供全體人民──尤其是中產階級──最大的自主權,讓他們掙脫傳統的依賴關係,這樣做除了確保個人自由以外,也幫人民省下很多錢和麻煩。特雷葛和貝格倫指出,北歐國家其實是世界上最個人化的社會。
我知道有些美國人會覺得這聽起來很可怕,那肯定讓他們聯想到極權主義國家──為了把人民變成體制的奴隸,而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所有情感關係。如果你因為在芬蘭住過,而對北歐社會抱持負面看法,那也是可以理解及寬恕的。芬蘭人也很愛抱怨國內的一切有多糟──舉凡社會服務有多爛、家庭關係有多麻煩、孩子成長有多慘、政府有多官僚等等。這有部分是人性使然,人無論生活過得多好,總是可以挑剔自己的處境有多糟。事實上,很多芬蘭人真的不知道自己過得有多好,因為他們不曾在美國這種國家當過公民。例如,很多國際化、高學歷的芬蘭朋友聽我解釋了上百遍,還是不懂為什麼美國已經通過俗稱「歐巴馬健保」(Obama-Care)的平價醫療法案,卻仍沒有全民健保。他們根本無法想像先進的富有國家會這麼落後。
儘管你在北歐社會還是會聽到抱怨,你只要比較近幾十年來北歐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家庭生活統計數據就會清楚看到,相親相愛的家庭、健康樂群的孩子、守望相助的社群其實是北歐的常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研究全球幾個富國的孩童福祉,比較兒童貧困、兒童健康與安全、家庭關係、教育、行為(包括飲食、少女懷孕、霸凌)等指標後,發現荷蘭、挪威、冰島、芬蘭、瑞典都名列前茅(註三)。很遺憾,美國的排名幾乎墊底。慈善組織「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的研究顯示,北歐國家是全球對母親最好的國家,美國的排名是第三十三位(註四)。這怎麼可能呢?這確實是有可能的,因為讓人掙脫財務和其他相互依存的束縛,使他們更加關心彼此,而不是更加冷漠,正是北歐式愛的實踐。
但是這些有關北歐極端個人主義和獨立性的討論,是否意謂著:即使北歐人很愛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家庭關係終究還是薄弱的吧。畢竟,讓夫妻擺脫財務上相互依存的關係,使他們不必非得待在一起不可,那不是鼓勵家庭分裂嗎?
事實上,北歐式愛的理論藉由讓個人享有自主權,反而使家庭脫胎換骨,變得更現代,更能因應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特雷葛和貝格倫為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準備了一份報告,標題是〈北歐模式〉(The Nordic Way),他們寫道:「家庭仍是北歐國家的核心社會制度,但家庭本身也充滿同樣的道德邏輯,強調自主和平等。在理想的家庭中,成年人有自己的工作,財務上不相互依賴,小孩也在大人的鼓勵下,儘早獨立自主。這種模式不會破壞『家庭的價值觀』,而是讓家庭這種社會制度走向現代化。(註五)」
特雷葛用來說明北歐式愛的理論以及北歐社會如何看待家庭的例子是老人照護。在美國,萬一你的年邁父母長年生病,照顧他們及支付醫療費可能會耗光你的財力和人生。在北歐,萬一你的父母長年生病,他們的照護與醫療都可以依賴國家的健保系統。結果是什麼樣子呢?你可以善用陪伴父母的寶貴時間,去做一些社工人員沒辦法幫你做的事情,例如陪父母散步、聊天、閱讀,或就只是一起共度時光。
特雷葛告訴我:「研究調查詢問瑞典人,他們比較願意依賴自己的成年子女,還是依賴國家?他們回答國家。如果你換一種問法,問他們是否喜歡孩子來探望他們,他們都會說喜歡。所以瑞典老人並非不想和孩子親近,只是不希望讓親子關係變成依賴狀態。」
儘管有些美國人仍懷疑北歐國家對自由市場的投入,但瑞典、芬蘭、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富國都是沉浸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種現代自由市場的生活,正是化解家庭和社群的傳統關係,讓性別角色逐漸平等,鼓勵個人化和獨立的力量。評論者有時聲稱,北歐國家沒什麼值得全球學習的地方,因為北歐的成功是某個孤立、文化單一、種族單純的小群體所特有的。但這種說法過於狹隘,忽略了更大的格局。雖然北歐式愛的理論看似某個地區特有的文化概念,但那裡衍生的優良社會政策,正好適合每個國家日益現代化時普遍面臨的挑戰。
如今美國積極採行現代的自由市場體系,可說是超級現代的社會,但美國卻像古代社會一樣,讓家庭和其他社群體制來因應現代自由市場所衍生的問題。從北歐的觀點來看,美國陷入矛盾的衝突中,但那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衝突,也不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衝突,更不是大政府與小政府之類的老套爭論,而是卡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矛盾。從現代化的觀點來看,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確實看起來膨脹得荒謬,且恣意妄為。美國政府以形形色色的政策過度干預社會,並為特殊利益量身打造福利的方式,在北歐人看來顯然是過時的治理方式。無論美國願不願意承認這點,持續陷在過去無疑會使美國在世界上愈來愈屈於劣勢。
世界不斷地發展與改變,每個國家都需要新的想法。美國知名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名為〈人才社會〉的文章中,把這個需要描述得特別貼切:「我們活在美好的個人主義時代。(註六)]」他表達的觀點幾乎和特雷葛一樣。布魯克斯引用的證據顯示,無論我們喜不喜歡,現代化正持續地進步。例如,幾個世代以前,未婚生子是羞於見人的事,但現在未滿三十歲的美國女性所產下的子女中,有一半以上是非婚生子女。一半以上的美國成年人是單身,28%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美國單人家庭的數量比結婚有小孩的家庭還多。認為自己政治立場獨立的美國人,也比共和黨或民主黨人還多。終生雇用的情況愈來愈少,工會的會員人數也急遽下降。
布魯克斯因此指出:「這個趨勢很明顯。」他也提到個人獨立性逐漸取代了傳統老舊的人際關係。「五十年前,美國人習慣群體生活,大家比較可能融入穩定、綿密、義務性的關係,大多是以永久的社會角色來定義身分,例如母親、父親、執事等等。如今,個人擁有更多的自由,在比較多元、鬆散、彈性的關係中游移。」
布魯克斯勾勒出來的美國樣貌,是允許「有抱負、有才華的人從各種美好的可能性中脫穎而出」,但缺乏那些技能的人則遭到遺忘冷落,無人聞問。雖然這多少道破了美國的困境,但並不是美國的全貌。說到「有抱負、有才華的人」,我們還必須補充,有抱負、有才華人的人還必須幸運擁有大量的私人資源,才能在現今的美國中找到機會。
布魯克斯說,現在是把美國遺忘的安穩綿密社會加以徹底改造的時候了。這正是北歐地區所做的,布魯克斯形容目前我們的文化和經濟生活的特色是「多元、結構鬆散、彈性的關係網絡」,北歐式愛的理論正好可以作為這種關係的扎實基礎。在這個愈來愈自由的年代,芬蘭和其他北歐國家找到了拓展個人自由,同時也確保絕大多數人(不止菁英)都能夠蓬勃發展的方法。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進展,能自己發展出「北歐式愛的理論」的國家,將享有長期的優勢。良好的生活品質、工作滿意度和健康、經濟活力、政治自由和穩定是息息相關的。有鑑於此,如果美國能仿效一些北歐社會的成果來振興自己,從哪裡著手最好呢?
以北歐人的觀點看來,從人之初著手,也就是從嬰兒開始,是不錯的起點。
註一:芬蘭人在1939-1944年戰爭中的犧牲:當時芬蘭總人口是三百七十萬人,其中有七十萬人參戰,九萬三千人喪生。參見See Leskinen, 1152–55。
註二:芬蘭人的犧牲人數:韓戰及越戰中喪生的美國人約九萬五千人,幾乎跟芬蘭兩次抗戰蘇聯的死亡人數差不多(九萬三千人)。二○一五年七月,芬蘭的總人口約五百五十萬人,美國則有三‧二億人。Leskinen, 1152–53; Leland, 3。
註三:各個國家的孩童福祉:UNICEF。
註四:全球對母親最好的國家:Save, 10。
註五:特雷葛和貝格倫談作為社會機構的家庭:Berggren,“Social,” 15。
註六:「我們活在美好的個人主義時代。」:Br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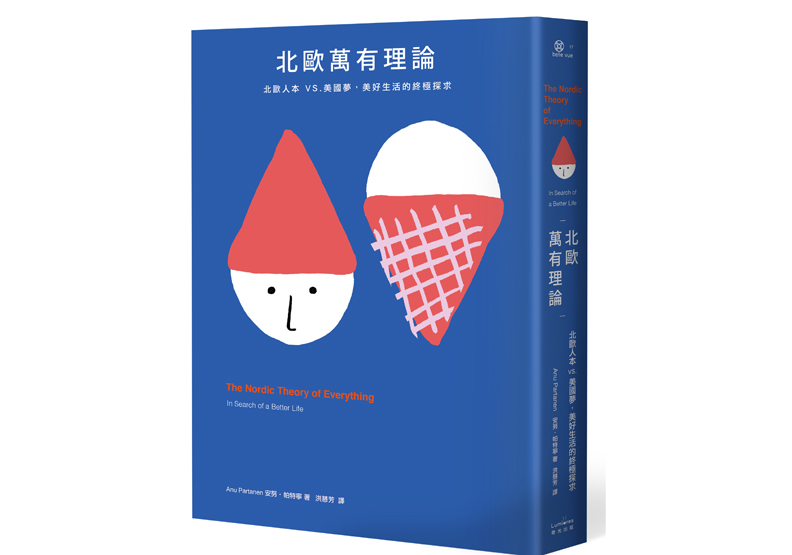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北歐萬有理論》一書,安努‧帕特寧(Anu Partanen)著,洪慧芳譯,奇光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Huy P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