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懶惰
2012年《紐約時報》部落格的一篇文章,小說家兼漫畫家克里德(Tim Kreider)有一段令人難忘的自述:「我不忙碌,我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懶惰、卻很有企圖心的人。」不過,克里德對忙碌工作的厭惡在他貼出這篇文章之前幾個月曾面臨考驗,他描述那段期間說:「因為職業上的義務,我不知不覺變得忙碌起來⋯⋯每天早上我的收件匣滿是電子郵件,要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或提出我必須解決的問題。」
他有什麼對策?他逃到一個他形容的「不公布的地點」--一個沒有電視、沒有網際網路的地方(上網要騎腳踏車到當地的圖書館),在那裡,他可以繼續不回應在那些小義務如針扎般的攻擊。那些小義務單獨看起來似乎無害,但累積起來卻嚴重傷害他的深度工作習慣。「我還記得金鳳花、九香蟲和星星。」克里德談到他隱退的日子:「我閱讀。而且,好多個月來,我終於第一次寫出一些像樣的東西。」
就本書的目的來說,我們必須認清克里德並非梭羅(Thoreau),他從忙碌的世界隱退並非為了凸顯複雜的社會批判。他搬到不公開地點的動機是出於一種令人驚訝、但務實的領悟--那讓他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以下是克里德的解釋:
懶惰並非度假、放縱或罪惡,它對大腦不可或缺,就像維他命D 對身體一樣,缺少它將使我們的心智生病,像是造成缺陷或佝僂病……聽起來似乎矛盾,但它是把工作做好所不可或缺。
當然,當克里德談到把工作做好,他指的不是淺薄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你花越多時間在淺薄工作,你就能完成越多的淺薄工作。然而,克里德關心的是深度工作--創造這個世界認為有價值東西的嚴肅努力。他相信,這些努力需要心智定期得到釋放和休閒的支持。
這個策略的看法是,你應該效法克里德,定期在你的職業生活中安排充足的休閒時間,免於工作壓力,以便把(深度)工作做好(雖然這聽起來有點矛盾)。有許多方法可以達成這個目的,例如,你可以採用克里德從淺薄工作世界完全退隱的方法,躲到一個「不公布的地點」,但這對多數人來說並不實際。
我建議的是一種較可行、但仍然很有效的做法:在工作日結束時,停止思考工作上的問題,不再檢查電子郵件、不在心裡重播討論,也不籌畫你將如何處理即將面臨的挑戰,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如果你需要更多時間,那就延長工作日的時間;一旦結束,你就必須清空心思,留給克里德的金鳳花、九香蟲和星星。
在提出支持這個策略的技巧前,我想先探討為什麼停止思考,能提升你創造出高價值成果的能力。當然,我們已經有克里德的個人背書,但背後的科學也值得我們花時間了解。深入探究這方面的文獻後,我發現有三個可能的解釋:
理由1:停止思考有助於領悟
思考以下摘錄自2006年《科學》(Science)期刊的一篇論文:
科學文獻數百年來強調在做決定時,有意識思考的益處……此處想探討的問題是,這個觀點是否理由充分。我們的假說是,它並不充分。
這段溫和的論述,字裡行間隱藏一個大膽的觀點。這項由荷蘭心理學家狄克斯特霍伊斯(Ap Dijksterhuis)主持的研究想證明,一些決定最好留給你的無意識心智來做。換句話說,與其積極的做這些決定,不如吸收相關的資訊後,就放下來做其他事,讓心智的潛意識層來領會,得到的結果會更好。
狄克斯特霍伊斯的團隊證明這種效應的方法是,給實驗對象必要的資訊做購買汽車的複雜決定。半數對象被告知要徹底思考這些資訊,做出最佳決定;另一半在閱讀過資訊後,接著做不相干的簡單謎題,然後在沒有時間思考的情況下被帶到做決定的地點。結果第二組的表現比較好。
類似實驗的觀察結果,促使狄克斯特霍伊斯和同事提出「無意識思考理論」,嘗試了解意識和無意識心智在做決定時扮演的角色。這套理論認為,做需要應用到嚴格規則的決定,必須用到意識,例如,在做數學計算時,只有你的意識心智才能遵循精確的數學規則,確保正確性。另一方面,面對牽涉大量資訊和多重模糊、甚至彼此衝突的條件,你的無意識心智很適合解決這個問題。無意識思考理論的假說是,因為大腦的這部分有更多可以派上用場的神經頻寬,能處理更多資訊並過濾潛在的解決方法,勝過意識中心的思考。
根據這套理論,你的意識心智就像一部家用電腦,你可以執行細心設計的程式,針對有限度的問題得出正確答案;而你的無意識心智就像Google龐大的資料中心,由統計運算法過濾以兆位元組計的零亂資訊,能針對艱鉅的問題找到出人意料的有用解答。
這項研究的意義是,給你的意識大腦休息的時間,能讓你的無意識輪班,整理你最複雜的職業難題。因此,停止思考的習慣,不見得會減少你從事生產性工作的時間,而是增加工作的類型。
理由2:停止思考有助於補充深度工作需要的能量
一篇2008年發表在《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的論文經常被引用,內容是一個簡單的實驗。
實驗對象被分成兩組,一組被要求在研究地點密西根州安亞伯大學校園附近的植物園木棧道散步;另一組被安排走路穿過安亞伯熱鬧的市中心。接著兩組都接受一項需要專注的「逆向記憶廣度」測驗。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是,大自然組的表現比另一組好20%。當研究人員隔一週讓同樣的實驗對象調換地點,再做一次做測驗,大自然組的表現仍然較好。
也就是說,決定表現好壞的不是人,而是他們有沒有機會先在樹林裡散步。
這項研究其實是證明「注意力恢復理論」的許多研究之一,這個理論認為,花一點時間置身大自然可以改善你的專注力。注意力恢復理論在1980年代首度由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家瑞秋.卡普蘭(Rachel Kaplan)和史蒂芬.卡普蘭(Stephen Kaplan) 提出(後者也是前述論文共同作者之一,另外兩名是柏曼﹝Marc Berman﹞和尤尼德斯﹝John Jonides﹞),理論的根據就是注意力疲乏的概念。注意力恢復理論指出,集中注意力需要「導向性注意力」,這種資源有限,如果你耗盡它,你就難以專注。就本書來說,我們把這種資源看成和前面討論過鮑梅斯特的有限意志力儲備是一樣的東西。
這項研究說,走在忙碌的城市街道,需要你使用導向性注意力,因為你必須處理許多複雜的事情,像是考慮如何穿過街道而不被撞到,或何時繞過一群速度緩慢、擋住人行道的觀光客。只要走個十五分鐘,實驗對象的導向性注意力就已耗損不少。
對照之下,走在大自然中,在夕照下,你置身在論文的領銜作者柏曼所稱的「天然神奇刺激」下,這些刺激引起的注意力很少,專注機制可以獲得補充的機會。換句話說,在大自然中,你不需要導引你的注意力,因為移動時很少碰上阻礙(不像擁擠的十字路口),並且有足夠的有趣刺激占據你的心思。這種狀態能給你的導向性注意力補充的時間,經過三十分鐘的補充後,實驗對象的注意力大幅提升。
當然,你可能說在戶外欣賞夕照可以讓人心情變好,而好心情就是幫助實驗對象在測驗中有好表現的原因。不過,研究人員藉由在安亞伯不同的季節重複這項實驗,推翻這個假說。在酷寒的冬季走在戶外並未讓實驗對象心情變好,但他們的注意力測驗仍然表現較好。
對本書的目的來說,注意力恢復理論不只限於大自然帶來的好處,這個理論的核心機制是,如果你暫停使用引導性注意力,就可以恢復這種能力。走在大自然可以讓我們的心智休息,其他放鬆的活動也能辦到,只要這些活動也能提供類似的神奇刺激。與朋友閒談、和孩子玩遊戲、邊煮晚餐邊聽音樂、出去跑步,在你工作結束後的晚上用來打發時間的各種活動,都具有和走在大自然一樣的注意力恢復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你一直打斷晚上的休息時間,檢查和回覆電子郵件,或是在晚餐後撥幾個小時趕截稿時間,你就剝奪了導向性注意力需要的不中斷的休息時間。即使這類短暫的工作只花很短的時間,也會讓你無法達到恢復注意力需要的深層放鬆。只有你深信今天的工作已經做完,才能說服你的大腦切換到開始為明日充電的放鬆狀態。換句話說,嘗試從晚上再擠出一點時間工作,會降低你明日的效率,你完成的工作可能比你嚴守休息時間還少。
理由3:晚上少做的工作通常沒那麼重要
保持工作日結束的明確界線,最後一個理由,我們必須回頭談艾瑞克森率先提出的刻意練習理論。你可能還記得,第一篇談到,刻意練習是以有系統的方式加強特定技術,是專精一件事必需的活動。我已經說明,深度工作和刻意練習有很多重疊之處,就此處的討論而言,我們可以把刻意練習視為高認知需求工作的代表。
艾瑞克森1993年針對這個主題討論的題目是〈刻意練習在追求專家表現所扮演的角色〉,他特別以一節的篇幅說明研究發現個人從事高認知需求工作的時間長短。艾瑞克森指出,對新手來說,每天約一小時的高度專注似乎是極限,但對專家來說,這個數字可以提高到四小時--但很少能超過。
例如,一項研究記錄一群優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在柏林藝術大學受訓的練習習慣。研究發現,這些優秀的演奏家平均每天有三個半小時處於刻意練習狀態,通常分成兩個不同時段。成就較小的演奏家花在深度狀態的時間則較少。
這些結果的意義是,你在一定時間內的深度工作量是有限的。如果你審慎安排時間(可以利用原則四介紹的策略,排除淺薄事務),應該會在工作日達到深度工作的每日最高量。因此,到了晚上,你已經達到能繼續有效深度工作的極限,任何你排進晚上的工作都不會是對你的職涯進步真正有用的高價值活動,你的努力很可能只是低價值的淺薄工作。
換句話說,推延晚上的工作,你也不會耽誤太多重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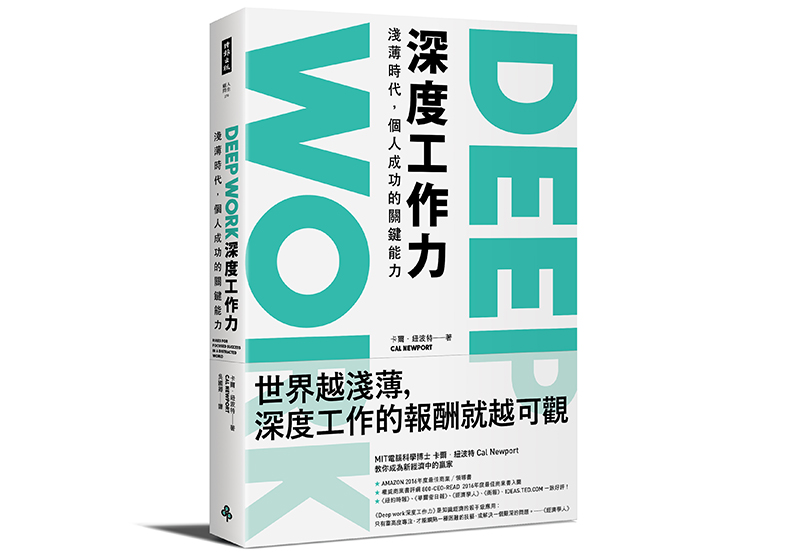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Deep Work深度工作力: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一書,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著,吳國卿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