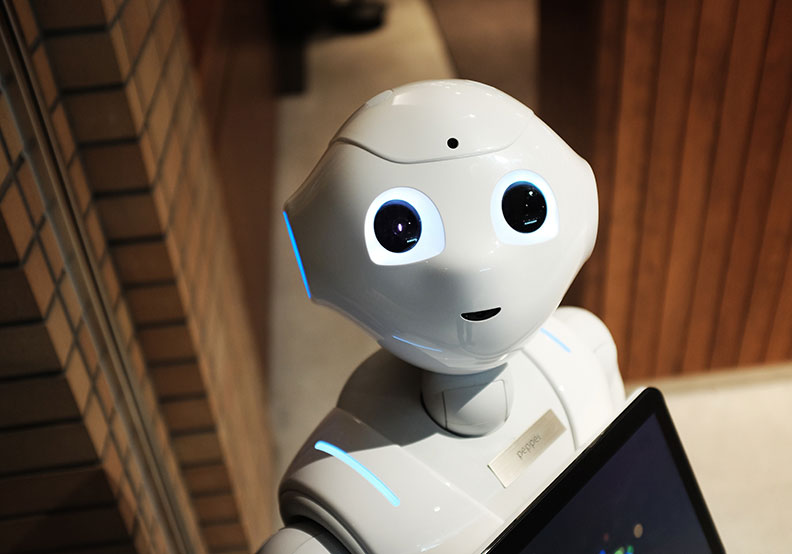自從工業革命時代起,科技的改變已經催生許多預言,不是所有的預言都獲得證實。凱因斯在他一九二八年的論文〈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預見在一個世紀後「找出經濟化運用勞力的手段,將超越找出勞力新用途的速度。」他預測到二○二八年,歐洲與美國的「生活標準」將會改善到沒人需要擔心關於賺錢的問題。那將是個富足的時代。「這將是人類被創造以來首次面臨人類真實的、永久的問題——如何運用來自免於經濟壓力的自由,如何從事休閒(這是科學與複利為人類贏得的),以及明智、欣然和健康的生活。」
二○二八的年份還沒到,不過我們似乎不在凱因斯預言的道路上。即使是在像美國的先進經濟體裡,大多數人並未感到免於經濟壓力。與其說是創造了富足的時代,讓大多數人不再需要擔心錢,不如說是節省勞力的科技一路上發展良好,進而創造了兩層式社會,分別由少數特別富裕的人與絕大多數愈來愈窮的人組成。
我也曾經提出我的預測。一九九一年,在我的《國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書中,我將所有現代的工作畫分成三大類,並預測每一大類將分別發生什麼事。我稱第一類為「例行性的生產服務」(routine production services),這類工作是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由美國資本主義的老兵從事的重複性任務——不斷重複在裝配線或辦公室裡完成。雖然這些工作通常被認為是傳統的藍領工作,但是其中也包括例行性的監督工作,包括例行檢查下屬的工作、執行標準的營運程式,以及例行的資料輸入與取回。我曾估計這類工作占美國所有工作機會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也預估當時占美國所有工作機會的三分之一的這類工作將穩定下降,並且被節省勞力的新科技及開發中國家拿遠較為低工資又急著想工作的勞工取代。我也假定美國剩下的例行性生產勞工的待遇將因同樣的原因下降。
我的預測沒錯。運用我當時使用的同樣方法。我發現到二○一四年,例行性生產工作構成美國所有工作的五分之一不到,同時其待遇中值(經過通膨調整)比二十年前低一五%。的確,所有能夠編碼寫成軟體的工作都已經或即將被取代。文件探勘(text-mining)程式即將取代許多法界工作;影像處理(image-processing)軟體將使實驗室技師成為不必要;租稅軟體也在取代會計師等等。
第二類我稱為「親自服務」(in-person services)。這種工作必須由人親自提供,因為人的接觸是這種工作不可或缺的。包括零售勞工、旅館與餐廳勞工、療養院助理、房地產經紀人、育兒勞工、家庭保健助理、空服員、物理治療師、保全人員,還有許多其他工作。這種工作的本質是一對一的銷售;確保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或確保別人受到良好照顧、快樂和舒適。在一九九○年,根據我的預估,此等勞工占美國所有雇員的三○%,而且我預估其人數將會成長——基於服務是由勞工親自提供——不論是先進科技或在外國的勞工都不能取代。不過我也預測「親自服務」的待遇將下降,有兩個原因:第一,「親自服務」將與大量過去例行性的生產勞工競爭,因為後者現在只能在親自服務的產業找到工作。第二,這些勞工必須跟勞力節省機械——自動櫃員機、電腦化出納員、自動化洗車、機器人化的自動販賣機、自助式加油——競爭,甚至零售勞工也要跟「個人電腦與電視螢幕相連」的系統競爭,「未來的消費者將能從自家客廳購買傢俱、家電,各種電子玩具——從所有角度檢視商品,選擇任何的顏色、大小、特性,甚至看起來是最吸引人的價格,然後將訂單即時送到倉庫,最後選擇的商品將直接送到顧客家裡。」金融交易、機票與旅館訂位、租車協定及類似的合約,都將在消費者家中與全球其他地方的電腦銀行執行。
同樣的,我的預測與結果差不遠。到二○一四年,親自服務的工作約占美國所有工作機會幾乎一半。此外,此等工作的待遇中值(在經過通膨調整後)低於一九九○年的水準。但是我沒預見先進科技入侵開始得那麼快,甚至連親自服務的工作都不放過。到二○一四年,亞馬遜忙著消滅零售業的工作機會,著手如何在其倉庫消除人力,甚至正在規畫未來透過空中無人機進行交貨。甚至連商業駕駛都遭到威脅。經濟學家勒維(Frank Levy)與莫南(Richard Murnane)在他們二○○四年的《新的分工》(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一書中,以駕駛卡車做為例子,說明由於這種工作需要複雜的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電腦將永遠無法執行這種任務。不過到了二○一四年,谷歌的電腦自行駕駛車(self-driving car)將對約四百五十萬名計程車、公車、卡車司機及清潔工的工作機會造成威脅。
第三類的工作我命名為「符號分析的服務」(symbolic-analytic services)。我將任何解決問題、找出問題、策略思考都包括在符號——數據、文字、口語跟視覺表現——的操作。這類工作涵蓋工程師、投資銀行家、律師、管理顧問、系統分析師、廣告與行銷專業人員,以及所有創作領域的專業人士,例如新聞業與電影業,甚至包括大學教授。其中大多數為經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通常以團隊方式一起工作或是盯著電腦螢幕。這類工作的本質是重組抽象的符號,使用的是各種分析與創造性的工具——數學演算式、法律論據、金融伎倆、科學原理、強而有力的單字與片語、視覺模式、心理洞察,以及其他解決概念難題的技巧。此等操作改善效率——更準確與更快完成任務——或是他們更能娛樂、逗趣、提供新知、吸引住人的心靈。
我在一九九○年預估,符號分析師占所有美國員工的二○%,而且預期其比重還會持續成長,他們的所得也會成長,因為對這批人的需求將持續超過能做這類工作的人的供給。符號分析的工作機會與另外兩類工作之間的這種擴大區隔,根據我的預測,將會成為驅動貧富不均的主要力量。在這一點上,跟我預測的結果也沒差太多,但是我並沒預期到有多快就會發生、這種區隔將變得多大,或是貧富不均和經濟的不安全感會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例如,我永遠也無法預期到,沒有高中文憑的美國白種女性預期壽命在一九九○年與二○○八年之間會減少五年。
我也未能預期到數位科技與龐大網路效應的結合,能將員工人數對顧客人數的比率降到非常低的水準。當風行一時的照片分享網站Instagram於二○一二年以十億美元左右賣給Facebook時,該公司只有十三名員工,而顧客有三千萬名。與之相反的是柯達,就在當時前幾個月申請破產。在顛峰時,柯達擁有十四萬五千名員工。
這個比率持續下降,當Facebook於二○一四年初以一百九十億美元買下WhatsApp,WhatsApp共有五十五名員工(包括兩位年輕的創辦人),一共服務四億五千萬名顧客。
數位化不需要許多勞工。將一個新點子向數以億計的人推銷,可能不需要很多勞工(即使需要的話)就能生產或分銷。一位在土桑(Tucson,譯註:位於亞利桑那州)的朋友最近設計了一種機器能判斷空氣中特定成分的蹤跡,他用3D印表機製作了幾百個這樣的機器,然後上網向全世界各地的顧客推銷。他只需要一部無人駕駛飛機進行交貨,而且他整個生意只需要一個人——他自己。
仔細想想在一九六四年美國最有價值的四家公司,平均市值為一千八百億美元(按二○一一年美元計),平均雇用四十三萬名員工。四十七年後,最大的美國公司價值約相當於前者的雙倍,但能以不到四分之一的員工人數完成他們的工作。
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取代勞工的科技,而且也是取代知識的科技。結合先進傳感器(advanced sensor)、語音識別、人工智慧、大數據、文件探勘,模式識別演算法正在催生具有智慧的機器人,能快速學習人類行為,甚至還能彼此學習。生命科學的革命也正在發展,使得藥品能按病人的特定狀況與基因組量身訂做。
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還有很多符號分析師將會在未來的歲月遭到取代。美國最大的兩個專業人士密集的產業——醫療保健與教育——遭到影響的情況將會特別嚴重,因為抑制成本的壓力與日俱增,且專業機器的可用性持續增加。我們正瀕臨行動式健康應用器材的風潮,例如能測量從卡路里到血壓的所有項目,以及各種軟體程式它們具備與醫療技師運作昂貴醫療儀器相同的功能™]試想超音波、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s)、心電圖™^,以及能告訴你身體有任何狀況與如何處理的診斷軟體。中小學與大學同樣會圍繞在智慧機器四周進行改組(雖然教職員一路上會大聲抗議)。許多教師與大學教授即將被一種軟體——所謂的磨課師(MOOCs)(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和線上互動式教科書——取代,引導學生學習的助理也難逃被取代的命運。
這種趨勢到哪裡結束呢?請想像一個小盒子——我們姑且稱之為「萬能器」(iEv-erything)——能為你生產任何你想要的東西,也就是現代的阿拉丁神燈。只要告訴這個盒子你想要什麼——變!——這樣東西就能立即出現在你的眼前。唯一的問題是沒人能賺錢來買這個盒子,因為萬能器做完了一切工作。這明顯是種幻想,但是當愈來愈多的工作是由愈來愈少的人來完成時,利潤將會流向更少的一群高階主管與擁有人兼發明人,使得其他人擁有愈來愈少的錢來購買生產出來的東西,因為我們不是失業就是做低薪的工作。在整個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是大量生產多數人的大量消費。這種模式不再存續,未來的模式似乎可能是一小群人無限制的生產供任何負擔得起的人消費。
根本的問題不在於工作機會的數目,而是所得與財富的分配。那些創造或投資創意大為成功的人正賺取前所未有的金額與報酬。WhatsApp的年輕創辦人之一的執行長柯姆(Jan Koum)在臉書買下他的公司時,持有公司股份的四五%,價值六十八億美元。共同創辦人艾克頓(Brian Acton)的二○%股份得到三十億美元。每位早期的員工據稱都有一%股份,每位分到一億六千萬美元。
如果目前的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擁有超大成功創意的人將會賺更多。如我所強調的,推論是這批人將會獲得無與倫比的政治影響力。但是社會上大多數人分不到這種經濟報酬,其政治力量就會消失。大多數人將會看到新科技催生的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產品與服務,但是買不起這些東西,因為新科技將會取代他們的工作以及壓低他們的待遇。
我在幾乎二十五年前做出這種預測時,我預料現代科技將會持續增加對教育程度較高勞工的需求,同時降低對教育程度較低勞工的需求。所以我假定對損失工作機會與工資下降的補救是讓人們獲得更多更好的教育,特別是能獲得高等教育。我只對了一部分。那些有大學文憑的人比沒有大學文憑的人表現得好上許多。在二○一三年,美國有四年大學文憑的人每小時賺的錢比沒有大學文憑的人多九八%。這個差距比先前五年時大學畢業生比沒念大學的人多賺八九%的差距大,也比一九八○年代初期六四%的差距更大。
不過我認為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將會穩定提高與獲得經濟大餅中較大的一塊是錯誤的。事實上,雖然受過良好教育勞工的供給持續增加,在美國對受過良好教育勞工的需求大約於二○○○年到達最高點之後,接著就逐步下降。我曾經指出,自二○○○年起絕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的所得增加的很少或完全沒增加。即使是所得最高的前一○%大學畢業生,在二○○○到二○一三年之間累積所得也只上升四.四%。同期內,大學畢業生入門工資實際上是下降的(女性下降八.一%,男性下降六.七%)。用另一種方式說明,大學畢業雖然已經成為加入中產階級的前提,但是一旦加入以後,並不能確保會占有優勢。中產階級在整個經濟分到大餅的百分比持續下降,同時頂層人口分到的百分比持續成長。
要扭轉由於遭到內置於市場規則而向上的預先分配、將大資金逐出政治圈、重新塑造公司,以及改善教育品質與教育的普及,這些都將有幫助。反制力量的目標不能僅只有這些。這些改變的本身不會轉變科技進步對我們影響的方向。但同時我曾經說明過,如果收入與利潤壓倒性的流向非常少數的一群人,任何這種經濟、社會的生產體系是不可能永續下去的。那麼,答案為何?
有些人呼籲對這些少數贏家的所得與財富進行課稅,然後將稅收重分配給其他所有人。反制力量提高邊際所得稅率是可能的。畢竟在二次大戰後三十年中,當時大公司與華爾街的力量受到有效的反制,最高的邊際稅率(marginal income-tax rate)從未低於七○%,有效稅率(包括所有扣除額與租稅扣抵)從未低於五○%。但是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要在四十到五十年達成普遍分享的繁榮,直接重分配的規模必須超過這個幅度。當幾乎所有東西都能透過取代知識的科技做成,而且這些科技是由少數一些人所持有,即使是皮凱提提議對全球財富課稅恐怕都還不足。我們需要的是什麼?而且要如何重組市場才能達成這個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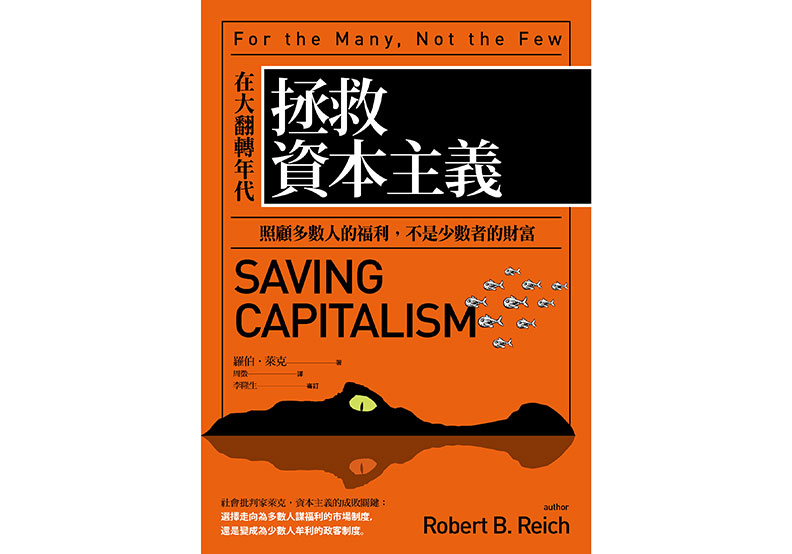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一書,羅伯‧萊克(Robert B. Reich)著,周徵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Alex K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