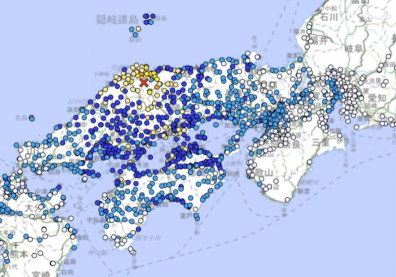第一位獲得瑞典學院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高行健,其最新舞台鉅作「八月雪」即將於今年12月在台面世。
為了這項跨不同表演藝術領域的實驗作品,文建會耗資新台幣1500萬元全力支持。
「八月雪」的劇本早已完成,但要其實現、展演成表演藝術,困難重重。高行健卻要知難而行。「我們不套用現成的模式,專挑困難的做,」高行健說。
高行健以文學作品得到諾貝爾獎的殊榮,但他不只在文學領域上出類拔萃,更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
法國馬賽市政府預計動用100萬美元的預算,為他籌劃「高行健年」活動。這是馬賽市少見僅僅為單一藝術家舉辦一整年的大活動。
「高行健年」囊括了造形藝術、戲劇、歌劇、電影,活動包括高行健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高行健的新戲劇作品「叩問死亡」,以及高行健的造形展覽、行為藝術作品等等,而他所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也預計於2004年1月首演。
「八月雪」是馬賽歌劇院和台灣文建會共同合作的新歌劇,將於2002年12月19日起在國家劇院演出五場,在台首演時,包括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及歐美策展人都會來台觀賞;2003年10、11月再轉進馬賽歌劇院上演長達一個月。
實驗性質濃厚
高行健作品的特質向來具有強烈的實驗性和前瞻性,「八月雪」也不例外。「它是一齣實驗性質濃厚的新劇種,」文建會主任委員陳郁秀說。
「八月雪」的故事主軸是六祖慧能的禪悟過程,而舞台表演形式則對中國劇場與西洋劇場的歌、樂、表演進行新的探索。
「八月雪」的意境像是幽遠的水墨畫,輕筆勾勒出禪者胸中的山壑。高行健希望闡釋出宗教不成為一種壓迫、一種政治權力的意義。在這個前提下,會喚起憐憫。「慧能的故事,或許可以喚起這個社會或人都會平和一些、寬容一些,」高行健說。
在高行健的眼中,六祖慧能是一位思想家。「慧能不做教化,不認為自己是救世主,認為大家應該自救,」高行健解釋說。
人的解脫、得救或覺悟是在自己。過去的世紀,知識分子通常都把自己當作救世主,或者變成法官、裁判,但高行健認為,知識分子其實不能承擔這麼沉重的任務。
在形式上,「八月雪」既非歌劇、京劇,也不是話劇、舞劇。「它是四不像,」高行健說。
如何運用形式來達成幽遠的意境?「我要挑戰自己,」高行健表示。
曾經編導過十六齣戲的高行健解釋,他的每一齣戲都沒有重複。不斷創新帶給他數不盡的壓力及困難,不過,困難會過去,他以「無所不難」,但是卻「知難而上」來形容編導「八月雪」的心情。
長期以來,高行健一直夢想編導一齣集合東西方戲劇,但又與東西方戲劇沒有關連的新戲;參加演出的演員要會唱、會舞、會演、對白要漂亮。
導演在摸索,對於演員挑戰難度更大。「八月雪」的音樂非古典、也非現代,京劇演員必須改用歌劇的聲音來演唱,拿掉原來京劇的聲調唸口白,而且還要會看譜。
高行健選擇的京劇演員們從來不知道,怎麼唸口白才能跟著指揮走?
但是,所有的參與的藝術家都在知難而行。
編舞二十年的林秀偉,頭一次被導演打回票。主角吳興國也好不到那裡去,為了一幕一分鐘的表演,吳興國從繁複的肢體語言,一路修正,修了快十次才符合導演的要求,「連我自己都快被打倒了,」吳興國說。
奧斯卡美術設計得主葉錦添也挑戰自我。一般人看不出來衣飾裡暗藏玄機,他卻要讓表演者舉手投足間充滿了語言。「演員不動時像一幅靜態的畫,一動就有數不盡的變化,」葉錦添說。
林秀偉形容這是台灣藝術界「共修」的機會,而她也從這次共修中,突破以往既有形式,有了一個再審視自己的機會。
雖然挑戰性很高,所有的藝術家卻反而覺得很輕鬆,葉錦添形容大家會感到輕鬆的原因,是「碰到對的人。」
高行健和所有參與的藝術家都很快樂。只要理念相同、有交流,就沒有負擔。「理念愈相同,做出來東西就會愈細,且不著痕跡,看不見我的,也看不見他的,就對了,」葉錦添說。
不過,外界對於文建會支持高行健「八月雪」,卻出現許多不同的聲音。
一位重量級的表演藝術家認為,「八月雪」並非固定班底的演出,演完就消失了。「如果是固定戲劇團的演出,我會支持,」這位藝術家說。
代表台灣在世界舞台發聲
但是,陳郁秀堅持的原因是「八月雪」的每一步都是創作。
從藝術家眼光來看,陳郁秀認為,「八月雪」最大的藝術價值,在於整個創作過程充滿挑戰與創造力。
「八月雪」每一步都是創作,也是挑戰。不但是高行健個人,也是集體的挑戰,能不能成功,對每個人都是問號。
彙集國內外戲劇界精英一同參與,累積相當分量的藝術能量。除了由高行健擔任導演,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校長鄭榮興擔任製作人之外,在音樂部分由大陸旅法作曲家許舒亞負責作曲,服裝、舞台設計分別為葉錦添、聶光炎,由國內知名的現代舞家林秀偉擔任編舞,燈光設計則為法國的Grosperrin Philippe。演員部分則由吳興國飾演六祖慧能,其他參與演出人員還包括葉復潤、曹復永等著名京劇演員。
原本不在「八月雪」編制內的聲樂家李靜美和甫在蕭提國際指揮大賽獲獎的江靖波,也在陳郁秀的請託下分別將擔任藝術總監和助理指揮。
集合跨國、跨領域的藝術合作,「八月雪」會為台灣戲劇界激盪出最大的能量,並且代表台灣在世界舞台發聲。「歷史上將會記載著『八月雪』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台灣發生,」陳郁秀說。從文化政策決策者的角度來看,「『八月雪』更可以證明台灣是個容許創意呈現的地方。」
台灣是一個容許理想、創意、幻想,同時,也有勇氣去實踐的地方。當全新的劇種在這裡產生,「世界會知道,台灣是個可以促進藝術品產出的國家,」陳郁秀說。
「八月雪」對高行健本人也很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八月雪」舞台劇是高行健穿越中國大陸到一個寬廣的世界之後,卻又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創作的作品。
藝術從來沒有疆域,莎士比亞的作品讓全世界的人都震動,因為他的作品自然超越了國界,也超越了語種。
「八月雪」能不能打破語種、文化甚至政治的藩籬?在國際藝術史上寫下新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