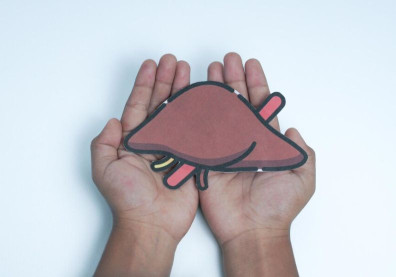楊乃藩/反應快、有急采的主筆
在中國時報執筆寫社論十七年整的楊乃藩,愈來愈加肯定社論可能發揮的影響力。
楊乃藩是新聞界有名的一支飛筆,同儕公認他「反應快、有急采」,他也樂言自己的寫作數量之豐、速度之快,少有人及。
頻率最高的時候,一個月三十篇社論裡,有二十多篇都是他寫的。舉凡經濟、社會、政治,只要涉及大眾關切的新聞事件,他都能在兩個小時左右,揮就一篇一千八百字的專評。
他寫的社論原則上是反映新聞。每早讀完報紙、看完電視新聞後,便和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商定題目,下午交稿;如有突發事件,他則漏夜臨場反應。
他形容自己落筆的取向是:「定論要有特色,使內容突出,不講模稜兩可的話,一結果,「有的立竿見影,有的經過長時間終於看到影響。」
建議多具體可行
七十二歲的楊乃藩曾經分別得到新聞局金鼎獎,及吳舜文新聞獎的「新聞評論獎」,得獎評語中都包括「所提建議多屬具體可行。」
例如,他從民國六十七年起陸續寫過二十八篇有關票據法刑責的社論,去年立法院正式通過廢除刊責的議案。兩年多前,他針對石門水庫大壩安全面臨挑戰為文,一個多月後,行政院長俞國華便指示省政府不得在壩上停車,同時停建有礙安全的建築,省府並發佈石門水庫易長的命令。
觀察的人指出,楊乃藩的社論稿所以能適時反映當前的社會情形,是因為他真正關心社會上發生的事,並具有新聞記者的眼光,「不是一位關在房間裡的主筆。」
事實上,楊乃藩交遊廣潤,閱歷豐富,雖身為主筆,仍經常到處參加會議,消息靈通。他本身就像一個記者,也是一個作家。
他曾任台糖公司主任秘書,二十年間,每期都替台糖通訊寫首頁的社論--小言,所取題材廣泛;又以任堅的筆名替中央日報寫了十年的小方塊。此外,他還曾經為財經首長幕後代筆撰寫講稿,自已又把旅遊四十多個國家的經驗出成遊記,這樣的經驗,使他碰到任何題目,都能快速的進入狀況。
他相信,社論作家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立場明確、反應快、具通才。一篇評論中肯而確實,就能引起回響和效果。
(溫曼英)
戴瑞明/媒體言論尺度的協調者
在各類意見領袖中,文工會主任戴瑞明相當特殊,因為他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執政黨的意見。他在幕後指揮運作,由屬下打電話給媒體,表達對處理某些新聞的期望與意見,被視為「協調」傳播媒體言論尺度的「一隻看不見的手」。
然而隨著台灣政治舞台空間的改變,外交官出身、曾任新聞局國際宣傳處處長、副局長的戴瑞明也嘗試調整他所扮演的角色。
解嚴之後,幾位報社高級主管不約而同地感到,來自文工會的電話似乎比過去少,而且態度相當客氣。戴瑞明也打破歷屆主任不對外界發表有關新聞協調意見的常規,接受本刊訪問。這些皆反映執政黨的觀念和做法已因社會變遷有所轉變。
「不做才是失職」
身材瘦長,戴金邊眼鏡的戴瑞明並不諱言,過去由於執政黨是個勢力極大的黨,往往帶給媒體較大的壓力。但在民眾政治參與需求日增的情況下,這種壓力逐漸減退。一位熟悉內情人士指出:「文工會未來想協調非黨營媒體,將愈來愈難。」
這對上任不到一年的戴瑞明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他認為,新聞協調是為了黨的利益,而今天黨的利益與社會、民眾的利益是相結合的,「否則我們怎麼能執政呢?」因此儘管有人不諒解,協調過程會有挫折,但基於職責仍須去做,「不做才是失職。」他說。
那麼文工會協調新聞的原則為何呢?戴瑞明指出,要能闡揚黨的政治主張,例如:「蔣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表示要反共、反分離,我當然要協調各媒體多報導。」但若是示威、打架這類事,則「希望媒體審慎處理,不要造成人心浮動,妨礙社會安寧。」
須更具說服力
但是戴瑞明也發現,文工會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未必與新聞媒體一致,尤其是報禁開放後,各報競爭激烈,更須各自凸顯特色,也更可能走上較刺激聳動的路線。 為了因應局勢的變化,未來文工會一方面要「對自己的黨營媒體多做要求」,另方面「多為新聞界提供資訊服務」,例如舉辦政策背景說明會來推銷自己。不過,「電話還是要打,但須更具說服力才能奏效。」一位消息靈通人士認為。
社會日益開放,朝野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力增加,對很多事也較能以平常心看待。一位黨營媒體高級主管舉例指出,過去文工會對街頭示威的報導皆不予考慮,現在則「可以坐下來商量」。而未來其他政黨陸續出現,他們也會用各種方法透過媒體宣揚主張,執政黨文工會的做法也不會再予人「獨霸」之戒心。傳播界人士因此預測,「時勢造英雄」的結果,戴瑞明在媒體心目中,極可能成為歷任文工會首長裡最開明的一位。
(楊小萍)
蕭新煌/不迴避爭議話題的學者
在經常面對新聞媒體的學者專家中,蕭新煌是廣結善緣、成果豐碩的一位。
他持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頭銜回國九年以來,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評論性文章已超過一百萬字,這一百萬字結集成冊,使年方四十的他憑添了六本著作。
六本書的題材從環境保護、消費者運動到國家發展、社會轉型……,其中有專文,也有參加座談會及訪談的紀錄,充分反映出這些年間他的言論涉及的範疇。
除了言論參與之外,他還以創會董事的身份,實際加入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工作。他自認,「我在美國所學的既不是消費者保護,更沒有事先的計畫要親自投入消費者運動,既沒有學術理由,也沒有想過要做一個社會運動的實踐者,有的只是一股「平常人」的社會關心。」
這樣的關心,造就了他雖身為偏處南港的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但卻常出現在不同的場合,幾乎每天都要趕文章、演講、座談或接受訪問的忙碌生活。
有些和地背景相同的學者,對他「外務頻繁」的奔波狀態不以為然,「學術中人應該專注」,批評的人說。
然而,也有些人客觀分析,他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儼如意見領袖般地崛起於台灣社會,確實有異人之處。
一位接近他的學界人士指出,他的口才好、腦筋快,對問題的剖析能力強;儘管有時候看法不見得成熟,但他不畏懼表現自己的意見、也不拘泥於學術的自我設限,不迴避可能引起爭議的話題,因此展現出多角度的社會關心。
和新聞界關係良好
他對社會的關心能廣為披露,事實上,植基於他和新聞界良好的關係。
「他言論的調子適合媒體的需要,」一位報社資深記者認為,蕭新煌所以受媒體歡迎,一方面是因為他能在短時間內,針對某些問題給予確定的答案,而答案正能配合報紙所需;另一方面,他所選擇參與的社會運動都沒有政治疑慮,見報的機率自然較高。
隨著日漸增面的知名度,蕭新煌似乎面臨欲罷不能的處境。最近,他甚至為台籍老兵的組織寫文章、做顧問。「他們需要我的名字,」他說。
不過,嚴肅地追究起他個人的終極目標,這位左右逢源的意見領袖表示,「還是喜歡當學者,效忠學術」。
他強調:「過去言論環境不是那樣自由、開放,社會學家有較被寬容的言論空間,發表意見是一種義務;現在解除戒嚴,言論尺度放寬了,社會上真正需要的,將是更多的思考。」
(溫曼英)
黃主文/在兩黨間走鋼索的民代
在諸多立法院的「明星」委員之中,跟趙少康、朱高正、李勝峰等人相比,黃主文顯然不是最耀眼的一個,但細數他的質詢主題,他卻無疑是國民黨立法委員中,質詢言論最鋒利的一位。
他擅長在微妙的政治言論中「適時」順應潮流,在各方言論若隱若現、欲語還休式地討論敏感的政治問題時,黃主文總是單刀直入,率先質詢。像著名的信心危機問題,就是他在立法院率先發難,引起輿論熱烈討論。
其他像票據法修正案、釋放票據犯、探親、戰士授田證問題,也是由他掌握機先,使質詢成為翌日報紙的頭條新聞。
黃主文的助理汪臨臨,形容國民黨對他是「又愛又恨」。十信事件是個典型例子。當時,黃主文發表「從責任政治到政治責任」的質詢稿,猛力抨擊財經部長,要他們負起政治責任。促成兩位部長先後下台。黨政保守派先是批評他過於激烈;事後又稱他顧全大局。因為當時反對派勢力企圖將十信事件,升高為倒閣的洪流。黃主文的質詢無疑將這股洪流,牽引到另一個對執政黨傷害較小的方向。
「做政治人物就要有政治勇氣,政府保守,要大力推動才會進步;我只是勇敢反映民意而已,」四十七歲的黃主文,質詢稿上雖然總是言論激烈,私底下的言談卻很平實,有時甚至有點木訥。
只是勇敢表達民意
從某個角度觀察,黃主文的出現,象徵時代的一次急變。在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民意的空間比過去寬廣,過去深埋在議事話題外的憲政、體制問題,在反對黨的激盪下,一一浮現。台大法律系畢業,曾擔任司法官的黃主文,適時而聰明地掌握這種政治新興力量,使自己的言論永遠是最熱門、尖銳、又不致出軌的政治話題。
從見報率勇冠立院,可以證明這種策略的成功。據汪臨臨統計,在黃主文四年立委生涯中,除了第一次總質詢的新聞,「沒有被報社做大」以外,其後所有總質詢稿,「每次至少都成為某家報社的一版,或二版頭條新聞」。
他的質詢內容有新聞價值,只是這種聲勢的推動因素之一;而他的助理,現任國會助理聯誼會會長的汪臨臨,更是幕後大功臣。
不失耿直的性格
汪臨臨所發揮的功能,頗能模仿西方先進國家國會助理的模式,不但以明朗筆調替黃主文撰寫大多數質詢稿,更重要的是替他結交記者。
到現在,另一位委員助理指出,汪臨臨甚至能事前判斷什麼樣的質詢稿,能上什麼報,能有多大篇幅。甚至黃主文在質詢時,事先都知道那一家電視台,幾點幾分會來拍攝他的畫面。
總體而言,黃主文陣營雖然善於結交媒體,但他仍不失耿直的性格。像國民黨最近有意提名他為立法院立委總部常委,被他拒絕。黃主文放棄這個許多人爭取的位子,主要是因為一旦坐上這個位置,為了顧慮黨德、黨紀,可能從此無法暢所欲言。
「知識份子在社會,經常要扮演反對的角色,社會才能進步,」黃主文如是說。看來,這位正處壯年的立委,仍執意繼續走在鋼索上。
(文現深)
楊憲宏/提供另一種選擇的記者
楊憲宏是記者,但他不是普通記者。他所寫的特稿,常常像一顆炸彈,震動整個社會。
多氯聯苯污染米糠油事件、翡翠水庫面臨污染事件、味全新AGU奶粉磷鈣含量比例不當事件、餿水油收回再用事件、石門水庫大壩沈陷事件等,透過他的筆,都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也為他贏得六次新聞報導獎。
他的表現如此不凡,很快成為聚光燈尋找的對象。各種演講、座談、訪問,「幾乎每週都有,」他表示:「全年近五十次。」
除此之外,他也在其他地方寫稿。「我也是自由作家,」他質問:「為什麼我除了做聯合報記者之外,就不可以有其他角色?」
除了與他本行有關的環境保護運動、公害防治運動外,他參與新電影運動、研擬電視改革,也經常為「民進黨」主要成員提供意見。他解釋說:「社會上充滿了各種是非題、選擇題、問答題,每一題我都有興趣。」他覺得這像是一場很大的電腦遊戲,「我參與其中,擔任角色」。
這樣的參與態度,令一些同業不以為然。聯合報一位資深記者使認為,他涉入報導主體太深,有違新聞記者公正客觀的原則。尤其在一些報導中,他似乎「太情緒化」、「個人主觀判斷很強」。一位與他合作過的記者勸他:「應該是記錄歷史,而不要嘗試去改變歷史。」
只是提供別種選擇
他反駁說:「新聞界對「客觀」的認定根本有問題。」爭執雙方的意見都登,便是客觀、均衡的報導嗎?「我認為真正的客觀是提供民眾另一種選擇。」
他承認,自己也常面臨「要不要這麼做」的抉擇;「幾乎可以看到,一個系列報導寫出來,社會往這個方向去;不寫,社會往另一個力向去。」這是不是企圖改變歷史?「不,」他搖頭:「我只是提供別種選擇。」
他也承認自已有犯錯的可能,有判斷錯誤的時候。但他相信即使有錯,也不會很大。「當我難以判斷的時候,我選擇站在弱者那邊」。他認為這是唯一的方法。這樣做,「晚上比較睡得著,」他說。
楊憲宏以「專業記者」著稱,但他表示自己憑藉的並非醫學、公共衛生力面的專業知識,而是科學教育的邏輯訓練。因此他不必瞭解核能和二氧化鈦,照樣可以「推出反核能、反社邦的理」。「我寫的不是什麼高深的東西,而是一般人都看得懂、可以檢驗的。」他信心十足。
(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