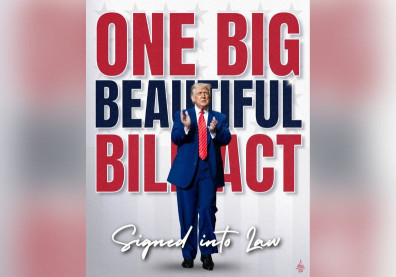在人權團體工作期間,有一幅畫對我影響甚深,那是二○一二年秋天,一名十一歲小女孩以不熟練的手法所畫。圖畫紙左半邊用拳頭大的字體寫著「不要歧視其他國家的人」,下方則有三個大塊頭的孩子並肩站立,朝一名獨自站得遠遠的瘦小孩子大喊:「走開!你和我們不一樣!」
這個瘦小的孩子挺身對抗三個大塊頭的孩子,如此爭辯:「才沒有!我和你們是一樣的!」
小女孩就是這個瘦小的孩子、也是圖畫創作者,她是由韓國父親和越南母親的多元文化家庭中的孩子,也是我在人權團體撰寫要呈交給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報告時訪問過的孩子。
她如此說道:「小時候,大家老是說『妳和我們不一樣』……我說話的發音很奇怪,所以後來大家就(對我)說:『妳和我們不是同一種人吧?走開一點。』總是嘲笑我……(學校)不是都會要求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舉手嗎?結果舉手的就只有我一個,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他們家好像是多元文化家庭耶。』」
「同樣都是人,只是語言不一樣而已,不需要特別強調是多元文化家庭,而且(聽起來)很討厭。」這個孩子說。
幾天後,我聽到一群活動人士到仁川一所高中支援學生社團活動的經驗。社團的孩子以同校學生為對象,親自做了多元文化相關問卷調查,其中有一道問題為「寫下平時提到多元文化家庭的兒童時,腦海會浮現的兩個詞」,最常見的回答如下:
「排擠、骯髒、外表、溝通、非洲、巧克力、炸醬麵、黑人、不幸……」
在那所學校的學生中,沒有任何一個孩子能夠單憑外表就立即認出他來自多元文化家庭。無論回答問卷的學生是否實際見過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他們對於貼在「多元文化」概念本身的嫌惡標籤,著實令人吃驚。
曾朝著長相和我不同的人大喊:「你和我們不一樣,走開一點!」這種內化的態度如今是否有所改變呢?在大人之間會有不同嗎?
令人遺憾的是,情況似乎並非如此。根據女性家庭部發表的〈二○一五國民多元文化包容性調查〉結果,可得知每十名國民中就有三名(百分之三十一.八)不願和外籍移工(或移民者)為鄰。
若和國際調查專門機構「World Values Survey」在二○一○到二○一四年的調查中相同的項目比較,表示不想和外國人為鄰的韓國人是美國(百分之十三.七)的二.三倍,澳洲(百分之十.六)的三倍,瑞典(百分之三.五)的十倍之多。
政府和學校的多元文化政策、大多數課程仍侷限於以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為對象。因無法適應學校而中途輟學的小學生中,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就足有其他家庭的四.五倍之多。即便是在多元文化家庭的子女超過二十萬名的現今,這些孩子經歷的困難仍和七年前大同小異。
韓國是種族歧視共和國
目前居住於韓國的外國人已達到兩百萬,可是對於移民者,特別是膚色黝黑,來自於「比韓國貧窮的國家」的外國人,韓國的歧視和嫌惡仍很嚴重。「血統純正的韓國人」成為「正常家庭」,而屬於「不正常」的多元文化家庭、移工、移民和他們的子女則遭到歧視。受集體主義的家庭價值影響,韓國人排斥外來的群體,表現出極端的譴責態度。也有研究指出,注重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和強調血統的國民特質越顯著,就越可能對多元文化展現出排斥態度。
雖然不曾像美國一樣表現出露骨的種族歧視,但我認為韓國是一個有種族歧視的國家。根據二○一七年國家人權委員會發表的〈嫌惡表現實際情況調查與規範方案研究〉,有一半以上在韓國任職的移工曾從他人口中聽到嫌惡的措辭,並對此心生畏懼。
在這些嫌惡的措辭中,可得知韓國社會將移工視為「骯髒、身上有味道,想避而遠之」的人,他們是「未開化、無知、懶惰並且見錢眼開」的群體,同時也是「到別的國家搶工作的群體」「潛在的恐怖分子」「被買來生孩子的可憐之人」。
光州大學教授勇比.多納(Yiombi Patrick Thona)#(編按:勇比.多納申請難民庇護來到韓國,因不同種族的身分受到歧視。後來開始在媒體上傳達尊重所有種族、性別和難民權利的觀念。)來自剛果共和國,其難民身分獲得韓國認可。因為太常在路上聽到別人說他「真的好黑」,稱呼他為「黑人大哥」,所以當他到了對自己毫不關心的外國時,反倒會渾身不對勁。
單純只因為不同,還有因為那份「不同」而給他人貼上「劣等」標籤的行為雖是一個問題,但我認為最嚴重的是,歧視那些不僅無法自行選擇父母,而且不管是否出自個人意願,跟隨父母來到韓國生活的移居兒童,在制度上的歧視也根深蒂固。
國內未登記的移居兒童推估約有兩萬名。因簽證過期或未申請外國人登錄證而處於未登記狀態的移居兒童,想必是生活在韓國這塊土地上的孩子中,處境最為惡劣、身在「死角中的死角」的孩子。政府批准的《兒童權利公約》規定,不分國籍、人種、社會身分,所有孩子都不應該受到任何歧視。但別說是管理未登記的移居兒童了,管制和被驅逐出境的風險,導致他們連最基本的權利都無法享有。
二○一三年,法務部做了一項變更。如果未登記的移居兒童正在求學,則將強制出國的期限放寬至完成高中學業為止。雖然只是將過往到國中為止的限制稍稍放寬而已,但這細微的變化,如果沒有人權團體聯手爭取移居兒童的權益,根本不可能實現。
當時的變化源自在韓國生活十年、突然被驅逐出境的高一學生民宇。七歲時,民宇便隨父母從蒙古移民至韓國,直到高一為止,已在韓國居住長達十年,因此韓語能力比母語更流利,他也認為自己是韓國人。某一天,勸阻朋友吵架時的偶發事件改變了民宇的人生。他為了幫忙翻譯,以關係人的身分來到警局,結果被揭發其未登記的身分,隨即被送到外國人收容所。和大人被關在同一個房間的民宇,明明就不是罪犯,卻在五天後戴著手銬被移送到機場,強制驅逐出境。在這期間,父母一次也沒見到。
多虧當時移民人權團體鍥而不捨的追究,法務部才做了些微調整,但民宇必須一直和父母分隔兩地生活。
還不只如此。在中國出生的毅寒,因母親獨自移民到韓國,由親戚撫養長大。在毅寒國中畢業時,母親要他搬到韓國,母子終於在久別十五年後團聚。就在毅寒打算在韓國上高中時,學校以他「不諳韓語」為由拒絕入學。學習韓語約一年半後,他申請了多元文化特色高中,但是學校要求他繳交家族關係登記簿、住民登記謄本等唯有韓國籍學生才有辦法繳交的資料。於是,基於「缺少具備能證明其為國民子女的資料」,毅寒的入學申請再次遭到拒絕。就連多元文化特色高中都不願接納毅寒,他究竟要上哪兒求學呢?
因為不具有韓國籍,所以當移民者的子女受虐時,也無法受到兒童保護專門機構保護,當他們走投無路時,也不能求助於社福機構。在這兒生活的移民子女,只不過是不具有國籍和滯留資格而已,「正常的韓國人」卻如此殘酷的對待他們,從制度上封鎖了他們接受教育、醫療服務和免於受到暴力的權利。

本文節錄自:《異常的正常家庭》一書,金熹暻著,簡郁璇譯,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