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定要幸福?如果在極小範圍內界定「幸福」的話,接下來阿蘭著名的說法可以算是其中一個答案──「保持快樂也是我們對他人應盡的義務 」。好心情和壞心情都很容易影響到周遭的人,為了讓身邊的人開心,自己也非幸福不可──這是阿蘭的想法。
這是很美好的回答,我認為它包含了某種面向的真實,但也是太過美好的答案。如果是我的話,頂多會持保留態度說:「不讓自己不開心,也是對別人的義務。」「我」的不開心,確實對身邊的人或對「我」自己都帶來壞處。不過如果有人說:「歡天喜地也是在盡對別人的義務。」很遺憾,那是在騙人。因為開心有時也會傷害到別人哪。再加上如果以阿蘭的說法作為基礎,甚至說出「讓別人幸福是義務」的話,就不能迴避接下來的這種抗議。
以讓他人幸福為己任的人,往往都像阿蘭般怡然自得擁有主流的感受性。毫無理由地就以為所有人的欲望、感受、興趣和嗜好都一樣,不願意面對讓別人幸福是無比困難的事。
──《不幸論》
「幸福」是多義而複雜的,要像阿蘭那麼漂亮地回答本章開頭的問題並不可能。和「幸福」這個詞的複雜程度相應,就必須要有複雜的回答,所以需要本章接下來的哲學思考。
「為什麼一定要幸福?」我起初覺得這真是奇怪的問題。但是,「幸福是什麼?」這問題也有許多答案,而且那些答案裡還有一些不可能同時成立的情況。關於特定意義的幸福,問「為什麼要幸福」有其價值。像〈序言〉裡所見,關於「幸福是什麼」的各種說法同時論述了「為什麼──關於某種意義下的幸福──應該幸福嗎?」
我們來想想「快樂說」、「欲望滿足說」、「客觀清單說」這三個關於幸福的代表學說互相衝突的狀況吧。快樂說和客觀清單說衝突的情況,或是欲望滿足說和客觀清單說衝突的狀況,都很容易明白。這些可以視為「主觀幸福要素」和「客觀幸福要素」的衝突。
需要稍加思考的是快樂說和欲望滿足說相衝突的情況。這是兩種主觀要素偏離的狀況。雖然快樂,但欲望未達到滿足,是第一種偏離。不快樂,然而欲望被滿足了,是第二種偏離。前者的話,可以舉出像是因為廣義的錯覺而得到快樂的例子:某人買下了名畫,非常快樂地過了一生,但那幅畫其實是偽作。後者則有下面這種例子:某人想成為有名的畫家,但終身沒沒無名,死後作品受到好評而成為著名畫家。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項。在某個意義上的幸福和別的意義上的幸福無法並立時,理由常常是因為兩種幸福的實現偶然不可能並立的事實。像是,兩種行為──任何一個都連結到某種意義的幸福──無法同時成立,這類能力上的問題(因為身體、時間、金錢等其他限制),我們只好優先選擇其中一個,而這個選擇裡絕對不包含「沒被選擇的行為前方是虛假的幸福」。
用文字表現或許有些抽象,一時可能無法理解,但我說的是很普通的道理。例如明天放假,有一個選擇是為了開心而去遊樂園玩,另一個選擇是為了未來的欲望滿足而準備考試,此時並不表示沒做的那個選擇是虛假的幸福。因為「在遊樂園一邊玩樂的同時一邊準備考試」這種偶然是不可能發生的,幾乎所有人類的能力都很偶然地就只有如此,若能同時做到兩種,大多數的人就會選擇同時滿足了吧。
所以,關於個別的幸福,問出「為什麼要幸福?」的問題時,若把這個疑問改為關於「什麼」的問題,也就是轉而去問什麼是真正的幸福,是言之過早。個別的幸福有它們能實現的理由,即使是無法兩全的幸福中,也不能說其中一方的幸福就是假的。烤一片牛排時不可能同時烤成三分熟的和全熟的,不代表其中一種烤法是假的。而且,三分熟有三分熟的好處,全熟有全熟的優點,它們有各自存在的理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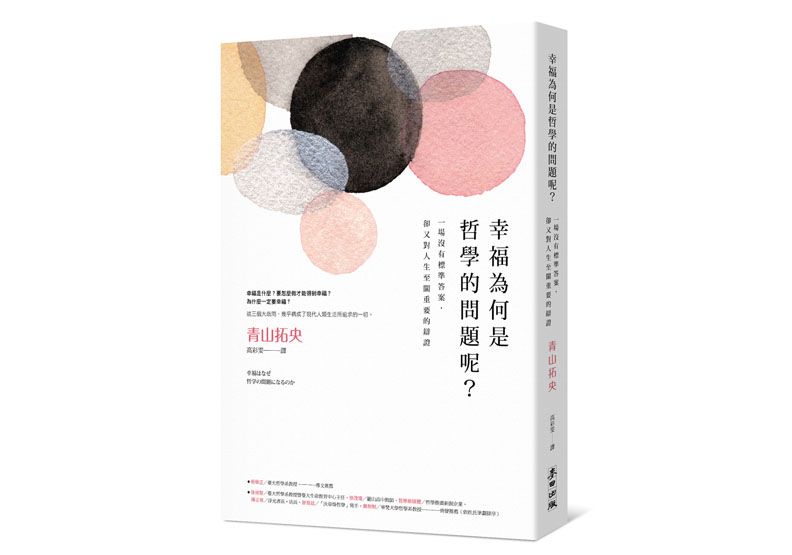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幸福為何是哲學的問題呢?:一場沒有標準答案,卻又對人生至關重要的辯證》一書,青山拓央著,麥田出版。
本文節錄自:《幸福為何是哲學的問題呢?:一場沒有標準答案,卻又對人生至關重要的辯證》一書,青山拓央著,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