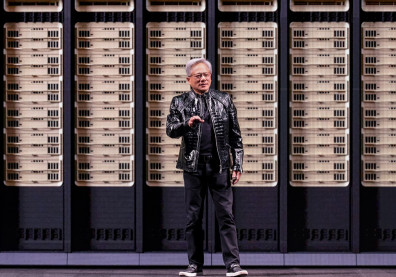那年過年,照樣留在醫院值班。凌晨五點正在值班室躺一下休息,接到了護理站的電話:「朱醫師,〇二二床鼻胃管自拔,要重新放。」
我翻了個白眼,又是自拔,早上五點耶!很不情願地準備好需要的用品:鼻胃管、手套、潤滑凝膠、聽診器,往病房走去。
〇二二病人是一個七十五歲的沈爺爺,聽說以前是將軍,威風八面。但好景不常,五年前開始失智,三年前腦部大面積中風,從此無法走路、說話、上廁所,只能終日躺在病床上。他這次因為肺炎併發敗血性休克送到醫院來,狀況其實不太好。
他住在單人房,走進病房,一股尿騷味混合著食物的味道迎面而來,映入眼簾的沈爺爺蜷縮在病床一角,他好瘦,幾乎只剩下皮包骨了。因為床躺久了,手腳關節缺乏活動都攣縮了。我想是因為他又自拔鼻胃管的關係,所以他的雙手都用了保護手套套起來,手套的另一端用棉繩綁在病床欄杆上。
病床旁邊看似坐著他的太太、兒子和女兒,每個人都焦慮地看著我。
「你們好,我來幫伯伯重放鼻胃管。」我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這麼早還要麻煩你。」奶奶很抱歉地跟我說,我沒有回應,就開始我的工作。
不料,平常理應是在十分鐘內就可以完成的任務,那天清晨很不順利。
放置鼻胃管,是從病人的鼻孔中把管子插進去,經過咽喉進入食道直到胃裡。其中需要病人配合吞嚥。意識清楚的人能配合吞嚥,管子通常很快就可以進入食道。
但是沈爺爺,說什麼就是不吞。
過了三十分鐘了,管子都無法進入食道,一直從嘴巴跑出來。
「伯伯,要放了,你要吞口水喔!吞口水!吞!」我在伯伯的耳朵旁邊大叫,但他不理我。我當時真的很生氣,但一個失智又中風的病人,如何能配合我呢?
更辛苦的是,每插一次管子,就會刺激他的鼻腔和咽喉,引發咳嗽反射,所以我一邊插,伯伯一邊咳,感覺幾乎要把肺咳出來。沈爺爺咳到眼淚直流,儘管他失智又中風,但是他的眼神還是憤怒地一直瞪著我,好像我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
奶奶看到她先生這樣,也忍不住掉眼淚,跟旁邊的女兒說:「我們不要放了好不好,他以前就很不喜歡鼻胃管,他好辛苦、好辛苦……」女兒挽著媽媽的手,看起來也很難過。不料,坐在一旁角落的兒子聽到這句話大聲地斥責奶奶:「說這什麼話!不放管子怎麼吃東西!怎麼會有營養!醫師,你不要聽她的。」奶奶被兒子一唸,不再說話。
我只是個小實習醫師,也很無奈,只能繼續做事。從左邊鼻孔插,失敗,伯伯咳個不停;從右邊鼻孔插,還是失敗,伯伯咳個不停,眼淚又流出來。插到最後,伯伯知道我要插了,頭就一直扭動,不讓我插,她的兒子和女兒只好用力把伯伯的頭固定住,好讓我做事。
伯伯的頭被四隻手卡住,頭歪一邊,眼神還是直瞪著我。不知為何,直到現在,我還會想起這個充滿了情緒與悲傷的畫面。
經過了九十分鐘的鏖戰,管子終於進去了。用聽診器確認,確定位置是在胃裡面,大功告成。我全身大汗,衣服都溼透了。
奶奶、兒子和女兒不住跟我道謝,臨走的時候,還聽到兒子打電話跟護理站說:「麻煩你們把我爸手綁緊一點,免得他又拔管子。」
我默默走出病房,天亮了。
*
很多實習醫師不喜歡鼻胃管,我想是因為,在一次又一次地插管子,與病人一次又一次地拔管子之中,被插拔的已經不只是那根管子,而是病人的意志、家屬的期待和醫療的無奈在互相拔河,同時還混雜了好多種無法名之的情緒。身為小醫師,那些都是我們無法處理的,我們只能奔走在病房之間,繼續插那個被拔掉的管子。
我常常想起沈爺爺瞪我的眼神,想著如果我是健康的他,我會怎麼做?如果我是生病的他,我又會怎麼做呢?
親愛的朋友,你會怎麼做? 本文節錄自:《人生最後的期末考》一書,朱為民著,商周出版。
本文節錄自:《人生最後的期末考》一書,朱為民著,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