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霸凌
身為教室的領袖,老師可以透過很多做法防止霸凌,也就是說,你絕對可以在霸凌開始之前就加以遏止。前文提及的諸多策略:認識每一位孩子、和學生玩耍、慶祝學習成果、追求班級夢想,其實都是在支持這個目標——當你強化班級裡的歸屬感,就是在預防霸凌。然而,有時候雖然我們已盡力提倡班級裡的正向互動,但霸凌行為還是可能發生。一旦碰上這種狀況,教師絕對不能姑息,必須立即處理。
根據美國全國科學、工程與醫學學院(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的報告,有一八%〜三一%的美國孩子與青少年曾遭受校園霸凌。儘管各界對於霸凌的定義不一,但記者羅珊.卡西(Roxanne Khamsi)已明確地指出:「霸凌最常見的定義就是重複、刻意的攻擊性行為,加害者擁有更大的權力——無論這個權力失衡是真實存在,或是想像出來的。」
住在美國時,我教過兩所公立學校和一所私立學校。每所學校都有很合理的預防霸凌的對策。除了固定的全校聚會、反霸凌工作坊(workshop),學生還共同簽署了一張很大的海報,誓言反抗霸凌。這些都是很好的預防對策,但我仍舊沒有看到任何可讓全校共同面對霸凌行為的流程機制。
十多年來,芬蘭一直在尋找處理學校霸凌的策略。在赫爾辛基學校,我見到全國最受歡迎的反霸凌計畫,稱為「奇娃」(KiVa),有九○%的芬蘭學校都在執行。「奇娃」在芬蘭語中是「反霸凌」的意思;這同時也是個雙關語,「奇娃」的發音和芬蘭語的「善良」很相近。
這個全國反霸凌計畫看起來非常有希望。針對芬蘭學校七千位學生的研究顯示,奇娃明顯改善了兒童的精神健康,這也是他們最常受到霸凌的部分。
邀請高年級學生參與霸凌會議
奇娃的策略包括:預防學生收到關於霸凌的宣導資料(例如:電腦軟體),在教室裡進行角色扮演。我在赫爾辛基教書時,則看到奇娃的另一項優點:當霸凌發生時,便有一系列清楚明快的處理步驟開始運作。這次寫作時,為了確認奇娃的完整步驟,我和赫爾辛基的同事寶拉.哈巫(Paula Havu)聊了一會兒。她曾參加反霸凌的訓練。
假設學生之間有了衝突,一個孩子指責幾個同學有類似霸凌的行為,例如:經常不讓他在操場上一起玩,這個學生可以請老師召開一次奇娃會議。(旁觀者也可以要求開會,例如:看到霸凌行為的老師和學生。)老師和學生們都得先填一張表格,簡單描述經過,並同意協商的日期和地點。之後,老師會把這張表格放進特別的檔案夾。奇娃教師團隊會固定檢查檔案夾,若有需要,他們便會通知高年級的學生團隊,這些學生接受過訓練,知道如何處理這類衝突。
解決霸凌問題的會議通常安排在下課時間,在一個沒有人使用的教室裡,老師、雙方和高年級的學生團隊共同協商。在奇娃會議中,雙方都有機會描述自己的遭遇。一開始的重點是傾聽彼此的談話。然後,老師邀請雙方自我反省,想想下次若發生類似狀況,可以採取怎樣的做法。重點在於讓這些學生「自己」想出解決方案,以避免衝突再度發生。一旦雙方承諾會執行預防策略,老師就會如實地記錄下來,會議便結束。
重點在於如何解決,而非言不由衷的歉意
寶拉.哈巫說:「在奇娃會議中,除非自己想要,否則不用道歉。因為若是由別人要求你道歉的話,任何人通常都是心口不一地說說而已。在奇娃會議中,必須專注於問題出在哪裡、誰做了什麼、你可以怎麼做。」
奇娃的成員通常會和雙方相約,於兩週後召開後續會議,重新檢視衝突。如果問題還存在,就會採取更進一步的步驟,並通知家長。
芬蘭學校絕不容許霸凌,奇娃計畫的主旨是,連續運用很多(比較)小的措施,根除龐大棘手的問題,例如:舉辦解決衝突會談,或在教室裡進行角色扮演,並請學生發表感想,藉此預防霸凌發生。寶拉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優良的計畫。」
過去我在美國學校教書時,若能確實執行奇娃計畫裡的某些關鍵元素,我和我的學生便可以從中獲益。我當時的課堂偶爾會出現霸凌行為,但我不知如何處理。如果能持續和學生討論霸凌議題、學習如何反抗,應該會很有幫助。
我也認為學校必須建立一個機制,專門應對學生的抱怨與困難。通常,我只處理我看得到的衝突。或許我早該在教室放一個信箱,像芬蘭學校的奇娃檔案夾一樣,讓學生告訴我彼此之間的互動是否遭遇困難。
最後,我認為在課堂中,每當衝突發生時,必須強調解決辦法,而不只是要求道歉。光是讓事情過去並非真的解決,多花時間和學生討論可以採取的正向措施比什麼都重要;如果能寫下進一步的解決方案,並安排後續會議,效果會更佳。
學校裡的霸凌行為將會摧毀學習的樂趣,霸凌發生之前的種種小動作也具有同樣的威力。所幸奇娃計畫提出了各式建議,協助學生站起來反抗霸凌,以維護課堂中愉快的學習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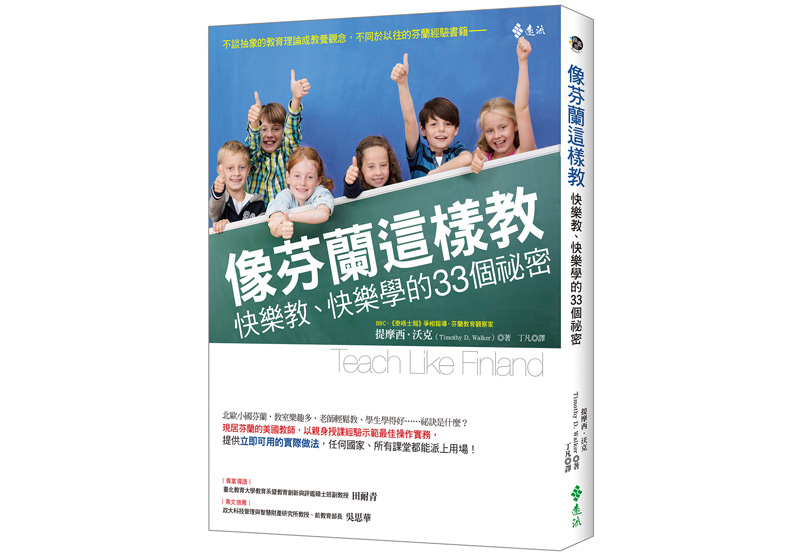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像芬蘭這樣教》一書,提摩西.沃克(Timothy D. Walker)著,丁凡譯,遠流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