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歐洲、亞洲和非洲等地旅遊的時間超過十年,從未想過要寫一本旅遊書。我向來有點討厭旅遊書:這些書似乎任性自溺、單調乏味,而且內容多半是作者的個人偏見。我一直認為旅遊作家經常掛一漏萬,錯誤連篇。我痛恨觀光式的旅遊,許多旅遊作家寫作的素材總不脫這些,像是金字塔啦、泰姬瑪哈陵啦、梵蒂岡啦、這兒的名畫、那兒的馬賽克圖案啦等等。在大眾旅遊的時代,每個人都去看同樣的東西,而旅遊寫作似乎也是這麼回事。我所指的是六○年代和七○年代初的情況。
那時候的旅遊書是個無聊的東西。它是由一個無聊的傢伙寫給一群無聊的人看的書。我很討厭旅人刻意淡化或是閉口不談旅途中曾有過的絕望、恐懼或淫欲,或是曾經對著計程車司機尖叫,或是嘲弄油嘴滑舌的企業大亨;以及他們在旅途中吃了些什麼食物,看哪些書來消磨時間,各個地方的廁所長得什麼樣等等。豐富的旅遊經驗告訴我,旅遊有大半時間是花在行程受阻以及惹人厭的事情上──像是公車拋錨、旅館員工態度惡劣、市場小販貪得無厭等等。旅遊的真實面其實是有趣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然而很少人將它如實地描繪出來。
我們有時會在某本書中發現旅遊的真趣──伊夫林.沃夫在《標籤》(L──els)一書中描述他被誤認為他哥哥艾列克的趣事;或是奈波爾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中不避諱談到他自己的善意和壞脾氣──《幽黯國度》是一部結構很棒的書,不但極具個人風格、富有想像力,而且提供豐富的訊息;或是在某些章節片段中體悟到旅遊的真趣,例如安東尼.特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西印度群島和南加勒比海》(The West Indies and the Spanish Main):
當時我在聖湯瑪斯(牙買加)一家鞋店裡買靴子,一名黑人快步走進來,以著高分貝的嗓音說,他要一雙鞋。他是剛下了工的工人。他頭上戴了一頂愛爾蘭人稱之為caubeen 的舊帽子,身上只穿了件襯衫,而且打赤腳。由於店內唯一的夥計正在幫我找鞋,當下沒空招呼他。
「我現在就要一雙鞋。」他用一種非常獨裁的聲音大吼著。
「稍坐一會兒,」店員說:「我馬上就來。」
他真的坐了下來, 但坐姿非常奇怪。他落座的同時,雙腳跟著從地面抬了起來;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的兩隻手緊扣在膝蓋底下,好讓雙腳掛在手臂上。他這個坐姿完全是在身子落座、雙腳離開地面的那一剎那同時完成。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他瘋了。
「給我一塊踏墊。」他大聲嚷嚷著;雙手依然撐住他的腳,不過顯得十分費力。
「好的,好的。」店員說,不過眼睛依然在找我的靴子。
「馬上幫我拿塊踏墊來。」他再度大聲嚷嚷。椅子的座位很窄,而且椅背很直,他這個坐姿說來並不容易;讀者若也嘗試這麼做,就會知道很費力。他因為動怒再加上姿勢很不舒服,幾乎哽住說不出話來。
售貨員給了他一塊墊子。大多數人都不會忘記,這種墊子在鞋店裡很常見。我想,這些墊子是用來讓那些雅緻的客人不會因此弄髒襪子。
這位想買鞋的紳士以前看到高貴人士都有這種奢侈的服務,因此抱定決心既然花了錢也應該得到同樣的享受。然而,他腳上既沒穿鞋也沒襪子,事實上並不需要那塊小墊子。
這裡發生了一起充滿人性化的插曲,特洛普湊巧看到這一幕,因此把它記錄下來;對我而言,這似乎才是旅遊寫作的重點。
寫旅遊書的心路旅程
旅程──旅行的路線──則是另一項重點。我讀過的許多旅遊書大抵出自某個旅人追逐一個城市或是一個小國家──像是《發現葡萄牙》之類的東西。這絲毫不像旅行,而更像是我所熟稔的一種長期居留,類似我過去在馬拉威、烏干達和新加坡的狀態。我去那些國家是打算留在那兒,我在那兒有工作、有駕照、每個週末固定會去採買東西。但我從未想過要寫一本關於那些生活細節的旅遊書。旅行必須與行動和事實有關:去嘗試每件事、去親身經歷,然後將它報導出來。
我覺得,挑選對的行程──包括選擇最佳路線以及正確的旅遊方式──是獲取經驗的不二法門。旅行需要你全然投入,那將是一次穿越內地從容不迫的長途旅行,而不是從一座大城飛到另一座大城,後者對我來說似乎一點也不像是旅行。我喜歡的旅遊書都是一些奇特的旅行經驗──我不只喜歡特洛普和奈波爾的作品,還喜歡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空調夢魘》(The Air-conditioned Nightmare;這是一本駕車橫跨美國大陸的遊記),或是馬克.吐溫的《赤道環遊記》(Following the Equator;那是一場全球巡迴演講之旅)。我希望我的遊記是一系列的長途火車之旅,然而何處才是我的征途?
這是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內心思索的事,當時我在維吉尼亞大學任教一學期。我一方面在寫《黑屋》這部小說,一方面等待《聖傑克》出版。在那個時期,每當我完成一本書,立刻又展開另一本書的寫作。我的妻子和我們的兩個孩子當時住在倫敦,她也在工作──說真的,她的收入不錯;不過我依然覺得我才是真正該負擔生計的人,但我賺得並不多。我的《聖傑克》預付版稅很少,我想,《黑屋》的預付版稅想必也不會多到哪裡去。錢財,確切地說,是個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然而它卻是我決定寫第一本旅遊書的關鍵因素──理由很簡單,我需要錢。當我向我的美國編輯提到寫這類書的可能性時,她樂觀其成。她說:「我們會先給你一筆預付版稅。」在此之前,我從未收過預付版稅。通常,我都是先完成一本書,交稿後才得到款項;我從未還未動筆就先拿到錢。
通常只有在被問到非常具體的問題時,你才會開始清楚思考自己的意圖。我當時大概的想法是寫一本關於火車的旅遊書,然而我不清楚究竟要到哪些地方去──只知道那將是一趟漫長的旅行。同時,我想像的是寫一本和漫長旅行同樣冗長的書,裡頭描述許許多多的人和許許多多的對話,但沒有一般景點的觀光。不過編輯的詢問點醒了我,因而想到,何不嘗試穿越亞洲的火車之旅。我可以搭乘「東方快車」從倫敦出發。當我查看這條路線時發現,我可以繼續穿越土耳其,進入伊朗,再進到巴魯奇斯坦地區(註一);而且搭一小段巴士之後,我還可以在伊朗東南部邊境城鎮扎黑丹(Zahedan)再搭火車進入巴基斯坦,多多少少穿越亞洲。我的想法是到越南去,搭火車到河內,然後繼續穿越中國、外蒙古和蘇聯。結果這個旅行路線有一大半最後證實不切實際或是不可行。一九七二年,當我向中國大使館表示,我想申請簽證以便搭火車穿越中國時,他們逕自把電話掛斷,理都不理(我後來等了十四年才得以實現這趟我記錄在《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一書的旅行)。當時,巴魯奇斯坦地區正爆發戰事──我於是更改路線,從阿富汗穿過。我決定把日本和整條西伯利亞鐵路線納入行程。我不在乎到哪裡去,只要是在亞洲地區,有鐵路系統,並且可以拿到簽證就足夠了。我想像著自己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不斷地換搭火車。
在這同時,我正在完成小說《黑屋》。這是一部以英格蘭鄉村為背景的小說,內容不僅嚴肅且充滿了鬼魅之氣。我希望我下一部是個充滿陽光的作品。當我把《黑屋》完稿交給英國出版商時,才剛敲定旅行路線。他建議我們一起吃個午飯。幾乎就在飯局展開前,他告訴我,他不喜歡《黑屋》這部小說。他的說法是,「這會壞了你的名聲」。
這是為何我在英國找了另一個出版商的原因,這件事也讓我更相信必須出版這本旅遊書:我非常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靠寫小說來謀生。我所想到的是與這趟火車之旅周邊有關的事,而非旅行本身。我不喜歡把家人留在倫敦;我過去從未做過如此慎重的一次旅行;我感覺受到這筆預付版稅的拖累──金額其實並不多。我的作家朋友們大都嘲笑我想寫旅遊書的想法。我從未開始擔心旅行本身的事,儘管我的身體和精神正遭受一種莫名的痛楚所困擾──我一直焦慮自己快要死了。我總感覺我將以「和死神約會」來結束這趟旅行,而且我必須行萬里路、經歷極大的痛楚之後才會終結生命。如果我選擇坐在家裡,吃吃喝喝,那麼我就不會死掉。我想像著,那會是一起愚蠢的意外,就像修士和神祕靈修學家多瑪斯‧牟敦在肯塔基修道院隱居了二十七年之後,同意外出傳教,不料一個禮拜後竟然在曼谷因誤觸電風扇磨損的電線而意外身亡。
我是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從倫敦出發。那是個陰霾天。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妻子跟我揮手道別。幾乎就在當下,我覺得自己犯了一個荒謬的錯誤。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變得非常鬱悶。為了讓自己心情愉快一些,並給自己這趟旅行其實是份工作的幻覺,我開始大量記筆記。從我離開那一刻到我四個月後回到英國──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想家──我寫滿了一本又一本的記事本。我把所有的一切記錄下來──包括各種交談、有關人和地方的描述、火車細節、有趣的點點滴滴,甚至包括我正在讀的小說的評語。我至今仍保存其中幾本書,在這些像喬伊斯的《流亡》(Exiles)、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故事集、遠藤周作的《沉默》等平裝書和其他平裝書背後的空白頁,我都塗寫了蠅頭小字,等轉寫到大本筆記本時再做更詳細的描述。我都是用過去式的時態來寫。
在我交給出版商的手稿中,有一篇關於阿富汗的文章,編輯建議我剔除(「那章沒搭火車,」我的編輯說),不過我後來將這篇編入合集《日出與海怪》中出版。我寫這本書的難題在於找到一個合適的形式──一個架構;我決意把它寫成一系列的火車之旅,只要專注在旅行所發生的事即可。我從未讀過像我正在寫的這樣一本書。這讓我憂心之餘也充滿了希望。寫這本書與旅行本身所花費的時間相當,同樣是四個月。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這本書至今仍繼續出版,而且賣得相當不錯。有些人以為這是我唯一寫過的書,這令我大為惱火,因為我認為《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的文筆更為流暢,而《騎乘鐵公雞》所提供的資訊更豐富。好比說在《火車之旅的饗宴》中,我所搭乘的火車穿過了南斯拉夫的尼什(Nis)。我提到這個地方,但並未費神去找關於尼什的任何資料。我剛查閱了一下藍色旅遊指南,發現尼什是康士坦丁大帝的出生地。接著我再細讀其中的介紹,它提到「尼什本身雖非宜人之地,卻有幾個有趣的歷史遺址」,這讓我想起我在尼什逗留的原因。尼什最近的發展是,科索沃內戰期間,它被北約炸彈夷為平地,成了萬人塚。
令人滿意的是,這本書進展得相當順利(書名靈感來自印度一條街名Bazarr)。我寫這本書時並不了解,每趟旅行都是獨一無二的。我的旅遊書談的是我自己的,而不是你的或任何其他人的旅行。縱使有人跟我同行,而且也寫了本關於這趟旅行的書,它也一定是一本內容完全不同的書。當時我不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每趟旅行都有其歷史性的一面。就在我完成這趟旅行後不久,這些國家都經歷了政治變革。伊朗國王流亡海外,伊朗成了外國遊客的危險之地;阿富汗發生內戰──蘇聯提供援助;印度和巴基斯坦恢復鐵路聯繫。寮國實施鎖國政策,禁止外國人進入,並且推翻了君主政體。越南修復鐵路,如今已能從胡志明市(西貢)搭火車到河內。我搭過的許多火車已經停止行駛,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東方快車」。今天往返於倫敦與威尼斯之間、同樣標著「東方快車」之名的火車是給那些對旅行存有自私、奢華幻想、貪圖舒適享受的有錢人坐的,跟真正的「東方快車」完全無關。不管我所搭乘的那列老「東方快車」有多糟,至少我可以說,不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許多人都搭過這列火車往返於歐亞之間。它既便宜又親切,而且就像所有很棒的火車一樣,它是一個在輪子上運行的世界。
我寫這本書時有如在黑暗中摸索──儘管我小心翼翼地來掩飾這點;我對自己敘事能力的自信實乃虛張聲勢,它就像藉吹口哨來提高自己的士氣一樣。我知道自己採用了一種可敬的形式,也就是旅遊書的形式;不過我是用自己的方式──亦即適合自己以及我那獨特旅行的方式來書寫。它一點也不像小說:小說需要靈感、高度的想像力,以及長時間的閉關自守。我發現,旅遊書的寫作是一種蓄意的行為──就像旅行本身一樣,它需要健康、體力、自信以及樂觀和深度的好奇心。當我完成一部小說時,從不知是否還能再寫另一本;然而當我完成這第一本旅遊書時,我知道自己可以再繼續寫下去。
註一:巴魯奇斯坦地區(Baluchistan)—涵蓋巴基斯坦西南、阿富汗西南和伊朗東南的廣大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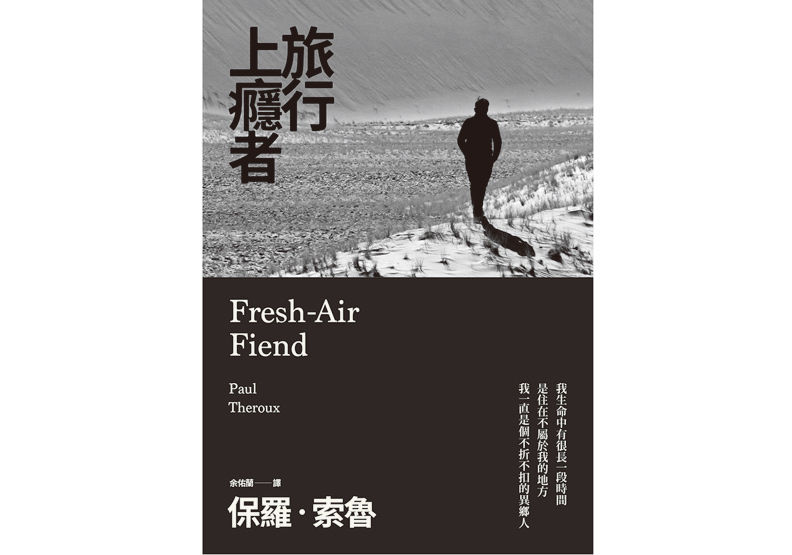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旅行上癮者》一書,保羅.索魯(Paul Theroux)著,余佑蘭譯,馬可孛羅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