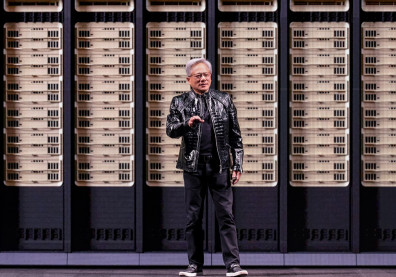當白居易聽完琵琶女的故事後,立刻感慨地說「同是天涯淪落人」,接著整個第四段就回到白居易自己身上,談的都是自己的「天涯淪落」。請注意,一個人怎麼講他自己的得與失都是在暴露他的人格,當他抱怨他所沒有的,那就是他很想要的,反向可推,那些抱怨就暴露出他的真實欲望。我們現在就用這個道理來推敲一下,白居易到底想要的是什麼?這整個第四段全部都在抱怨,請看他抱怨的是什麼呢?
首先,一開始就是「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離開了長安這一個代表世俗的成功場域,就是「去中心化」。
當時,長安在文人心目中是唯一的天下中心,只有身在長安,才代表是人文薈萃裡的一員,也分享著這個大家所積極追求魚躍龍門的功名富貴;離開長安也就等於離開了世俗的成功場域。所以唐代文人是這樣的:一般的文人寧可在長安做一個小官,稱為京官,也不願意到地方去做首長,雖然那可能品級更高、權力更大、收入更多,可是他們寧可留在長安做個小官,那代表一種榮耀甚至成功;而且在長安這個天子腳下的地方,這邊出門可能遇到一個貴人,那邊出去可能遇到一個大官,近水樓台,容易建立人脈、獲得權位,反映的就是趨炎附勢的人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的性格,第一個就是對於「去中心化」念念不忘。
值得思考的是,到底「天涯淪落」是根據什麼去定義的呢?簡單的意義就是流離失所,到了邊陲之地。問題是,天涯就一定是淪落嗎?關鍵應該是你怎麼看待「去中心化」以後的處境。
這裡可以參考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們望塵莫及但心嚮往之的人物,就是蘇東坡。蘇東坡一路被流放貶謫,最後到了如今的海南島,「天涯海角」這個詞就是他寫在那裡的四個字,這真的是天之涯、海之角的地方;在這個地方過了一段時間後,終於遇到朝廷大赦,蘇東坡可以返回中原,這時又要渡過瓊州海峽,然後才踏上中國的土地,當他在海邊看著眼前無垠的天光與海波,心中有感而發,寫下了「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詩句。
這時的蘇東坡已經又老又病,即使後來平安渡過海峽,但一路往北走還沒有到達家鄉,在路上他就病死了,所以渡海之前也算是人生到了終點;然而即使這樣的窮途末路,歷盡了滄桑,承受了各種失敗打擊否定,他在輾轉流落到這樣一個天涯海角,面對著隔離了他的人生的一道障壁時,所顯示的竟然是如此純淨無瑕的人生觀、世界觀——「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第一句是說,雲影消散了,月亮的皎潔絲毫不染雜質,上面沒有黑子、沒有陰影,下面一句是說,你看整片的天空、整片的海洋本來就是沒有雜質的、乾乾淨淨的。可見蘇東坡看到的是存在本身的美好,這個美好的本質根本不受汙染。那麼汙染來自哪裡呢?汙染其實是來自你內心的翻攪,你的心在憂鬱在煩惱在渴望,被各種欲望和情緒所主宰,被許許多多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攪得心裡面簡直是一灘渾水;但是蘇東坡說,事實上存在的本質、世間真正的本質是乾乾淨淨的,沒有任何的蒙蔽、任何的扭曲。
這就是蘇東坡,即使到了人生最後的這個時刻。這跟大家很熟悉的<定風波>不是很像嗎?他不是說「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這也表現出他人格一貫的境界,真的是令人敬佩。
當然,蘇東坡的境界很崇高,我們無法、也不應該用他的境界來苛責一般人,但是白居易不是一般人吧!他歷來受到了那麼大的讚揚,說他又豁達、又灑脫,而且他字樂天,常常以「樂天」表達出他已經超越世俗的得失,可以樂觀開朗,這也是他想要營造出來的清高脫俗的形象。
但是,白居易只是被貶到江州而已,就在長江的江南沿岸,這裡他卻已經覺得簡直是荒郊野外,感嘆天涯淪落,可是瓊州海峽在哪裡?海南島在哪裡?那才是名符其實的天涯海角。通常人的心理反應是:距離越遠,你的心就越失落,也越覺得失敗、越自我否定,這是人很正常的一種心理,但蘇東坡卻隨遇而安,所以我們才覺得蘇東坡很偉大;相對地,當我們實實在在地讀白居易的詩,就會發現:他真的是不把得失放在心上,真的是超越世俗榮辱嗎?未必盡然。從這一段所描述的處境,就清楚呈現了這一點。
請看再來他抱怨什麼,也就是他想要什麼?是音樂,即「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可是請注意,重點不只是音樂,關鍵是哪一種音樂?「絲竹聲」代表了精緻的、高雅的音樂,他說明明有音樂啊,但是「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他鄙視原住民的鄉村音樂,可見他要的是那種訓練有素、來自長安的高級音樂,因此下面才會說「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那才是讓他的耳朵清明起來的仙樂,簡單地說,就是「京都聲」。
這也是為什麼白居易一開始會注意到琵琶女的原因。琵琶女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嗎?何況在那之前,深夜的天色一片黑暗,根本沒看到人啊,所以白居易絕對不是因為琵琶女的美貌而注意到她的,更不用說這時的琵琶女早已年長色衰,談不上美貌。事實上首先吸引他的是什麼?詩歌前面的小序說得很清楚:「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被稱為「仙樂」的就是這個「京都聲」。
足見白居易存有很嚴重的差別心和等級觀,不屑於地方上的鄉村音樂,他要的是這種高級音樂,代表全世界最先進、最精緻的演奏技巧,乃至於那種時髦的「京都風格」,於是形成「琵琶—仙樂—京都聲」與「山歌村笛—俗樂—荒鄙之音」的鮮明對比。
公平地說,我們必須承認,「京都聲」確實比庶民音樂要更精緻複雜、更有人文內涵,這是無可諱言的,畢竟那是經過幾百年長時間的文化累積;但是對白居易來說,更重要的差別還是在於:這個「京都聲」代表了長安,也就是天下中心的權威象徵,所以才更吸引他的耳朵,同樣顯示了他對於長安的念念不忘,以致凡是打上「長安」烙印的,都會特別吸引他的注意。
接著,我們再繼續看白居易還抱怨什麼?「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他抱怨江南的低窪潮濕,到處是雜亂無章的植物,讓人水土不服。無形中還是厭惡這是一個村野,村野鄉居沒有那麼的舒適,又低濕又荒涼,配合「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這些都是在渲染村野鄉居的落後偏僻,帶有一種未開化的粗野不文。可見對他來說,想住的應該是整潔有序的長安豪宅,擁有各種都市化的享樂,所以居住條件也是白居易很在意的一點。
再來呢,所謂「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白居易又在感慨他沒有什麼,因此嚮往渴望呢?就是朋友啊,「往往取酒還獨傾」就是感慨沒有朋友的孤獨,以致遇到「春江花朝秋月夜」,也只能一個人喝酒,真是白白辜負這樣難得的良辰美景。換句話說,他渴望的就是朋友。可是他想要的朋友又是哪一種呢?這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我們來想一想。
王維有一首詩<終南別業>,後面六句講到:「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王維很能享受孤獨,興致一來,就一個人到山林裡面遊賞大自然的風光景色,即使「勝事空自知」,跟花鳥邂逅、聽水聲泠泠這些美好的勝事只有自己知道,還是非常自在。走到溪水的盡頭也不會掃興,反而坐下來抬頭看天,領略到廣闊的蒼穹上白雲無盡的生機,比起低著頭走路,反倒獲得更開闊的視野、更無限的自由,甚至帶有「上帝關起了一扇門,就會打開另一扇窗」的哲理,陸遊那著名的「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從這裡化出來的。然後這首詩最後說「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偶然之間遇到一個鄰家的老人,就跟他說說笑笑,根本忘了回家的時間。
請看,「偶然」表示是沒有預先安排好的,就意外地遇到一個鄰家的老人,「叟」通常不是指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而比較是一般普通的老先生,結果王維這麼一個詩歌、書法、繪畫、音樂全方位的藝術天才,竟然可以跟鄰叟聊得這麼投契,這真的很不容易。難處就在於雅俗的落差以及知識水準相距懸殊,不用太久就會發現不曉得該談什麼比較好,雙方的交談往往很難撐下去,但王維能夠跟一個鄰叟「談笑無還期」,那心胸是多麼的寬廣自在,跟任何人他都可以如此順暢地交流,顯示他一點都不高傲,完全沒有架子,更沒有因為自己的知識帶給自己限制。就這一點來說,王維跟蘇東坡有異曲同工之妙。
蘇東坡說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意思是說,從天上的玉皇大帝到慈善機構所收容的乞丐,他都可以從容自在地相處,毫無嫌隙隔閡,那該是有多大的學問智慧,尤其是要有多麼開闊的胸襟!這樣的人格真是何等自在,連李白都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他們的寂寞都不是白居易這一種。
仔細推敲,從白居易對謫居之地只有生活枯燥無聊、環境低濕難耐、鄉音鄙俚刺耳、居處孤獨無友的負面描寫來看,白居易想要的朋友應該比較接近劉禹錫所說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陋室銘>)。
果不其然,基於人格的一致性,白居易在別的作品裡也清楚呈現這一點。源自江州司馬時期的「醉吟」一詞,後來變成了白居易自己的別號,還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的自序文,等於是他自己的自傳。有趣的是,其中所顯示的價值追求,正和<琵琶行>一樣,差別只在於<琵琶行>是用「抱怨沒有」的方式呈現,<醉吟先生傳>則是以「滿足已有」的筆調書寫。
透過學者對<醉吟先生傳>的研究指出:白居易其人其詩之特質,是他往往在生計、年齡、官位等生存基本條件都確認自己安然無恐、優裕有餘之後,乃由之獲得心靈的滿足,因此,閒適的心境就建立在物質的、外部的條件得到滿足的前提之上;同時,他所描繪的快樂全是源自都市的恩惠,都市的燈紅酒綠為他提供了個人盡情縱樂的機會,而導致閒適的社會化、世俗化;至於朋輩交遊作為他人生快樂的最主要來源,又多是精心篩選過的僧侶、士大夫等特定人物與特定分野,迥非來者不拒的平民風格。
而這一段闡釋,恰恰可以說明<琵琶行>中白居易的性格特質,竟然也同時吻合了琵琶女的性格特質。這個驚人的相似性頗為耐人尋味!也許可以說明「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一句詩的真正意義。
(圖說:「唐人宮樂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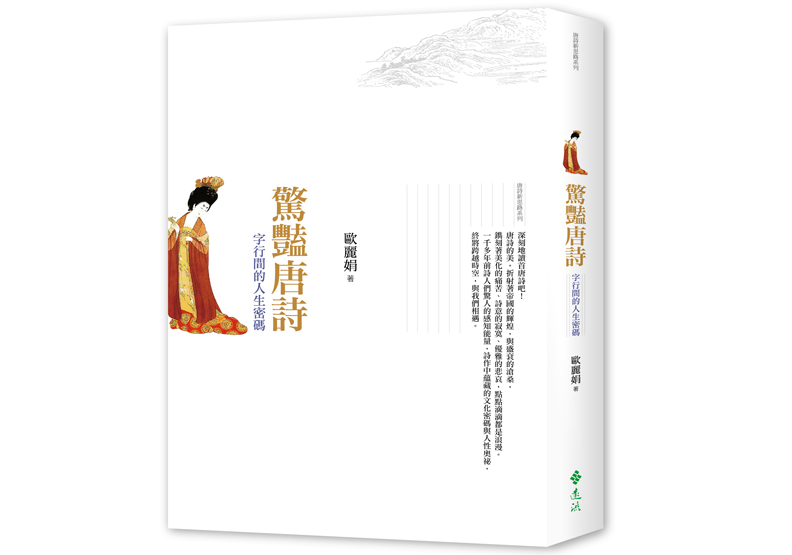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驚豔唐詩》一書,歐麗娟著,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