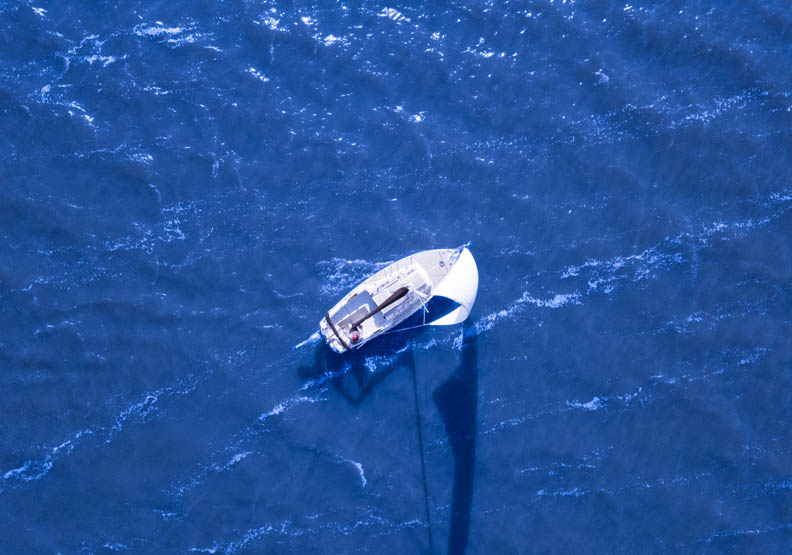隨著年紀增長,你的眼界也會愈來愈寬廣,就像能夠透過望遠鏡來看世界一樣。你的目光會聚焦,看見自己從未注意過、或從來不想看的東西。我現在就能看出自己的諸多缺陷,真希望有些事情當初能以別的方法處理。
現在,回首過往,我才終於明白薛尼有多麼愛我,超級愛我。他對我的付出勝過世上任何人。他用愛澆灌我、支持我的事業,可是我卻從不滿足。
到了我們關係的尾聲,他和我說:「妳並沒有對我付出全部的自己。」
悲哀的是,確實如此。發現李奧波德和我原本以為的那個人不同之後,我就在未來的關係裡做了調整──我再也無法對任何人全然付出。
二○一四年,薛尼過世前不久,我和他曾匆匆一會,因此而有機會能夠告訴他,他對我的意義多麼重大,而我有多麼愛他。我們兩人的仳離曾經讓我痛苦多年,那次會面將我從折騰人的罪惡感釋放出來。
我和薛尼分開的時候,攝影師理查德.阿維頓對我說:「妳在尋找的那種幸福,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
當時,這番話令我猛吃一驚,讓我想起自己曾經帶給多少人痛苦的回憶;我在森林裡漫不經心地遊蕩時,一路粉碎著別人的心。如今,這番話現在不會再驚嚇到我了,裡面蘊含的真相,是我隨著歲月流逝才逐漸理解的。
阿維頓說得對,我在尋找的那種幸福並不存在。那就是桑塔格寫的:「對於你從未擁有過的東西,那種渴望會一直懸浮在你頭頂上,一輩子都逃不開。」
如果,妳當時能理解這一點,事情會有任何不同嗎? 大部份的情況是,我可以透過理性和智性去理解某件事,但這都無法改變我在情緒上的感受──無論我是多麼希望可以做到這點。如果妳之前就看清事實,能夠減緩妳的騷動不安嗎? 能夠讓妳比較容易滿足嗎?
我很希望這麼想,可是我也無法確定。如果你能看清自己的行為模式,你就能瞭解自己行動或情緒背後的動機,這對你肯定會有無比助益。這當然不表示,我就不會蠢動不安或不滿,可是,至少我可能不會像當初那樣衝動行事。
我心中一直有股熱情,就是作家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所謂的「生之狂熱」。可是部分的我也渴望穩定,而穩定和那種狂熱,互不相容。
在我演戲生涯的起點, 我曾經試演過劇作家田納西. 威廉斯(Tenessee Williams)的劇本《奧菲斯的沉淪》(Orpheus Descending)裡,卡蘿.克崔爾(Carol Cutrere)這個角色。她有句台詞是這樣的:「我想被看到、被聽見、被感受!」
那也是我想要的。
當你覺得自己有那麼多可以付出,內在有如此多的激情,那麼,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出去找到它,並且實現它。如果你有那種生之狂熱,便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擋你去滿足那股狂熱,而每次你只要又陷入愛河或是完成某個創意目標,你告訴自己,「這就是了!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可是不久後你就會開始想,「這樣不夠,我還要更多。我想要完美!」
你父親和我說過,「隨著時間過去,我們都會逐漸變老,而我只會比現在更愛妳。」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對他來說,已經足夠;隨著時光流轉,一切只會愈來愈好──這個概念對我來說,實在新穎有趣極了。只有非常平衡的心靈,才會有這樣的想法。聽他這麼說,我興奮且感動,可是這種想法對我來說確實很陌生。我從未以那樣的角度思考過未來。
要是我當時便能明白現在這些道理,我會坐下來,好好思考,把那種狂熱的本質看清楚。我天生對生命懷有本能的欲望,隨時準備享受浪漫,我一向以開放的心胸迎向生命,現在依然如此。這就是一切的鎖鑰。因為這樣,無論我經歷過多麼艱難的風波,它們都無法讓我變得剛硬或凶悍。
如果你心中也有那股生之狂熱,不要因為你渴望更多,就做出什麼傻事,或是搞砸你已經擁有的一切。因為人的慾望是永無止盡,你永遠無法滿足的。一旦你察覺了這點,意識到那種狂熱,也許你就會看出自己何時走偏了路、或是讓無法滿足之心掌控了你的想法,驅使你踏上最後可能會後悔的路線。
每當我不開心或是不滿意的時候,就會想起古羅馬作家維吉爾(Virgil)寫的,「也許終有一天,即使憶及此事,也會心生愉悅。」這句話引人深思,不是嗎?
無論何時,如果你感到蠢動不安或是愁雲慘霧,只要把自己的眼光放遠到未來某一刻,也許你將會戀戀地回顧此時此刻,當前一切也將變得更堪忍受。即使看起來可能很糟糕的問題,在未來也許就是正向的轉機。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儘管有不少負面影響,這種蠢動不安的精神──有時也像是種祝福。因為對生命的本能欲望,能讓人永保年輕與活力,而這正是點燃想像力和創造力的靈感之鑰。
「永不滿足!」演員華特.馬舒(Walter Matthau)曾經對他的妻子卡洛這樣形容我。他這句話並非是在讚美我,但我偏要這麼想。人生裡有如此多值得感謝的事情,即便是這樣蠢動不安的精神,我也滿懷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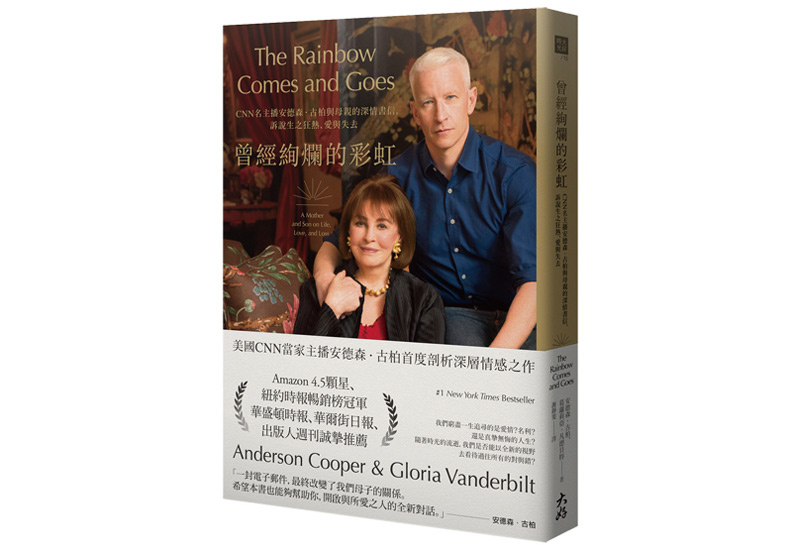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曾經絢爛的彩虹》一書,安德森.古柏(Anderson Cooper)、葛蘿莉亞.凡德貝特(Gloria Vanderbilt)著,謝靜雯譯,大好書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