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哲學
松尾芭蕉 Matsuo Bashoō
一六四四年∼一六九四年
在西方,我們隱約覺得詩對「靈魂」有益,使人敏銳與智慧,但我們不見得知道該怎麼做。詩是詩,生活是生活,很難實際有所交集。在東方不然,有些詩人知道詩作能發揮何種效果:詩能引導我們走向禪宗的智慧與平靜。十七世紀的僧侶俳諧師松尾芭蕉即為一例。
一六四四年,松尾芭蕉生於伊賀縣的上野城。他兒時在領主藤堂良忠家當侍童,藤堂良忠教他「俳句」這個詩歌格式。傳統上,俳句分為三行,兩句描寫意象,由結尾句銜接。日本文學最有名的俳句是《古池》,即出自松尾芭蕉之手:
古池
青蛙躍入
水聲響
這首俳句平淡簡單,但靜心品味方覺優美之至。
一六六六年,藤堂良忠過世。松尾芭蕉離開家鄉,在外飄泊多年,最後落腳江戶,在此聲名鵲起,作品流傳甚廣。然而松尾芭蕉變得鬱鬱寡歡,離群避世,搬至郊外小屋,時而浪跡各地,最終在一六九四年離開人世。
松尾芭蕉是出色的詩人,但不認同「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觀點,反而想幫助讀者進入禪意的獨特心境。他的俳句反映禪宗最重要的兩個概念:「侘」與「寂」。對松尾芭蕉來說,「侘」是指安於簡樸,「寂」是指安於清寂(跟千利休藉茶道追尋的心境相同)。最能陶冶「侘」與「寂」的當屬大自然,無怪乎是松尾芭蕉極常寫到的主題。比方說,這首俳句描繪春景,於世無求,只是欣賞日常之美:
早櫻
正含苞
桃花伴放
松尾芭蕉所寫的主題出奇簡單,沒有政局分析,沒有三角戀情,沒有家庭糾葛。他意在提醒讀者,真正重要的是能安於周遭事物,體察此時此刻,感受生活中最簡單的種種:四季的推移遞嬗、對街鄰居的哈哈笑聲,還有旅行時的小小驚喜。現在看一看這首傑作:
菫花—
何其嬌美
於山徑
松尾芭蕉也向讀者提醒,百花、天氣與自然景物盡皆變動不居,瞬息即逝,一如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有必要留意時間的流逝,留意天氣與景物的變化,從中預先窺見自己的死亡:
棣棠花
潺潺—
水瀑流
這種生命無常的感受有時教人心碎,卻也使每個片刻彌足珍貴。
松尾芭蕉不僅喜歡寫作,也喜歡繪畫。許多畫作傳世至今,上面寫有相配的俳句。
在文學上,松尾芭蕉推崇「平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如同出自兒童之手,厭惡虛假造作,反對華美詞藻。他對弟子說:「在我看來,一首好詩的韻律與轉合宜平易,好似溪水流淌過細砂。」
「平易」的最終目標是使讀者擺脫心頭負擔(即生活的瑣碎煩惱),與萬化合而為一。松尾芭蕉認為好詩能使我們跟自然短暫融為一體,透過文字化為岩石、流水或星斗,進入「忘我」之境。
松尾芭蕉使我們彷彿棲身於他所描寫的對象上,感受「忘我」的概念,儘管那只是隻不怎麼詩意的死魚:
魚鋪
成家鯽
露出寒齒
現代社會充斥社群媒體的個人頁面,滿是精美的履歷,我們費心準備好要脫穎而出,聽到逃脫自我可能有點奇怪,但松尾芭蕉點出「忘我」的價值,理由是這有助擺脫種種糾纏世人的欲望與缺憾。
松尾芭蕉長年心頭鬱結,浪跡於危險的窮鄉僻壤,身上只帶文具與少數物品,度過一個又一個難熬的漫漫長夜:
蚤虱咬嚙
馬尿聲傳耳畔
徹夜無眠
然而「忘我」使他從憂煩鬱悶中超脫—也能使我們超脫。他的俳句反覆叫我們珍惜所有,明白眼前的難題跟浩瀚宇宙相較根本不足為道。
松尾芭蕉的俳句簡單淺顯,卻猶如醍醐灌頂。這些詩句的價值不在文字優美(雖然確實優美),而在激發最珍貴的心境,提醒詩人與讀者,滿足源自從簡樸中獲致快樂,源自從自我的禁錮中逃離(即便只是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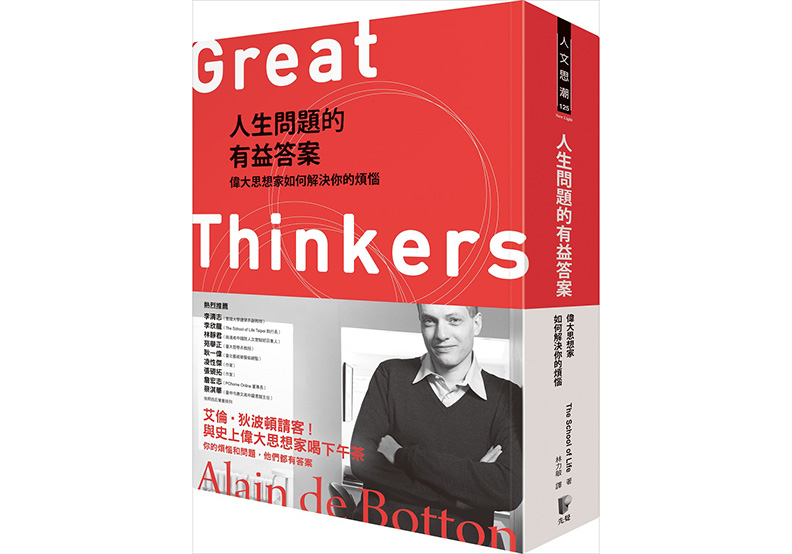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一書,The School of Life著,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主編,林力敏譯,先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