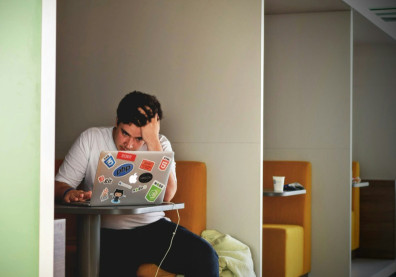站在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的頂樓,全球最重要的貿易航線盡收眼底。那是二○一四年的春天,在清晨的薄霧中,數十艘貨船和油輪依稀可見,正等著穿越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狹窄水道。每年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交易貨品會通過麻六甲海峽和新加坡,這是連結東亞和歐洲及中東的海上樞紐。
這一間飯店的地下室也可讓人一瞥全球化如何在此運作。那是一間超大型的賭場,而最有利可圖的顧客,是一擲千金的中國人。這些中國觀光客在賭桌上輸的錢,讓賭場老闆薛爾頓.艾德森(Sheldon Adelson)獲利豐厚。艾德森是在拉斯維加斯起家的超級富豪,有明確的右派政治觀,會用他的財富贊助鷹派的共和黨員參選美國總統,並支持以色列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右翼報紙。在此,東南亞一個旋轉的輪盤將中國、美國和中東連結在一起。
新加坡現為全球的十字路口,但它擢升到這個地位是最近的事,主要得利於它的位置橫跨歐亞之間最重要的貿易路線。而那條貿易路線,即麻六甲海峽的歷史,也體現了東西方之間的權力轉移。十五世紀時,位於今馬來西亞南濱的麻六甲鎮,是一個強盛伊斯蘭王國的所在地,但該國的蘇丹在一五一一年葡萄牙侵略行動中被廢黜。當時抵達麻六甲的葡萄牙船隻,是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先鋒,往後數個世紀,他們殖民了大半的世界,葡萄牙本身也崛起為全球最大的帝國之一,幅員從巴西、非洲南部、印度次大陸直到東亞。葡萄牙的殖民延續了數個世紀,而它最後兩個亞洲據點,是直到不久前才讓出的。澳門在一九九九年歸還中國,東帝汶則在一九七五年脫離殖民。
然而,在我眺望麻六甲海峽時,已經很難相信葡萄牙曾是全球一大強權了。最近一次訪問里斯本時,我順路造訪達伽馬的雕像,也就是一四九八年發現從歐洲到印度的航線、為葡萄牙帝國奠定基礎的探險家。里斯本國際機場寫著中文、向中國投資客推銷房地產的廣告牌,這更能表現現代葡萄牙的情況。身陷債務危機,而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紓困的葡萄牙,正試著透過向願意花五十萬美元買房地產的外國人兜售居留簽證,來振興本國經濟。
到二○一四年時,里斯本曾是世上首要權力中心的歲月已完全過去了,反觀新加坡已崛起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天際線布滿鑲有巨型國際金融企業之名的摩天大樓:花旗、匯豐、瑞銀、澳盛。它的港口和機場都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繁忙。
新加坡和葡萄牙的命運翻轉,正是財富和權力從西向東移轉的象徵。新加坡最早是在十九世紀初被英國人建為貿易站,但誠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時指出的:「新加坡已經存在了一百八十年,但在一九六三年之前的一百四十六年,它只是英屬印度的前哨基地。」一九六○年代,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甚至沒有自己的供水系統,想要獨立的希望看來也暗淡無光。但在李光耀堅定的領導下,新加坡善用它擁有的每一項優勢,特別是戰略位置。後來它和台灣、香港和南韓合稱「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以驚人速度成長的同時,也(套用李光耀的話)「從第三世界跨入第一世界」。
穿越麻六甲海峽的商品成了新加坡繁榮的基石,也是全球貿易蓬勃發展的和平年代的一大象徵。但,在不同的形勢下,麻六甲海峽也可能變成國際的引爆點。海峽最窄之處,夾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間,僅有兩哩半寬,而中國從外界進口的石油大多必須經過這個細細的孔道。每年通過麻六甲海峽運往東亞的石油量,是通過蘇伊士運河的三倍。
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深知麻六甲海峽對戰略的重要性,正如巴拿馬運河連結美洲東岸和太平洋,麻六甲海峽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也是中國取得中東和非洲能源供應的門戶。美國一位軍事計劃人員直言:「如果發生戰爭,那就是我們取勝之處。」換句話說,中國的一大弱點在於它仰賴海運進口,以石油為最,但也包含其他重要物資,如穀物和鐵砂。如果真的爆發衝突,美國海軍可以試圖在麻六甲海峽和另三個較少使用、連結南海和印度洋的海峽(巽他、龍目和望加錫)口掐住中國的經濟。
但中國對這個弱點一清二楚,過去十年,「麻六甲難題」一直是中國戰略討論的焦點,也已促使中國大幅提高鋪設橫越大陸的油管和天然氣管,從俄羅斯、哈薩克、巴基斯坦和遙遠的中國新疆省運送能源的經費。中國海軍也從該國提高的軍隊預算中獲得特別高的挹注,因為中國希望降低海軍遭美國封鎖的可能性。
麻六甲海峽在美中戰略思考中扮演的角色,反映了東南亞在亞太霸權爭奪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東南亞已經歷一段黃金年代。國外貿易和投資激增,使迥異如新加坡城邦和廣大的印尼群島等國家,都享有多年經濟迅速成長的光景。就連曾因實行共產主義或軍事獨裁而與世隔絕的國家,如越南和緬甸,現在也成了不容忽視的貿易國,更是外國投資客和觀光客的重要目的地。
但在人們的記憶中,東南亞也是群雄逐鹿的戰場。日本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占領新加坡,「粉碎了白人所向無敵的神話」,更是對英國國際形象一記毀滅性的重拳,開啟大英帝國在二戰後垮台的序幕。日本和同盟國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最血腥的戰鬥,是在菲律賓、緬甸和馬來亞進行的,而東南亞的衝突並未隨戰爭落幕而結束。隨著殖民時代步入尾聲,英國在馬來亞對抗一場暴動,法國則在印度支那討伐越南獨立同盟失敗。接著,脫離殖民的戰爭退場,改而上演冷戰的血腥衝突。越戰奪走五萬五千名美國人和超過百萬名越南人的性命。鄰近的柬埔寨也因越戰陷入動盪,經歷波布(Pol Pot)和「紅色高棉」(Khmer Rouge)近乎種族滅絕、造成一百多萬柬埔寨人民喪命的統治。一九六五年,印尼軍事政變後的大屠殺,以「疑似共產黨員」的罪名殺害數十萬人,這次政變也讓親西方的軍事強人蘇哈托(Suharto)因而掌權。居帝汶島東半部的東帝汶,也在一九七五年葡萄牙統治垮台、引來印尼入侵後,造成相近的死亡人數。
但從一九八○年代起,東南亞開始將它浴血的過往拋諸腦後。隨著冷戰逐漸結束,和平曙光乍現,這個地區的國家把握了全球貿易迅速增長、通訊和運輸改善,以及西方和日本跨國企業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契機。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等國家,開創了一道以出口、製造業和外國投資為基礎的迅速經濟成長公式,之後,這套公式也為中國所採用,且規模大得多。如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貝利(Christopher Bayly)和提姆.哈波(Tim Harper)指出的:「直到一九八○年代,日本經濟復興、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崛起,以及亞洲共產主義朝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轉型,亞洲才開始嶄露頭角,成為二十一世紀超強的大陸。」
一九九二到九五年間,我主要在曼谷擔任《經濟學人》駐東南亞通訊記者時,那個地區已成為全球化經濟的中心。大型日本跨國企業,如豐田(Toyota)和索尼(Sony)等,都把泰國和印尼當成製造基地,東南亞本身的公司則是中國最早的外國投資客。我的第一次上海之行,是報導泰國卜蜂集團(Charoen Pokphand)在當地所做的投資,該集團經營的生意甚廣,從加工雞肉到摩托車應有盡有。一九九三年,這筆投資讓中國人喜出望外,高興到讓一部全新的卜蜂摩托車雄踞上海機場行李轉盤的正中央。在那個時期,上海新興的中產階級仍較可能買得起新的摩托車,而非汽車。河流南岸的浦東一帶,卜蜂集團設廠之處,當時仍是倉庫林立的破敗地區。十五年後,上海的街道車水馬龍,浦東則宛如現代摩天大樓的叢林。
在一九八○年代及九○年代的短暫歲月,東南亞國家是亞洲發展的輻輳,甚至堪稱中國和印度的榜樣。但現在,經過二十年的迅速成長,中國和印度經濟體的龐大規模,意味著東南亞再次為巨人的陰影所籠罩。與此同時,東南亞和中國之間的商業往來遠比之前緊密而熱切。一九九○年代初期,曼谷和上海間一天只有兩個班機,如今有十四班。像泰國這種以往仰賴西方觀光客的國家,已愈來愈來倚重中國市場,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酷愛旅行。
中國經濟持續「和平崛起」,讓東南亞各國抱持希望:他們可續搭亞洲日益繁榮的順風車。但中國民族主義的擴張也令人憂慮,尤其是戰爭可能回到東南亞這點。這個地區最深思熟慮的政治人物,都非常清楚當地潛在的危機。
儘管繁華而耀眼,新加坡的處境卻和以色列有八分像。如該國第三位總理李顯龍(也是李光耀之子)二○一四年在倫敦一場午餐會上跟我說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小國家多半命不長久。」
為保長治久安,新加坡試著和區域的巨人培養感情,成效頗佳。事實上,它或許是世上唯一一個可自稱和中國及美國都有特殊關係的國家。「李PM」(新加坡人習慣這樣稱呼他)親自展現了他的國家兼顧東西方的能力。他自幼就會英語和中國普通話;後在劍橋大學念書,以數學一等榮譽畢業。只是有點遺憾地,李顯龍拒絕劍橋三一學院的入學許可,放棄學術生涯,回到新加坡從事建國工作。他在服役一段時間後,追隨父親腳步進入政壇。
李氏父子都決定,要讓國家卡好位置,以便取中國崛起之利。自一九七○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即力行讓該國七十五%的華人人口同時學習普通話和英語的政策。他們認為新加坡人該講中國統治菁英的語言,而非在新加坡自家裡較可能說的區域性方言,如福建話,這個堅持表現出斷定中國必將崛起的先見之明。新加坡人是中國的早期投資者,許多前景看好的北京公務員都來新加坡受訓。隨著中國愈來愈富裕,新加坡也成了中國資金的熱門標的,熱錢源源注入新加坡的房地產和銀行。而在中國人民幣終於國際化後,新加坡政府也致力讓本國成為人民幣交易的海外重鎮。如李顯龍對我指出的,中國絕對可以在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中施展魅力:「中國人非常認真……他們過來做推銷,有明確具體的提案,還有資源做後盾。所以他們會和你合作進行海洋研究,也會在教育方面幫上忙。他們會列出七、八個品項,確定無一遺漏,也希望彼此關係良好。」除了經濟,中國和新加坡也有政治連結。一如中國,新加坡也推廣儒家思想,強調階級與責任,以和西方的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分庭抗禮。
但就在新加坡人和中國交好的同時,他們也依賴美國。美國海軍的船艦會輪流進出新加坡,將新加坡用作維持南海秩序和看守麻六甲海峽的基地。美國海軍猶如新加坡抗衡印尼和中國等較大鄰國的保單。
新加坡小心翼翼、兼顧東西方的平衡舉措,反映了亞洲當前不安定的權力平衡。無可避免地,這也有得罪雙方的風險。當我問李顯龍,中國對於新加坡口頭支持美軍繼續在太平洋露臉一事的看法時,他心平氣和地回答:「他們不喜歡,但能諒解。」他繼續解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我們仰賴美國人在這邊扮演良性而有效的角色,就像他們自大戰以來一直在做的事那樣。」新加坡的樟宜軍港是兩艘美國戰艦在此區活動的重心,二○一五年,中國聲索領海之舉引發緊張情勢,美國海軍宣布再派兩艘軍艦固定輪流進出新加坡,並有針對性地指出,這些沿海用的船艦非常適合在南海的淺水域運作。但李顯龍的官員不願用「基地」一詞,來形容美軍於新加坡的存在,也幾乎沒有美軍人員駐紮於此。對新加坡人來說,美國海軍並非以他們城邦為基地,他們只是使用了設備而已。
新加坡人的敏感充分反映出,為了華盛頓和北京兩邊都不得罪,新加坡的行事有多戒慎恐懼、委屈求全。無疑地,當二○一四年越南和中國爆發海事爭議時,新加坡國營媒體的新聞報導顯然刻意保持中立。任何希望東南亞能稍微團結一點的人,恐怕都要失望。覺得失落的不僅是越南人,一位白宮官員也跟我抱怨,新加坡什麼也沒做,無意促成東南亞口徑一致以回應北京的挑釁,連公開談論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動都沒有。美國擔心新加坡的政策不僅反映該國現在不想招惹麻煩的自然傾向,還反映對未來微妙的押注。同一位官員在二○一四年跟我發牢騷:「他們常說得一副認為中國稱霸太平洋勢所難免的樣子。」確實,前新加坡外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就很喜歡這樣說:「我們知道一千年後中國仍將是我們的鄰居,但我們不知道美國人會不會在這裡待上一百年。」
因為人口不到六百萬,新加坡的態度或許乍看之下沒那麼重要。但事實上,新加坡與中國和西方獨一無二的強烈連結(與它的財富和戰略位置有關),賦予它遠超過面積和人口代表的地緣政治的地位。如果新加坡的態度被視為接受了東南亞正逐漸變成中國後院的現象,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會因此下結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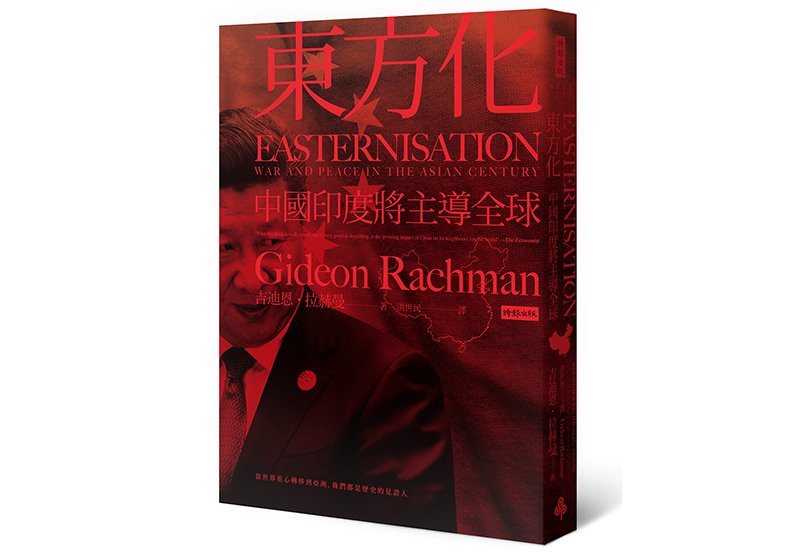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一書,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著,洪世民譯,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