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
某婦女開設牙醫診所,由前夫擔任主持牙醫經營,但自從婦女與前夫離婚後,她將全部希望都放在栽培兩個兒子身上,並舉債兩千多萬元供他們補習、重考及就讀牙醫系七年,並雇用司機接送、女傭照顧生活起居飲食等。當年,擔心兄弟二人將來不願奉養,老年需仰人鼻息,便在民國八十六年間與二子簽訂系爭協議書,議定他們日後成為執業牙醫師後,要以執業收入純利的六成,按月攤還她直到總額五○一二萬元;日後如果媳婦和母親商討或兒子媳婦孝心感人,還可以再考慮減少攤還的金額;另媳婦如果忤逆母親將喪失對遺產權利等語。
次子主張,和母親簽訂協議書時,他只是二十歲的大學牙醫系二年級學生,竟約定他日後須清償母親扶養費用,且將母親扶養兒子的時間、心力換算成金錢,已違反
公序良俗,應屬無效。
一審判決
不認為違反公序良俗,認為原告真意在於返還扶養費用,但扶養費應依一般社會消費情形計算。
一審新竹地院判決,由於是第一次事實審,地院花了不少篇幅在整理原告的陳述,本案原告也就是母親,非常令人意外地,她並沒有請律師(除了三審外),所以關於她扶養支付的名目金額,法院花了很多心力整理在判決附件,原告鉅細靡遺列舉了過去幫兒子支付的費用項目,包括女傭二十四小時服務、有機米、黑毛豬、土雞每星期一次送給兒子、鍋碗瓢盆、搬家費用等都列出來。
但地院所認無名契約何以不得據以請求返還的理由,並沒有說得非常清楚。但另一方面,地院也沒有以違反公序良俗宣告無效的途徑,阻擋原告向兒子請求返還扶養費用。
地院以原告各次開庭的陳述,認定原告真意是請求被告返還扶養費用,但認為二十歲前所支付的,是原告履行對未成年子女的扶養義務,不得請求返還。而地院認為不應該隨原告主張單方面任意給付都需返還,必須以日常生活所需為限,因此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的每人平均月消費支出,判決被告應返還一七○餘萬元。
二審判決 違反公序良俗無效
高院直接認為因為次子才剛滿二十歲,原告就急著跟兩個孩子簽署返還扶養費用的協議書,使其與兄長需負擔五千多萬元的債務,顯違父母子女倫常,這份協議書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而無效。
高院也認為:即便滿二十歲,母親雖不再需要負擔未成年子女的扶養義務,但也有直系血親相互間的扶養義務,二十歲的學生雖有工作能力但不能期待其工作(無謀生能力),所以不是成年在學學生就喪失受扶養的權利。
我認為其實這可能比較符合目前大多數民眾的第一時間法律感情,一般可能認為母親這樣的作法將扶養的義務過度以金錢衡量,似乎太過現實。而一般二十歲還在讀大學的學生,沒辦法全職工作,多仰賴父母親的資助才能完成學業、取得在社會上謀生的基本條件,如何有條件與地位與母親對等切磋此一鉅額扶養費條款?不過我揣測,因為這約定有些悖離一般人法律感情,才造就本案有新聞價值可言。
系爭協議書背後的動機
這個案子讓朋友打趣道:還好父母「涉世未深」,沒有跟自己簽下這種協議書。
我們來觀察一下這位法律上「深謀遠慮」的母親,她將自己的婚姻與事業結合在一起,前夫有牙醫師的專業技術,加上她的出資,開立了牙醫診所。不料,在七十九年就因前夫(從判決中推測可能有)外遇情形而雙方離異,前夫另外在新竹地區開立一家牙醫診所。
這位具備經營牙醫診所的經驗與know-how 的母親,原本將希望寄託在兩名兒子身上,希望他們能繼承牙醫衣缽。終於,在兒子經歷重考、轉系等辛苦過程後,總算不負期望考上牙醫,兒子還從就學時代就結交同居女友,但這位單親母親顯然因為自己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因此,格外重視兒子的女友有沒有可能孝順未來的婆婆。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猜測恐怕這位未來媳婦受到的檢視壓力非常大,要跟未來婆婆相處融洽應非易事。母親在重重的不安全感之下,遂急忙與甫滿二十歲的兒子們簽立了這系爭協議書。後來,最不願見的事情果然發生了,這位兒子恐怕與母親越來越生矛盾,終於不願意再在母親經營的牙醫診所上班,甚至兒子下一份工作就是前往母親最不希望的去處,那就是前夫的診所。我猜測這應是這起訴訟的導火線。
最高法院 本案契約還沒有到需要宣告無效的程度
最高法院先說明「違反公序良俗無效」的法律規定,是在對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的限制,涉及生存權時,必須要考慮雙方處境的優劣以及基本權被侵害是否具有明顯的反社會性。
本案中,最高法院探究協議書的其他記載:認為她所定的返還金額條款具有金額上限、並以收入純利六○%計算,且有記載將來可能有減少催討的可能,以及關於遺產分配的原則(就是未來媳婦要孝順她)。綜合判斷,認為系爭協議書尚沒有到達反社會性嚴重的情況,也不致於肇致兒子日後無法生存。亦即,母親載明只要兒子、媳婦乖乖,將來金額還可談,以此暗示了發回更審的法院應該讓本案通過契約有效性的門檻。
只是,二十歲的兒子在簽約當時是否在經濟、學識、經驗不具有結構性劣勢?
最高法院似乎認為兒子還有磋商的空間與能力。但我想最高法院若真的這樣評判我國二十歲的孩子,恐怕有點高估了二十歲的成熟度,加上磋商的對象是母親,不簽也許下學期就被趕出家門或母親不幫繳註冊費了,兒子能說不簽嗎?
高等法院更一審 對直系血親尊親屬的扶養義務非不得事先約定
更一審高等法院承繼著最高法院的開示,並且引用了民法第一一二○條,認為扶養方法與費用,當事人非不得事先協議之。另外認為此依約定並不會肇致兒子日後無法生存,也沒有其他訂約的瑕疵,或施以詐術或強暴脅迫之情形,而兒子既然成年,有相當智識能力理解協議書內容,並且依照自由意志決定是否可以簽訂協議,所以認為系爭協議書有效。更一審高等法院認為雙方的真意應該是「對日後扶養母親的方法與費用」予以協議,這邊就不同於原先第一審地院的認定了,地院是認為真意是「返還過去代墊的生活費用」。也因此更一審高等法院直接計算兒子執業以來的純利之六○%計算,扣除若干代墊費用之後,判決兒子應付母親二二三三萬餘元。
月薪嬌「媽」?我的愛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
這不免讓我聯想起日劇《月薪嬌妻》,劇中男主角是一名忙碌上班族,與原本僱來日常幫傭的女子—也就是女主角,辦理「契約結婚」。男子仍以女子的實際工時給付薪資,女子則同住一個屋簷下,對外宣稱是夫妻入籍,藉以節省稅捐及兩人的生活支出。但兩人日後萌發愛情後,成為真正的夫妻,丈夫是否可以兩人生活是有感情基礎的,就不再給付全職主婦的妻子薪資了呢?而女主角也質疑如果不給予,是否就是一種情感的榨取了呢?
這些問題繼續衍生,我們可以思考看看,夫妻或親子之間對於日常生活經濟上的相互付出,撇開「愛」的成分後,能不能以金錢衡量?這種觀念在傳統世代是無法想像的,但到了下一世代是否能延續傳統思維?法院的判決又可能對新倫理的架構推波助瀾嗎?
從最高法院以及更一審高院的判決傾向看來,對於當事人締結契約的自由(私法自治),法院仍然是最大程度給予尊重,非嚴重到不通情理,一般人聞之均憎惡(反社會性),原則上法院是不隨便宣告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的。
但觀察判決脈絡,基本上還是有幾個負面排除的判斷標準,我認為此類扶養費給付、返還扶養費用預定,或是婚前協議等條款要被宣告有效,應該要具備這些條件:「法律未明文禁止」、「條款的自限性」、「可得確定性」。
其一、「法律未明文禁止」這應該很好理解,就像更一審高院找到的民法第一一二○條,未來扶養費的方式可以容許預先約定。
其二、「條款的自限性」,這指的就是條款不是一面倒,而是有個限度,有個「時間上」或是「金額上」的限度,不是「無條件」、「無限期」,若協議中出現「無條件」、「無限期」這幾個詞,恐怕在契約效力上就比較容易遭到法院的彈劾。
其三、「可得確定性」,指的是契約給付的標的或是給付條件,不是個虛無飄渺的東西。本案的「孝心感人」有點處於灰色地帶,但鑑於它是個減少給付的斟酌要件,所以最高法院還是讓它過關了。
我認為,高等法院更一審認定本案母子之間的協議,本質上應是對未來扶養費的約定,應值贊同,繼而,基於上開文中所說的幾點判斷標準,我認為此協議書應該不致於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
但至於扶養費約定,能否因為締約人的締約自由受到壓縮,能否考慮適用或類推民法七十四條「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的規定予以酌減?可能也有待再研究。
未來本案若有再上訴到最高法院,希望看,最高法院是否再一次確認這些標準,這些判決真真切切可能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與家人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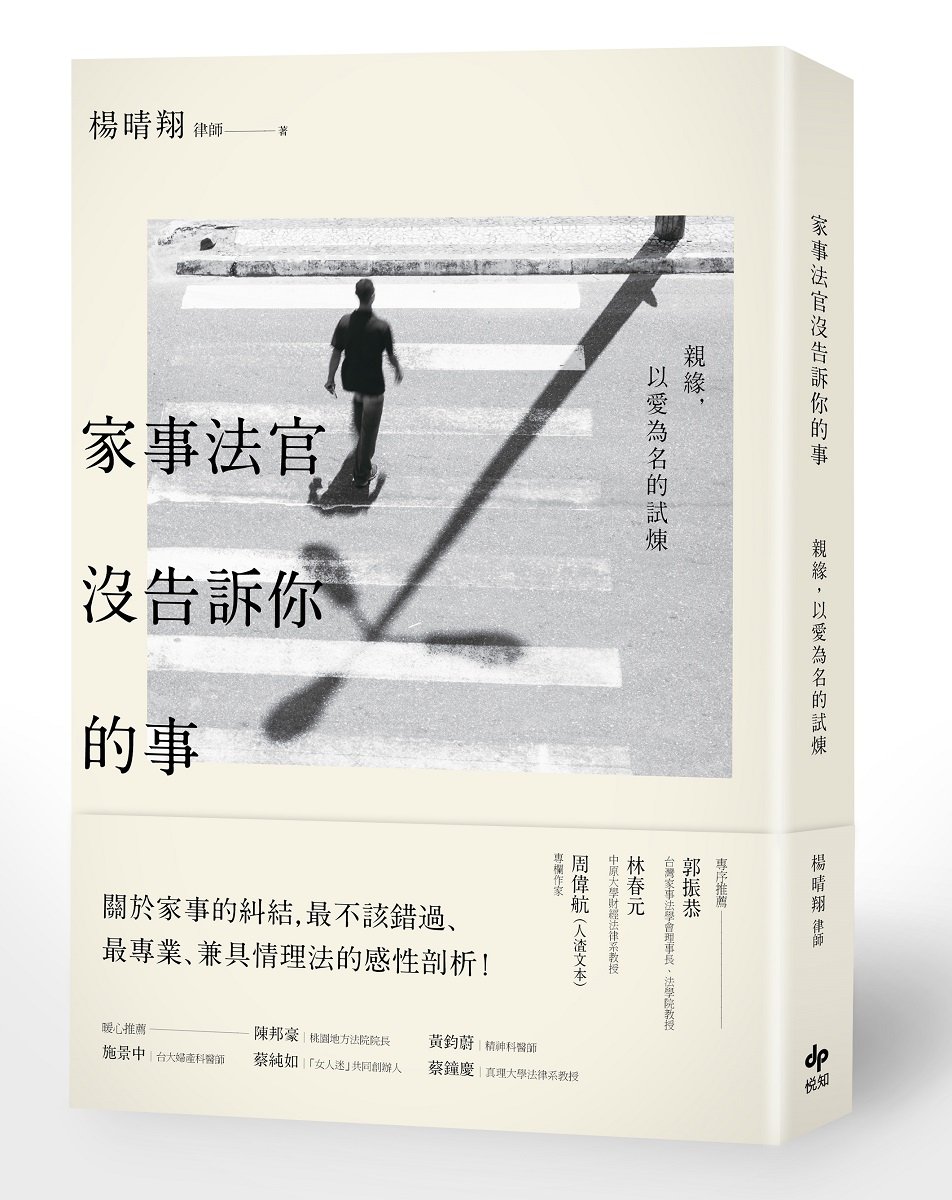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親緣,以愛為名的試煉》一書,楊晴翔著,悅知出版。
圖片來源:pakuta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