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內心深藏著一種對債務的矛盾心理。我們熱愛手上的信用卡,那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小道具,不過很多人也發現,支出狂熱的歡愉中總隱藏著一絲淡淡的罪惡感。不知怎地,一般人似乎都覺得儲蓄比借錢消費有道德。這種感受對我們眼前的討論很重要,因為在倫理道德及資本主義的論戰中,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變得愈來愈重要,而且令人不得不擔憂。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凱因斯就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提到,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關係,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終極基礎。人類看待債務的矛盾心理,也因世世代代的人愈來愈支持債權人(而非債務人)的強大法律及文化偏差,而被強化。凱因斯在戰後那一篇論戰短文中,尋求攻擊這樣的偏差。
這個偏差由來已久。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古代巴比倫國王漢摩拉比(Babylonian king Hammurabi)法典──是大約西元前一七九○年起草擬,它一開始就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規定無力還債的人應該將自己、妻子、孩子、妾或奴隸賣給債權人,或將家人分送各地從事強制勞動,以免除未清償的債務。1這套法典中也設定了利率的上限,穀物出借的年利率最高為三三%,可用相同的穀物償債,另外,出借特定重量的白銀,年利率為二○%。
那些規定提醒我們,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衝突,說穿了只是反映有錢人和窮人之間由來已久且永無止盡的鬥爭罷了。古典歷史學家芬利(Moses Finley)的評論也提醒我們:自古至今,各地反覆不斷爆發革命,這些革命的主要訴求都是和解除債務及土地重分配的呼聲有關。另外,誠如新聞工作者科格安(Philip Coggan)在最近一本有關金錢與債務的精采書籍中寫到的: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稜鏡──放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戰爭──看見所有經濟歷史。他巧妙地引用十九世紀初一位美國思想家泰勒(John Taylor)的說法,泰勒說:銀行產業「將國家分成兩種族群,一種是債權人,另一種是債務人,而且讓他們彼此之間充滿敵意。」歷史是非常好的起點,因為歷史殷鑑能讓我們體會,即使在現代,一旦債權人允許家庭、企業或政府過度舉債,債務也能產生動搖經濟體系的能量。過度舉債和脆弱的銀行體系一樣,都可能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正常運作。
首先,請注意,古代由漢摩拉比法典創始的債務人/債權人關係的野蠻規定,因自由主義的一次大爆發而變得緩和一些。大約在西元前六百年,雅典法治改革者梭倫(Solon)在一場局部導因於過度舉債行為而起的經濟危機過後,提倡廢除所有利率限制、降低或撤銷很多債務,同時禁止個人以當奴隸來抵債的行為。不過儘管有這個前例,一百五十年後遭遇類似經濟危機的羅馬人,卻捨棄梭倫的手段,選擇回頭採用漢摩拉比的方法,重新對貸款利率設限,同時允許債務奴隸的存在。
從那時開始,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勢力就不斷來回消長,只不過,諸如債務奴隸之類的極端懲罰手段早已不復存在。然而,近代的債權人還是繼續享有,能將倒債的借款人送進牢裡的非凡法律力量。諸如馬夏爾西(Marshalsea,這個監獄在狄更斯的《小多麗》〔Little Dorrit〕一書中占有極吃重的地位)等債務人監獄,向來以慘無人道著稱(幸好現在這類監獄已廢除),而這類監獄的存在,證明了世人這種維護債權人的偏差。
連語言都有加強非難債務的傾向。在耶穌使用的阿拉米語(Aramaic)中,「debt」(債務)一詞是個雙關語,除了代表債務,它也意謂罪惡,另外德國文字「schuld」的詞源,也連結了債務與罪惡兩個意義,這或許是德國人在管理國內經濟與經營國際貨幣關係方面,極端遵守財務保守主義的因素之一(儘管還有其他很多因素)。不過,債務的道德寓意並不像這種優良持家觀點所顯示的那麼一番兩瞪眼,而且那種觀點和現代資本主義有點格格不入,這是說明「看似常識的觀點可能對經濟有害」的經典例子之一。誠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波洛紐斯(Polonius)對阿提斯(Laertes)的建議:
不要向人借錢,也別借錢給他人:
因為貸款經常無法回收,還會因此失去朋友;
何況,借錢也會模糊節約的界線。
就心理層面來說,這是非常敏銳的觀點,但絕對會造成經濟停滯。
多數人都認同「債務人/債權人關係充滿難題」的說法。首先,一筆牽涉到「今天借錢給某人,以換取對方未來償還更多錢」的金錢交易,總是隱含經濟疑慮,因為所有以舉債方式來取得資金的投資活動都難免有風險。另外,即使是誠實的借款人都不見得有能力還錢。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裡的安東尼奧便是最佳範例,他的債權人是夏洛克。而且事實上,直到相對近代,授信行為都還被視為一種友誼與信賴的行為;這種行為隱含一種道德與社會意義,而且財務上的義務還能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償還。但在莎士比亞那個時代的人眼中,夏洛克以那麼狹隘的法律與財務觀點來看待他對安東尼奧的放款,一點也不足為奇,因為身為猶太人,他並不受基督教社會重視親戚及友誼的觀念所束縛。
以當時的風氣來說,夏洛克的貸款條件非常獨特(一旦違約,貸款人將遭受合法但不合理的懲罰),因為在那個時代,債務的清償通常不是以財務的形式進行。詩人米爾頓(John Milton)的父親是位放款人,經營放款收息的事業。這位年輕詩人的太太包威爾(Mary Powell)的父親,曾拖欠米爾頓的父親約三百英鎊,於是,他提議把女兒嫁給米爾頓,以取代擔保品。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莫札特的《費加洛婚禮》,它是以博馬舍(Beaumarchais)的歌劇為基礎;劇中一個老管家瑪賽琳娜(Marcellina)借錢給費加洛,但費加洛逾期未還款,對方提出的懲罰條件便是要費加洛娶她。不過,最後他發現自己是瑪賽琳娜的非婚生子,所以逃過這個懲罰。另外,也請注意,雖然十九世紀有無數小說的情節和無力還債有關,但如今這樣的故事情節多半消失。那無疑局部反映了一個事實:隨著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變得愈來愈複雜且不講人情,債務關係的道德及社會意義逐漸沒落。在此同時,開明法律的約束也讓債權人比較不那麼殘忍,讓因債務而淪落到被羞辱、乞丐、娼妓與自殺(巴爾札克、左拉、狄更斯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中常見到這種情節)的人大幅減少。
所以說,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非常微妙的。雖然債權人總是占據天生的有利地位,但隨著債務的規模增加,那樣的偏差也會消失。據說凱因斯曾評論:「如果你欠銀行一百英鎊,你會很頭痛。但如果你欠銀行一百萬英鎊,換它得頭痛。」當債務人瀕臨違約邊緣,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的動態會變得有趣。舉個一九七○年代中期金融危機期間貼切的案例:一九七七年,英國地產公司(British Land)在李特布雷特(John Ritblat)領導下,碰上嚴重的現金緊縮問題。該公司的歷史記載:
每天都得和銀行人員開會。在信用危機來襲前的繁榮時期,並不是每一份貸款文件的精確或詳細度都符合銀行的要求,所以,經常得和律師開馬拉松式會議,且所有律師費用都得由貸款人負擔。後果就是,新條件規定的法律義務愈多,貸款人就益發難以恢復業務的穩定性……但到了某個階段,銀行方面負責本公司業務的資深銀行人員之一,堅持要向公司的董事會詳細解釋他的銀行對英國地產公司當時的財務狀況有何看法。他看起來很憂鬱,而且最後還問董事會是否同意他的評估以及他對細節的掌握度是否充足。
李特布雷特說:「喔,不夠充足。情況比你解釋的糟多了。」他接著補充很多解釋,讓那個遺漏非常多資訊的銀行人員和他的團隊困窘不已。
等到那些債權銀行察覺到它們捅了多大的婁子後,隨即做出一個明智的結論:銀行需要李特布雷特協助它們解決先前輕率放款行為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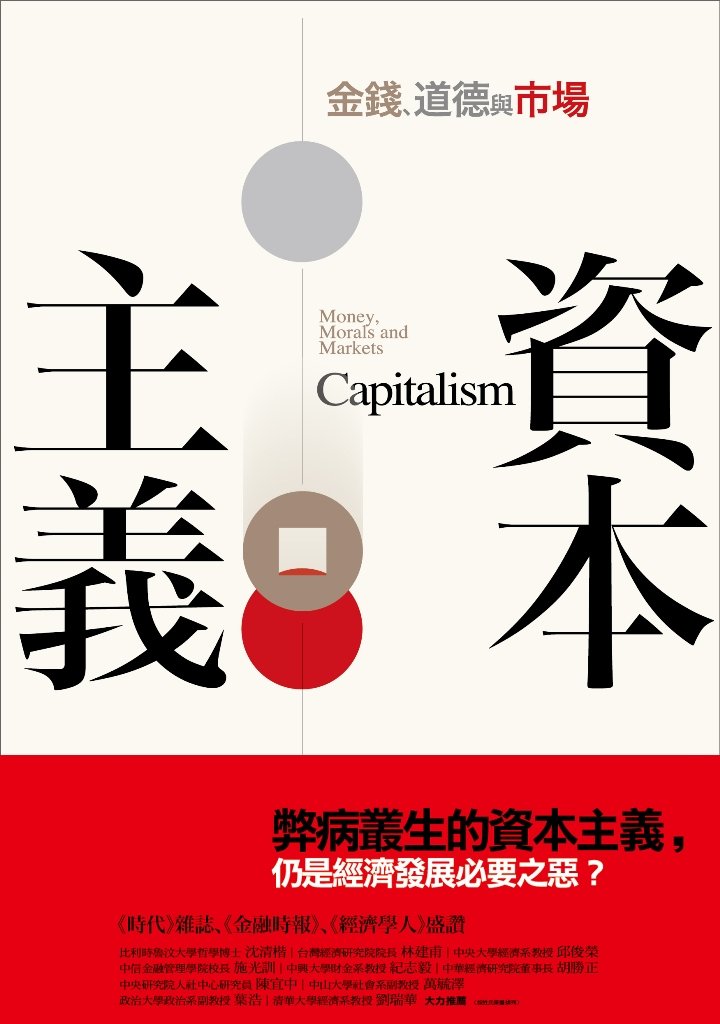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資本主義:金錢、道德與市場》一書,約翰‧普倫德(John Plender)著,陳儀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f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