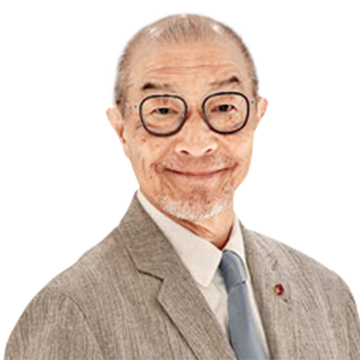今天出現中韓斷交的情況對我們來講,當然很失望,都不能因此讓兩岸交流遲緩下來。我們現在國統綱領有近程、中程、遠程,這三個階段,都經過主觀、客觀的評估;要交流遲緩,就表示原來設定的方向是錯誤的。
兩岸民間交流的目的,是從進瞭解、降低敵意,直到你不杯葛我、我不杯葛你。
交流的著力點--人
我們推動兩岸交流的著力點,也不是在中共政府,而是在大陸的中國人。讓廣大的中國人瞭解到台灣中國人的社會體制、經濟發展與歷史文化,彼此影響,促進社會多元、政治民主。
當兩岸民問交流擴大,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會改變;另一方面,中共的領導階層,也比較容易體會;如果他們一直霸氣,再加上如果中國大陸的政革開放不成功的話,是會形成中共所顧慮的「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出現。
至於「一個中國」的概念,除了書本教我們的以外,我自已也在檢討,究竟這「一個中國」的問題在那裡?為什麼台灣有人談到「一個中國」會感到很猶豫?
例如去年,我到北京去談文書驗證,對方說,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當時我很警惕,趕快翻國統綱領,裡面也有「一個中國」的原則,講得清清楚楚--我們秉著一個中國的原則,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一切爭端;基於此,我跟對方說,好,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對等互惠互相尊重的精神,我們來談兩岸如何共同防制海上犯罪。對方對於「相互尊重」說沒問題,但看到「對等互惠」就很緊張。
大陸方面談「一個中國」,我們國統綱領也是「一個中國」,我們為什麼緊張呢?
後來到了香港機場,有人告訴我,有人認為如果我們白紙黑字寫「一個中國」的原則的話會有問題,因為國際社會一般認為,看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我們早在擬訂國統綱領時,就應對這個問題深思熟慮過了。
至少「一個中國」這四個字,是在今天主觀、客觀條件下--主觀指我們的領導階層認為我們是中國人;客觀條件是,我方絕對不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方不能接受中華民國--我們取其中,而產生「一個中國」四個字。
有危就有機
今天如果我們跟對方的關係已經進入遠程,而大陸體制卻沒有改變,我很同意我們絕對不能把「一個中國」擺進去談,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秉著一個中國的原則談統一,會被對方吃掉。
可是今天我們是在近程階段,談的是共同防制犯罪。文書驗證、掛號信……,寫「海峽兩岸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對等互惠互相尊重的精神,來磋商有關海峽兩岸文書驗證的事務如下……等」,這都不帶政治性的。如果我們瞭解國統綱領的這個程序與用意,「一個中國」就不生困擾,也可以把許多小問題解決了。
今天兩岸政府各有各的想法,要期待雙方想法一致,並不實際,也太理想化;不過老百姓則不一樣,大幅開放比較沒有風險。
當然每件事有風就有險,有危也有機。照大陸今天開放的狀況,及台灣今天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我覺得大幅度開放兩岸民間交流,而不要根本改變我們國防的防衛戰略、戰術力量,就不會造成我們安全的危害,反而提供了我們更深一增的屏障。
今天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才提供了兩岸交流的空間,兩岸關係才得以發展。我們的時機、優勢和方法都需要運用智慧,子孫的福祉與安全才會有保障。
今天我們大陸政策的困境是,我們沒有共識,都有一些矛盾。內部有統獨矛盾;外交政策和大陸政策也有矛盾,就像「一個中國」的概念,產生了很多困擾。
儘管客觀立有困擾,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主觀上有沒有想清楚究竟要怎麼做。
兩岸要突破的是心理上的障礙;突破後海闊天空,很多事就可以做。
譬如經貿方面,政府總是擔心老百姓走得太快,跑去了怎麼辦?那麼是不是可以考慮設定一個基金或一許畫,類似美國早期對往拉丁美洲或東南亞投資的企業提供保險,保障老百姓到大陸投資,有什麼風險,政府可以負責;相對的,政府也可以瞭解企業對大陸投資的實際狀況。
如果政府用這種方式支持民間,加上有個很積極的大陸經貿政策,政府就比較可以和中共的主管,透過海基會說,今天我有一個很積極的、前瞻性的且善意的計畫,就是鼓勵台灣工商業界到你那裡去;既然我方是善意的,這就成了一個雙方共同合作的計畫。
大陸體改,台灣不能缺席
另外像文化上的「希望工程」,今天政府只要拿一億;或者不拿錢,李總統和郝院長捐出一日所得,為「減少一個大陸失學兒童,增加中國一分希望」來盡中國人的一份力量;這些都是積極的、善意的,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認為今天我們能跟中國大陸之間有所突破,不是因中共領導人對台灣採取什麼措施,而是基於它本身的需要。當他們在體制止改革開放時,不管是積極的或消極的,我們都必須要參與,才能提供我們子子孫孫長久的保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陸各種改革如果成功了,我們要獨立也不會冒大險,因為當它走向一個成熟的社會時,才比較不會侵犯我們。
無論主張獨或統,兩岸關係的改善絕對都有幫助。對兩岸關係,每一個中國人不能對歷史繳白卷。如果大家有這樣的認識,也比較可以建立共識。
(苗天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