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殺問題再拉警報。2024年自殺死亡人數4062人,時隔14年重返十大死因。青壯年族群全面上升,其中25至44歲增幅最大,接近一成;青少年自殺率在十年間翻倍,反映東亞社會單一價值觀的壓力。更嚴峻的是,多數個案生前未被關懷系統列案,65歲以上僅17%,男性未通報比例更高達八成。
青壯年自殺全面上升,青少年十年翻倍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呂淑貞指出,台灣自殺標準化死亡率在2006年達到高峰後曾一度下降,但2019年起逐年回升。2024年全台共4062人因自殺死亡,較2023年增加164人,再度擠入國人十大死因。
攤開分齡數據,呈現兩大警訊。首先,15至24歲青少年近十年自殺率幾乎翻倍,2024 年比前一年再增加14人(+5.4%),已躍升為年輕人死因的第二位,高於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全球第三位,其中女性增幅尤為明顯。
其次,25至44歲族群在2024年新增105人(+9.2%),成為增加最多的年齡層;45至64歲族群也增加60人(+4.5%)。至於75 歲以上長者,僅2024年首季就比去年同期多出20人,再度凸顯久病不癒與照顧壓力的沉重挑戰。
逾七成自殺者生前未被列案,男性高達八成
呂淑貞表示,根據衛福部2024 年死因統計,男性自殺率為每十萬人口17.0人,女性為 9.9人,約為女性的1.7倍。
分析顯示,僅約26.9%的自殺死亡者,在生前曾進入關懷訪視系統,其中男性未通報比例高達79.5%。另外,通報率也隨年齡增加而下降:0至24歲為38%、25至44歲為 35%、45至64歲僅26%,65歲以上更低至17%。呂淑貞強調,通報不是壞事,而是「接住生命」的重要環節,政府與社會各界必須持續擴大守門人訓練與資源覆蓋。
她也提醒,許多男性或特定職業群體因擔心被貼上標籤而抗拒求助,社會須營造無污名的氛圍,讓需要協助者敢開口,否則壓抑只會不斷升高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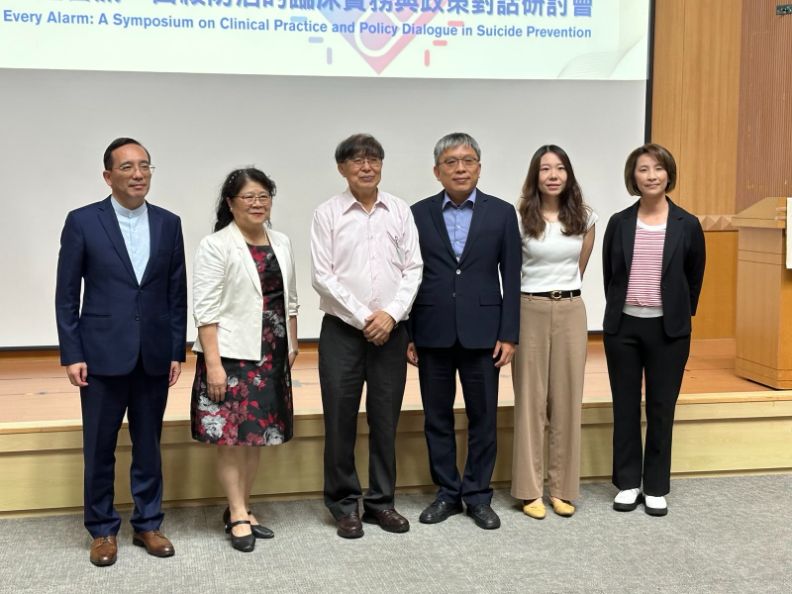
青少年自殺率升高,東亞年輕世代陷風險網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陳柏熹指出,台灣青少年自殺問題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等高工業化、都市化國家有相似趨勢。
他說,這些國家普遍存在對「成功」的單一標準,加上教育競爭激烈、房價高漲與就業困境,讓年輕世代承受龐大壓力。少子化並未減輕孩子的負擔,反而因資源過度集中與關注,使壓力更為加劇。
相對地,澳洲與加拿大的自殺率近年呈下降趨勢。陳柏熹分析,原因不僅在於建構心理健康系統等「硬體」措施,也包含「軟體」面向的社會氛圍調整。這些國家更鼓勵多元人生選擇,減少單一價值帶來的比較與競爭枷鎖,證明制度設計與早期防治能發揮關鍵作用。
衛福部拋三政策:救急、可近、高風險支持
針對防治青壯世代自殺,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陳柏熹表示將以三層次推動。一是救急:除1925安心專線與文字協談外,2024年新增「心理健康急救方案」,讓第一線助人者能像 CPR 一樣即時介入。
二是提升可近程度:全國心理衛生中心正持續佈建,今年目標為71處,明年將增至100處,提供更廣泛心理支持服務。同時,政府推動青壯世代「三次免費心理諮商」支持方案,並非僅止於三次,而是透過初步篩檢辨識高風險者,協助銜接後續醫療。
三是針對高風險族群:以青少年學生為例,已啟動「嚴重情緒障礙早期介入方案」,由專業團隊進入校園提供外展服務;教育部也同步推動社會情緒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心理韌性。
醫師觀察:反覆自傷要關注、黃金追蹤是關鍵
北醫附醫精神科主治醫師洪珊指出,自殺往往呈現「階梯式」進展,從意念、計畫到企圖,最終可能導致死亡或未遂。過程中有些人會透過自傷發洩情緒,雖非以死亡為目的,卻因反覆行為而隱含高度風險,須嚴格關注。
她表示,醫院的防治策略分為三級:初級著重院內與社區衛教;次級則在病人入院時以「全人量表」篩檢心理狀況,若分數過高,會立即轉介社工或精神科;三級則針對急診自殺企圖個案,啟動通報與治療機制。例如,一旦量表顯示高風險,系統會自動通知社工追蹤,並強制精神科會診,確保病人即時獲得支持。
國際數據顯示,急診後的黃金追蹤期極為重要。美國建議30天內安排複診;台灣因醫療可近程度更高,通常能在3天內安排精神科門診,確保高風險個案持續受到關懷。
洪珊也舉出多個臨床案例:有青少年因幻聽與妄想而走向極端;一名外籍配偶在憂鬱與家暴壓力下,險些帶著孩子一同輕生;年輕女性因人格障礙反覆自傷,最終在跨院合作下逐漸穩定;酒精成癮者則因健康惡化並疑似自殺而猝逝。
她強調,這些案例反映不同族群背後,皆有複雜的疾病與社會因素,須透過跨專業合作才能有效介入。

心理師觀點:同理傾聽、灌注希望
北醫附醫臨床心理師黃意霖指出,自殺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心理特質、童年創傷、家庭功能失衡、社會孤立、經濟壓力與污名等多重影響交織的結果。真正引發行動的,往往只是「最後一根稻草」,因此若能在日常中及早察覺風險訊號,並給予支持,就可能改變事件走向。
她指出,臨床會執行系統風險評估,包含意念頻率與強度、觸發情境、是否出現具體計畫、是否有相關歷史,以及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平衡(如責任感、家人、自我價值等)。
治療核心在於建立「治療聯盟」與灌注希望。透過同理傾聽、以「我們」為主語同行,把抽象痛苦轉化為可操作目標,允許個案在狀態不佳時採「低耗能模式」,讓希望感逐步落地。
在危機處理上,黃意霖說,心理師會與個案共同擬定個人化警示訊息與應對清單,預先連結校園、家庭與醫療資源,並確保環境安全。
她也提到,政府提供的三次免費心理諮商,降低求助門檻,讓高風險個案踏出第一步;但前線專業者承擔的壓力同樣龐大,亟需常態化督導與同儕支持機制。
人人都是守門人,共織生命安全網
專家共同強調,自殺防治不是單一部門的責任。呂淑貞呼籲打破污名,提高1925安心專線知曉率(據2024年自殺防治認知調查,目前不到8%),並加速校園與職場心理師配置。
陳柏熹提出「社會處方箋」,強調透過文化、運動、藝文與社區活動,重建人際與社會連結。洪珊與黃意霖則提醒,人人都能是守門人,陪伴與傾聽就是最基本的支持。
專家一致呼籲,自殺並非無法避免,而是可預防的公共衛生挑戰。唯有及早辨識、及早介入,並凝聚家庭、學校、社區與醫療力量,共同織起生命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