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僅12歲的林品彤,在電影《小曉》中,飾演一名罹患ADHD的女孩,贏得2023年第60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創下國片影史紀錄;而讓家長、學校備感困擾的ADHD,也因此引發注目。根據研究,ADHD患者有增加的趨勢,甚至與新冠肺炎引起的腦霧相關,不但影響工作、家庭,也讓人際關係受挫。英國對心理疾病的去汙名化,也許可以成為他山之石。
什麼是「ADHD」?
「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kinetic disorders, ADHD)以往是小兒科醫師受諮詢的常見議題,近年來,ADHD開始在成人精神科醫師、神經科醫師,以及內科醫師之間,成為討論主題。
據估計,全球兒童心理臨床案例中,有50%的比例證實為過動兒,比例很高。由於ADHD對這些幼小患者的生活造成潛在影響,適當確診和治療,成為必須重視的課題。ADHD的主要症狀有:一、與相同心智年齡者比較,患者的專注時間短;二、容易略過思考行為的後果貿然行動;三、容易分心、無法專注需完成的事情;四、躁動,動個不停。

另據《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IV, DSM-IV)的標準,前述特徵主要可分為兩類;注意力缺乏及過動(衝動)。年幼患者的異常行為大多出現在七歲以前,部分症狀甚至在學齡前就可發現,通常需經至少六個月以上的觀察,藉以排除環境或社會心理壓力導致的行為模式改變。不分年齡的患者ADHD行為,必須在不同環境下都能被觀察,同時頻繁地發生於學校、家庭、社會和工作環境後,才能確認罹患ADHD。
ADHD不同於「廣泛性發展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PDD,又稱社交障礙)、「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或是其他「精神病疾患」(Psychotic disorder)引起,也不是由精神障礙引起(如情緒障礙,焦慮症或人格異常)。
ADHD屬於「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之一,這個概念當初由一位澳洲女性社會學者莘格(Judy Singer),在1990年代所提出,莘格本人即是一位自閉症患者,她在研究後指出,「神經多樣性」肇因於大腦結構及功能的差異,這些差異導致許多腦中非典型的認知處理,引發涉及情緒、同理心、注意力不集中和衝動等症狀。
除了ADHD,「神經多樣性」還概括「自閉症」(autism)、「讀寫障礙」(dyslexia,失讀症)、「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和「書寫障礙」(dysgraphia,失寫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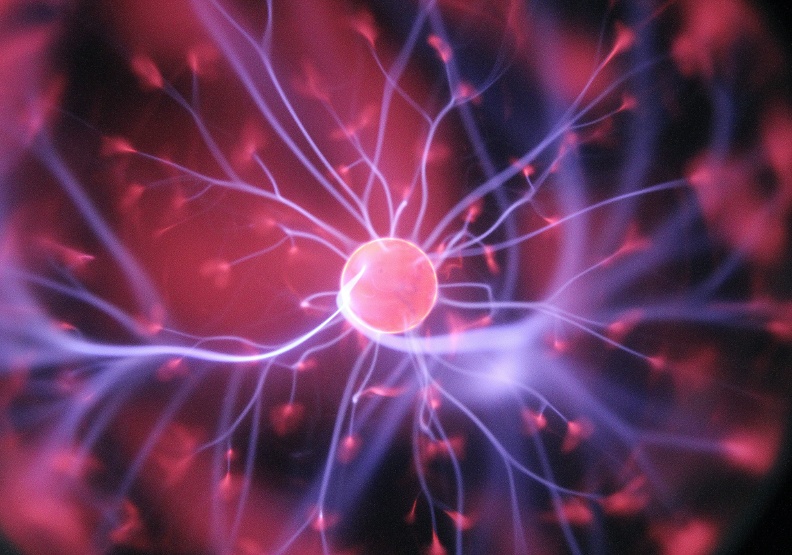
腦霧也會引發「ADHD」?
「神經多樣性」的大腦,在醫學上被視為殘疾,這種殘疾已逐漸出現在各國工作申請或住宿的評估項目中。如今,全球高達20%的人口被歸類為神經多樣性人群,其中高達6.7%的成年人患有ADHD。然而,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的標準,ADHD診斷的關鍵是12歲之前,因此,當大腦在長大後因身心創傷而改變時,會發生什麼事?
2021年,《JAMA Network Open》一篇論文的研究發現,因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腦部執行功能、處理速度、記憶力和回憶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結論提醒,新冠肺炎引發的「腦霧」(brain fog)症狀,確實可能與慢性神經認知的發展有關,甚至加速癡呆症的出現。
研究發現,腦霧基本是因為患者大腦控制執行功能的區域「額葉」(Frontal Lobe)受損所致,額葉涉及人類決策、計畫、使用工作記憶和控制衝動。
無獨有偶,2023年10月,《細胞雜誌》(Cell)上的一篇論文報導,長期的新冠肺炎腦霧症狀,可追溯至免疫系統蛋白驅動的血清素消耗。這個發現與ADHD發生原因類似,兩者症狀都根源於額葉功能受損,由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過低造成,所以,當包括正腎上腺素、血清素和GABA(γ-胺基丁酸)等神經傳導物質分泌不足或耗盡時,便會造成腦霧與ADHD。
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ADHD患者在注意力不集中、過動和衝動時,會尋求更大的刺激,目的就在於刺激大腦釋放更多多巴胺。
當2020年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發期間引起的集體性身心創傷,該怎麼認定?如果全球部分人口的大腦因病毒發生變化,各國社會如何應對神經多樣性人口數量遠比目前得知數量要多更多的情況?

美英如何應對?
在美國,近年被診斷出罹患ADHD症狀的患者人數創下歷史新高,尤其自2020 年以來,ADHD的確診數量激增,儘管仍未知這些患者是單純ADHD,還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但數據顯示,愈來愈多美國民眾加入過動症支持小組。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報告指稱,光是2020至2021年間,尋求興奮劑處方的美國求診民眾比例,從3.8%增加到4.1%。此外,2022年一項統計顯示,82%至94%的美國民眾至少曾確診新冠肺炎一次,其中,22%至 32%的確診者表示,他們的注意力、記憶力明顯下降。2021年的另一項統計指出,22%的確診患者在感染新冠肺炎三個月後,開始出現認知障礙。
美國這些人口普查數據描繪的新冠肺炎腦霧景象,令人擔憂。因此,美國研究人員重點已開始轉向腦霧是否可逆,亦即能否透過興奮劑藥物的短期服用來逆轉病情。巴西研究人員也開始進行隨機對照試驗,用以協助對腦霧與後天性ADHD 的客製化治療。
約25年前,莘格提出神經多樣性的概念,用來描述這些與一般人不同的少數族群,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後,愈來愈多人發現自己罹患某種形式的腦霧(後天ADHD)。為避免遭公眾汙名化,美國國家科學院(NAS)修改對新冠病毒引起腦霧症狀的定義,並偕同CDC,於2024年準備啟動對ADHD罹患率的最新調查。
英國目前有約180萬名心理疾病患者等待治療,與十年前相比,患者透過英國全國保險(NHS)的轉診率增加44%,但NHS的精神科醫生十年來僅增加6%,人力完全無法負荷暴增的病患人數,這一差距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更是雪上加霜。
根據統計,英國心理障礙疾病的預算,僅占NHS的9%,考量未來英國民眾的心理健康,英國國會準備改革將精神病患定罪、汙名化的《心理健康法》(Mental Health Act),同時重啟2023年初遭擱置的心理疾病研究計畫,強調心理疾病患者需要的是學會面對負面思惟,而非過度大規模醫療化,減輕已超負荷的英國醫療體系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