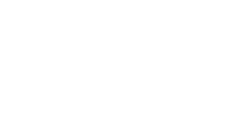(一)中國人需要深思
當前的國際情勢與世界市場已有了巨大的轉變,美蘇的核武裁減、共產國家內經濟政準的嘗試、經濟同盟的擴大、保護主義的蔓延、跨國企業發展的迅速、日本經濟實力之不可抵禦及軍事潛力之不可忽視(軍事支出將為世界第三位),位居亞洲的中國人需要深思。「深思」不僅是為這一代,也為下一代;不僅是為大陸上的中國人,也為大陸以外的中國人。
「一九八八年世界發展年報」剛發表舉世最富裕的十九個工業化國家的名單。以一九八八年每人所得為準,瑞士第一(一七、六八0美元),美國第二(一七、四八0美元),西班牙殿後(六、0六六美元)。十九個國家中,日本是唯一的亞洲國家,名列第六(一二、八四0美元)。
其餘的紐、澳在大洋洲;美加在北美洲;挪威、瑞典、德、法等十四國則在歐洲。新加坡(七、四一0美元)與香港(六、九一0美元)每人所得都高過西班牙,但未列人「工業化國家」。
(二)睡獅比小龍重要?
在人口超過一百萬的一百二十餘個國家與地區中,大多數的國家仍然陷於貧窮。七十三個國家的每人半均所得不及七五0美元。
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曾有過曇花一現的經濟成長。真正擁有持續成長的只有亞洲四小龍--中華民國、南韓、新加坡與香港,它們的經濟成就有三個基本特徵:以外貿成長來帶動經濟、以市場經濟來誘導資源分配、以民營企業來扮演積極的角色,撇開南韓,這三條小龍更有一個共同的分母;都是華人,或者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當三條小龍的經濟成就受到國際肯定時,擁有全世界華人最多的中國大陸像睡獅一樣,它的每人所得不及三小龍的十分之一(見表一)。儘管它的每人所得像印度一樣的低(三百美元左右),甚至比海地、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還要少,但世界各國不敢輕視它。
即使面對當前經濟改革的重重困難,世界銀行在剛出版的年報中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仍做了正面的評價:「在一九七三~一九八0期間,國內生產毛額平均增加了五.四%,在一九八0~一九八七期間,增加了一0.三%。一九八五年時到達頂峰,為一二.七%。每年人口成長率仍是相當低--一.六%,每人平均所得的長期增加趨勢,在開發中國家來說,算是出奇的快,某些地區仍然相當的貧窮,但是人民的健康、識字率、出生時預期壽命與很多中所得國家相近。」
從現實的國際政冶來肴,美國政府高層次的一個長期戰略委員會在今年年初的報告中,預測中共在二0一0年會變成世界第二強國。季辛吉在他剛發表的「給下屆美國總統的備忘錄」(美國新聞周刊九月十九日)中,他認為日本、中國、印度以及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的重要性會與日具增,必須要納入一個新的國際體系,他在四頁多的長文中,居然沒有一句話提到過台灣、新加坡與香港。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希說,如果他當選總統,就要立刻召開世界高峰環保會議,蘇聯、中共是重要的出席者。
在這些西方謀略家的演算中,一頭巨大的睡獅顯然比三條活躍的小龍還更值得重視。
當前的中國大陸,因其地大物博,十億五千萬人口及龐大的軍事力量,得到國際重視,但因所得太低,得不到尊敬;相對而言,台灣、新加坡、香港,因它們的經濟奇蹟得到國際尊敬,但因地域太小而得不到重視。
從經濟策略上來看,克服國內而場狹小、有效運用資源、減少保護主義衝擊、增加本身國際地位的一個工具就是戰後相繼成立的經濟同盟,如歐洲共同市場(一九五七年)與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一九八八年)。
面對這樣區域性經濟結盟的興起與蔓延,面對世界市場這樣的瓜分與保護,分布在亞洲國家與地區的十億多華人如何自處?仍然堅持政治體制的不同,個別發展。受制於美、日等國?或者「讓政冶歸政治」,設法形成經濟合作,凝成一股前所未有的華人力景,為中華民族爭世界一席之地?
做為一個中國人,尤其做為要對歷史負責、對後代子係負責的中國政治家們,還有什麼課題比這個更重要?
(三)鄭竹園與陳憶村的提議
事實上,對亞洲華人的經濟結合,能近幾個月以來至少有兩個值得重視的提議。
一個提議是旅美學者鄭竹園教授上半年在紐約與台北提出的「大中華共同市場的構想」。他指出: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對峙近四十年之後……在現階段政治與經濟制度互異的情勢下,全面性的統一不可能達成,唯一可行的道路,是仿照歐洲國家的先例,成立一「大中華經濟共同體」,或稱「共同市場」。他所提議的共同市場包括台灣、大陸、港、澳及新加坡。
鄭教授並提出幾項原則:(1)各成員維持原有政治經濟體制,不相統屬;(2)共同市場求經濟上的互助,不求政治上的統一,政治統一為未來目標;(3)總部可設在香港或新加坡;(4)共同市場可以減少貿易限制、提供優惠貸款,但不包括資金與勞力的直接交流;(5)成員有自由退出的權利。
另一個提議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研究所所長陳憶村。他與其他五位大陸學者於今年八月下旬與來自台灣的五位學者,一起參加了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舉辦的「中國經濟關係」討論會。
在「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現狀及其發展趨勢」論文中,他建議基於大陸、台灣、香港三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應當共建「中國經濟圈」。他進一步指出:這個經濟圈可採取內、外兩種循環。
「內循環」是結合大陸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市場與台灣、香港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建立產供銷體系。「外循環」是指圈內三個地區經濟一方面繼續自主地參與既有的國際分工與合作,另一方面發揮三方面合作的優勢對外。
大多數與會的學者都覺得陳先生這個建議有他的前瞻性。日前台灣與大陸經過香港的間接貿易,在過去十年間(一九七八~一九八七)為五十六億美元,今年預計達到二十億美元。陳先生也在文中強調:「雙方均應注重經濟效益,減少政治干預,加強合作,互通有無,」關鍵當然就在政治干預。
如果沒有國家安全與政治體制的考慮,台灣可以向大陸提供各種生產設備、中間原料、耐久消費品以及各種形式的投資;大陸可以向台灣提供石油、煤、棉花等農工業原料及龐大的潛在市場。
在討論會上,于宗先與陳明二位教授認為,基於各種因素的考慮,時機尚未成熟,筆者也認為:在日前,文化交流遠比直接貿易與直接投資更切實際。
(四)他山之石
不論是狹隘的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廣泛的共同而場,最初的目的即往一定期限內,相互裁減關稅、設限、人為的貿易障礙,並且對外採用一致的稅率;然後准許資本、服務及勞力移動,甚至最後建立相近的農業、運輸、金融.社會福利等政策。
由於國與國及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錯綜複雜因素的糾纏,即使較單純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不是三年或五年可以簽訂的。以美加雙方關係的密切,二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構想遠在一九四七年就由加國提出,最後雙方簽約是在今年一月,前後相距四十一年。
一九五七年,歐洲共可市場創設時,六個國家終於克服了歷史上的恩怨、政治上的猜忌、文化上的互異、經濟上的障礙,變成了受人矚目的經濟集團。
一九九二年時,已擴大為十二個國家的歐洲共同市場將變成一個整體市場,以其擁有的三億二千萬人口及高所得,不僅可與美、日等國分庭抗禮,且已超越美國的國內市場,變成邁向二十一世紀時「最不可忽視的經濟集團」。
在討論「共同市場」時,成員之間的經濟水準差異,不應當是大障礙。例如,歐洲共同市場中,去年葡萄牙的每人所得不到三千美元,而丹麥則超過一萬五千美元,西班牙的失業率接近二一%,而盧森堡則不到二%。
(五)中共領導人的挑戰
當前所提議的「亞洲華人共同市場」或「中國經濟圈」,其困難在於成員之間政治制度、經濟體系、社會開放、生活方式的顯著差異,但是最大的障礙當然來自於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相互對峙。
要克服台灣方面的疑慮,正如不少海內外中國學者所一再提出:中共(1)應宣布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但可附帶台灣不得獨立的條件;(2)應放棄「四個堅持」;(3)不應當在國際組織中排擠中華民國。
如果北平真要建立「中國經濟圈」,那麼中共領導人就必須做上述的政策調整。為使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與經濟改革能產生實效,這樣的調整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陸留美學者陳平今年春天寫過:「經濟上的相互需要,長遠看比政治上的分歧更有巨大的向心力。」北平能做這樣的調整,才真正符合海內外中國人民的利益。如果若干年後其有「亞洲華人共同市場」的創設,最不願意樂見其成的就是日本、蘇聯及其他歐美國家。除了中國人自己,誰願意看到一個民主的、富強的、統一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