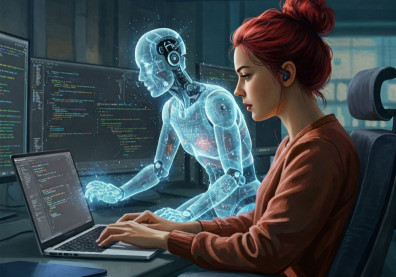4/4一年一度的清明節,追憶逝去親人:如果說這段過程,誰從來沒有苛責過我,沒有急著要我如何,我想那一定是「時間」。但時間所提供的,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就讓悲傷得到了療癒,而是讓我有充裕的機會,探索適合自己的步調與方式,來處理失落與悲傷。(本文節錄自《於是,我可以好好說再見》一書,作者:蘇絢慧,以下為摘文。)
我常常遇到這些喪親者周圍的親友問我:「這樣正常嗎?對嗎?好嗎?」我認為,不需再以社會主流聲音的「正常、正確」標準套在自己身上,評價自己。
二分法的邏輯判斷,並不能帶給我們治癒,反而帶來恐懼。對生命遭逢猛烈撞擊的人來說,生活、人生都像被命運扭曲了,所遭逢的一切也不再是常態生活的狀態,被拋出「日常軌道」外,又怎能再以常態生活的眼光與評價和要求呢?
無論怎麼做,我相信都有理由與意義。把家中所有關於死去親人的遺物丟棄,或保持原封不動,都可能來自於內心不想承認這段關係就此失去,或不想再經驗失去的痛苦,也可能都是他們心中認為最能維繫生存意念,勇敢活下去的做法。
有些人需要暫時封閉所有的記憶,來克服自己面臨的巨大悲痛與生存威脅;有些人則必須不斷的憶起、再憶起,不斷的以為親人還在身邊來度過生命的艱難時期。這些都是人為了因應強大威脅與壓力所產生的防衛機制。
這防衛機制能撐一時,卻非永久,因此必定會有一個時候,當防衛機制不管用時,那否認與不想面對、承認的分離痛苦便會真實顯現。
因此,不需要心急,我一直深信生命會出現一個適當的時機,來幫助人們拿出力量與能力,面對自己一直未完成的事物,包括處理悲傷、完成自我療癒。
生命自有處理傷痛的時刻
我記得,我在失去父親後,即使眼睜睜的看著他的遺體被推進焚化爐火化成一堆骨灰,但內心卻覺得不真實,像作夢般。要如何相信自己所愛的父親,從小擁抱我、愛我的父親,竟然不再有形體,化成了一堆灰燼?
這種不真實的感覺裡,我還覺得是老天開了個大玩笑,這肯定是一場騙局。為了維持自己認為「這不是真的」的念頭,我將父親唯一寄給我的一封信撕毀,然後告訴自己:「你沒死,你只是像過去一樣,不知到哪討生活了。」
這樣堅定、不容推翻的信念,讓我在19歲時寫著關於父親的文章裡,仍是:「我不知你去哪裡了?但我想,有一天你又會抱著屏東的大西瓜在姑姑家的巷口等我,告訴我今年的西瓜特別甜。」
如今寫著當初的心情還是心酸,依舊感到悲傷,也看見當時,雖然已喪父5年,我已經19歲了,心裡依舊不願意好好的告別父親,不願意回想父親死時的一切遭遇,那對我太沉重,我根本沒有力量承受。
真正開始承受、開始面對與處理是喪父12年之後,不知學習了多少知識與智慧來認識自己、瞭解自己,我才隱約感覺到自己有一點點力量,可以重新再看一次早年失去父親的悲痛。
令我訝異的是,那些我原本以為空白,沒有什麼可去言說的經驗,卻在一次次的敘說裡發現——我和父親情感連結的記憶並非原來認為的單薄。那些我原本「封箱」的記憶,慢慢的被我打開,我才驚覺原來自己的生命是如此豐厚,而父親留給我的愛,是那麼足夠,足以支撐我往後的人生。

悲傷不代表失敗
如今我可以自在的敘說父親,也可以在想要思念他時,無懼的好好思念,但我仍無法揚聲高喊:「我走過了悲傷、勝過了悲傷。」我相信,對喪親者來說,失去一位摯親是恆久的悲傷,是永難消除的印記。
然而,悲傷不是代表人生失敗或是不夠堅強,而是紀念一份恆久的愛是存在過的。
當只要憶起那個重要的人,悲傷就在那一刻湧出,沒有停歇,還是如此深刻。但是你會漸漸體會到,雖然悲傷還是再現,卻是不帶傷害自己、貶抑自己的情緒與念頭,而是單純的沐浴在充滿想念的記憶中,感受愛的溫暖在內心散開,再度讓你柔軟地擁抱自己的脆弱,並同時感受到自己的柔韌存在。
這時候,你會深深的體會到「療癒」的意義和感受。
從不敢回憶走到擁抱記憶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很辛苦的;時間雖長,卻是我認為不可避免的過程,我的直覺讓我選擇了一個自己可以面對的時刻。
如果說這段過程,誰從來沒有苛責過我,沒有說過風涼話,沒有急著要我如何,我想那一定是「時間」。
但時間所提供的,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就讓悲傷得到了療癒,而是時間讓我有充裕的機會,探索適合自己的步調與方式,來處理失落與悲傷,不是照著別人的步調,照著別人應該的方式與態度來面對。
時間,也能讓你走過更多生命歷練,用更成熟和穩健的人格和心智來理解生命的生離死別。
在悲傷療癒的路上,我們需要高度的尊重自己,高度看重我們與所愛的人之間的情感與曾有過的共同相處記憶。
在悲傷的路途中,我們願意陪伴自己,願意傾聽內心的聲音,願意為自己保留一只記憶的寶盒,珍藏著重要的記憶——曾深深感受到的愛與支持,陪伴與呵護。
在這漫長而反覆的體會中,有一刻你會真實的領悟到──療癒是,雖然心痛的感覺仍在,但已經可以承受那心痛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