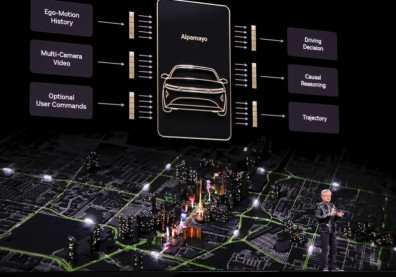2月25日對中船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一天,這是中船有史以來第一次同時交兩艘船,兩艘海上長城般的巨型貨櫃輪靜靜地停泊在高雄港邊。
不巧的是,冬日幾乎不雨的南台灣,降下了豪雨,穿著褪色制服的員工們,無視天候,在大雨中忙碌地穿梭。儘管天氣不好,可他們的心是熱的,因為過去好長一段時間,中船未曾提前交船,更未接單滿檔,這是老天的眷顧,大伙忙得起勁。
來到3月的中船基隆廠。一向陰雨綿綿的基隆,這天卻異常地出現近三十度高溫。因為3月底就要交船給陽明海運,員工趁著難得的晴天,無視周遭高溫、噪音與滾滾沙塵賣力地工作。
在中船工作已三十八年,月薪新台幣5萬4000元的內業工廠領班林守田,帶領的是基隆廠最大的一班(內業工廠),正仔細看緊最複雜的船尾加工程序。這些年天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還不支加班費,他無怨無悔,「現在景氣好,多努力點沒關係,我相信中船很快就會恢復過去的榮景,」他布滿皺紋的黝黑臉上露出希望的笑容。
成立於1976年的中船,在1990年代船運大好時,年年營收都在200億元上下。但在遭亞洲金融風暴波及後,營收慘跌四分之一,兩年前才開始緩步回升。
「中船員工比任何國營事業的員工都還苦命,」進中船二十五年,看盡興衰的中船行政室公關課課長王先至強調,「但我們卻更『韌』命。」
中船是苦孩子,不是壞孩子
中鋼與中船總公司都坐落於中鋼路上。從高雄的大動脈中山路轉進中鋼路時,「中國鋼鐵」與「中國造船」的招牌聳立路口,「倒過來看,就是『鐵鋼國中』跟『船造國中』,但兩所國中的升學率真是天壤之別,」去年7月才卸任的中船前董事長徐強苦笑著,儘管爹不疼、娘不愛,「但中船是苦孩子,不是壞孩子,希望有一天能成為爭氣的孩子,」這是他三年前從成功大學借調中船當董事長後,一直掛在嘴邊的話。
提到2001年最後一天開始執行的「再生計畫」,徐強說只能用「悲壯」兩個字形容。再生計畫開始前三年,中船累計虧損110億元,僅111億元的資本額幾乎用罄,銀行拒絕融資,員工薪資發不出來,中船差點成為第一個破產倒閉的國營事業。
因此,當時經濟部對中船下了「再生計畫」一劑猛藥,裁員47%,超過兩千三百人,而留下的人全減薪35%,創下國營事業紀錄。
是以,當時幾乎沒人看好這項計畫。有監察委員公開表示,中船一筆爛帳,早該關門,不必再生,否則只是浪費公帑;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也下達,兩年內若無大幅改善,即要勒令關廠;連中船員工本身都認為再生難如登天,甚至戲稱「再生計畫」是「往生計畫」。
儘管人事成本一舉由42%降到15%,但看不見未來的員工,人心渙散。原是一介教授的徐強,在前經濟部長林信義的請託下,接下了中船董事長這燙手山芋。堅持「要握到每一個中船員工的手,要走遍中船每一個角落」的徐強,上任第一步就是提振士氣。
上班第一天起就站在門口送員工下班,下班時會坐在喝悶酒的員工旁聽他們傾吐心事,甚至還和他們抱頭痛哭,就這樣一步步凝聚起中船員工的向心力。他更周旋在軍方與海外客戶間,為中船爭取到大批訂單,讓中船在短短一年內轉虧為盈。
「民營化是目標,企業化才是實質,」徐強拿出工業管理的看家本領,列出十六字箴言,「按圖施工,照表推程,嚴格控管,」若是做不好,那就「提頭來見」,他甚至真的送基隆廠和高雄廠的領導者一人一把寶劍,以示提升品質與掌控成本的決心。
中船因而蛻變,連陽明海運董事長盧峰海都誇說:「中船不僅能準時交船,甚至可以提前,重要的是,品質不打折扣,」陽明更因此與中船進一步洽談製造超大型貨櫃輪的可能性。
中船更幸運地碰上難得的海運景氣回升,不僅海內外訂單紛至,連日本廠商都主動接觸,現今中船的訂單已經滿載到2009年,創下歷史紀錄。中船董事李銘傳驕傲地說:「從去年接單累積的噸數來看,中船已經從世界第八重返第四,僅次韓國、日本、大陸,」這是當時差點面臨關廠命運的他所意想不到的(見頁228表一)。
中船基隆廠的大樓上,仍掛著數年前裝修的「同心協力求生存,創造新局救中船」標語。站在標語下,廠長黃宏志對外界看待中船翻身是靠海運景氣回升與拿員工開刀不以為然,強調「自助、人助(徐強)、天助(景氣)」才是中船起死回生的主因。
「現在正是民營化的好時機,」中船總經理兼代理董事長范光男表示,「等到景氣不好時就太遲了,」由於再生成功,目前美商MPH、港資中國航運和本土的長榮、陽明、萬海、中信等集團都表達了投資意願,加上國營會的支持,預計今年底將售出51%至66%的股權完成民營化。
苦幹三年,不抵一月匯損
然而,這得來不易的成功,卻面臨匯差和原物料上漲的大浪襲擊。連續三年獲利,去年更創下八年來最佳獲利紀錄的中船,因為接單時以美元計價,2005年造船平均簽約的美元匯率為新台幣34元,面臨現今升破新台幣31元壓力的中船,帳面營收將因此短少17億元,甚至有媒體大膽預測,中船將因此賠光三年來的累積盈餘。中船方面表示,外在因素難以克服,只能在成本和效率上著手,「員工苦幹三年,抵不過一個月的匯率波動,」課長王先至無奈地說。
國營事業中,中船是國際競爭壓力最大,也最受景氣影響的企業。好比過去一年間鋼價飆漲了六成,對每年需用二十萬公噸的鋼板,購料成本占總成本40%的中船來說,無異雪上加霜。更糟的是,不製造船的心臟——「主機」的中船,更面臨主機價格大幅成長30%的壓力。
「沒有製造主機的核心技術,加上沒有台機公司等周邊廠協力,中船只能淪為『配裝廠』,」觀察中船長達三十年的知情人士擔心,配裝不僅需要便宜材料,更需廉價勞力,在擁有原料與廉價勞力的大陸造船廠崛起之際,沒有核心技術的中船前景堪慮,「況且有主機製造能力的韓國,第一優先當然是支持韓國廠,中船只能任人宰割。」中船員工也語帶無奈:「現在我們甚至得先等韓國同意賣主機,才敢接單。」
困窘的是,技術斷層卻是中船的罩門。因為再生計畫不僅使許多優秀人才主動求去,在遇缺不補加上薪資低的情況下,新血更無法流入中船。「放眼望去,不是白頭就是禿頭,」徐強感歎,員工平均年齡四十七歲的中船,期待民營化能放寬用人限制,也吸引外國人才加入陣營。
然而,問題卻在台灣的造船專家後繼無人。一來因為過去設有造船系的台大、成大、海大早已紛紛縮編甚至改名;二來艱苦、骯髒、危險的工作,讓年輕人避之唯恐不及,「前一陣子來了三個海大學生,現在已走了兩個,有一個還是來一天就走掉的,」在中船有三十年資歷的機電基礎技術人員陳兩榮搖頭歎息。
政策反覆,民營關卡重重
人才短缺,與政策搖擺不定息息相關。「當初政府在草擬海洋政策綱領時,竟然忘了把造船業列入,我還寫信去抗議,」徐強點出政府長期以來漠視造船業的態度,「上帝就是把台灣放在海洋中,能不重視嗎?」
屬十大建設的中船,反映了當初的時代背景。因為對開發中國家來說,造船業不僅是吸引外匯及邁向工業化的入門產業,更能帶動無數相關產業的發展。
然而,造船就跟台灣曾稱霸全球的洋傘、玩具等勞力密集產業一樣,隨著產業轉型而式微。但造船業不像其他產業般說外移就能移,所以許多已開發國家仍保有自己的造船產業,並列為國防產業的一環,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立委蔡其昌表示,政府巨額的軍購,其中有些部分應該用在輔導本土國防工業的興起,他舉半導體設備業的處境為例,「台灣半導體大廠跟台灣半導體設備廠,最近的距離竟是美國,產品都需經美國的認可。」
然而,政府對政策的反覆,讓中船遲遲找不到定位。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陳水扁帶媒體下鄉時大聲疾呼支持「潛艦國造」,結果在美國願意出售潛艦後,陳水扁馬上改口說:「我們研發這樣的技術,是要成為亞洲或全球潛艦製造中心嗎?」當初支持中船的國防部也跟進表示:「中船只能電焊,欠缺設計品管測試,只會變成下一個漢翔(漢翔自製經國號戰機後,便面臨生產線停擺的難題)!」至今中船潛心製造的潛艇船體,仍深鎖在倉庫中,靜靜地被灰塵覆蓋著。
「政府買不到,花再多錢都會支持,買得到就不管了,」一位官員悻悻然表示,「沒有政策的支持,身為國營事業的中船哪也去不成。」
民營化,政府準備好了嗎?
民營化成了中船人盼望的曙光。歷經再生的磨難,中船工會成為少數國營事業中,對民營化反彈較少的工會。但是中船董事李銘傳卻不得不問,「中船人準備好了,但是政府準備好了嗎?」去年本來要民營的中船,卻因為民營化方案延遲通過而跳票,今年即將捲土重來。
「中船民營化太複雜了,況且中船負債比還那麼高,」一位經濟部官員直言,「要完成民營化,很難。」(見表二)對此,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吳國棟表示將先為中船減資再增資,並將明年6月民營化進程提前至今年底,「擔心民營化是當然的,但我會這樣安慰他們:國營會比你們還擔心民營化,國營事業都民營了,我們不就都失業了嗎?」他話鋒一轉,「問題是願不願意看見未來,中船愈早民營化,才能愈早有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