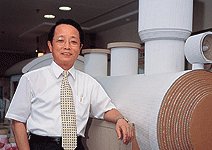在一般人印象,造紙業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夕陽產業,但事實上,台灣造紙業已成功地從節能中保持國際競爭力。與日本紙業相比,台灣造紙每單位所耗能量只有日本的77%,因此,在幾乎沒有市場保護的情況下,進口紙只能攻占台灣5%的市場。
對於正隆紙業來說,「節能」絕對不是應付主管機關的手段,更不是營造企業形象的廣告,而是關係企業生存的頭等大事。
一般製造業能源通常只占企業支出的4%到6%,但對於造紙業來說,10%的成本就砸在能源上。因此,正隆集團總經理蔡東和每三個月一定親自召開能源會議,各工廠更是每月都要開節能目標會議。如此才能將能源支出比重壓在6%到8%之間,也才能和同業競爭。
有人研究哺乳類動物體積雖然比恐龍小,卻能夠逃過大滅絕,主要原因就是哺乳類動物的食物吸收利用率比恐龍強。
規模只有造紙龍頭永豐餘80%的正隆,成立四十多年來,一直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就是因為它的超強「食物利用率」。
從節能到賣能
首先,正隆專攻工業用紙,成為台灣最大的工業用紙製造商,因為工業用紙使用成本低、原料以回收廢紙為主;相較之下,文化用紙利潤雖高,但進口紙漿供應量及價格經常隨著國際市場波動,不易掌握。
不過,工業用紙因為原料取得容易,進入門檻低,正隆要擺脫其他競爭者,自然必須在占成本第一位的原料和占成本第二位的能源上,多下功夫。
目前正隆的廢紙利用率是90%,除了回收68%的纖維外,剩下殘渣則做為鍋爐的再生燃料。2002年因此節省四千兩百八十五公秉的油料,2003年更節省了九千四百六十九公秉,節能效率增加了一倍。
在過去,正隆用的電是向台電買,乾燥紙漿的高壓蒸汽,則來自重油鍋爐,許多蒸汽因而浪費掉。
1984年時,正隆大膽引入造紙業首部汽電共生設備,後來又陸續引入多部設備,目前正隆汽電共生設備的發電量已經占到整個造紙業近三成。利用比油便宜的燃煤鍋爐,同時產生電和蒸汽,把整個能源的使用率由過去的30%左右,提升到將近70%。
由於在汽電共生方面累積了相當多的專門技術,正隆不但自用,同時也於1993年在紡織染整業聚集的桃園大園,設立專門的汽電共生廠,正式跨足能源產業。
大風吹,風車轉
2002年10月,正隆更大膽投資新台幣1億1800多萬元,於新竹竹北建造兩支一千七百五十千瓦風力發電機,主要的考量就為了節省能源支出。
竹北缺電,正隆關係企業天隆造紙廠一天需要一萬兩千千瓦的電,但是台電只能提供40%,其餘60%的用電必須靠自設的重油發電機,但是重油發電每度成本是台電電價的一‧八倍。現在兩支風力發電機每發一度電的成本只有0.77元,是重油發電的31%。一年下來,替公司節省1400多萬元的支出。
然而,兩年前當正隆決定安裝當時全亞洲最大的風力發電機時,全台只有台塑和台電有過建造風力發電機的經驗,而且機型也比較小,因此,正隆可說是一切從零開始。
首先,高六十米、葉片直徑六十六米的兩支發電機,從丹麥裝船,運到台灣,如何下船?陸運時,如何在高速公路實施交通管制?進到民房林立的巷道,如何迴轉?
天隆造紙廠總經理張清標笑說,所有運送過程都已寫成標準作業手冊,正隆將來可以靠這套知識向風力產業發展。
安裝還不算最困難的部分,張清標當時最擔心的還是附近居民的抗爭。
為此,張清標一行人還特別組團到德國和丹麥,實地考察當地是如何與民眾溝通、推動風力發電。
後來在與附近民眾溝通時,張清標就提到,根據民調,歐盟的居民80%支持發展風力發電,因為風力發電不會排放二氧化碳,噪音不會太大。
特別是德國和丹麥的「風力農場」,風力發電機通常就設在農舍旁邊,形成「立體經濟」,上面是風力發電,地面則是養牛、養羊的農場。環保意識強烈的德國和丹麥,都能將風力發電機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這些說明消除了居民的疑慮。現在豎立在竹北海邊空曠地帶的兩支風力發電機,甚至被新竹縣長鄭永金封為新竹縣的新地標;附近居民也常得意地向觀光客介紹:「我家就在兩支風車旁邊。」
除了在節能上精益求精,正隆還不忘在行銷上「榨取」能源的最後利用價值。竹北天隆紙廠生產的衛生紙取名「春風」,包裝上寫著「春風吹,動力飛。風力發電,能源無限」,把風力發電和環保產品巧妙結合起來。
根據風力發電規劃商英華威的調查,台灣每年有兩千五百到兩千六百小時風力夠強,能讓發電機滿載發電,風力資源是歐洲國家的兩倍。然而,除了正隆紙業外,尚未看到理想的商業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