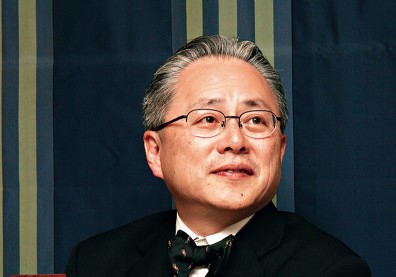「我有一個很糟糕的毛病,一講到蒙古就停不下來,」身披細格網狀流蘇披肩,戴著多圈古銀質短項鍊,一身民族風味的席慕蓉略帶歉意地笑著說。
以《七里香》等溫婉詩作享譽的席慕蓉,自1989年踏上蒙古的草原後,不但「從單純的個人走向浩大的歷史卷帙」(蔣勳語),更將創作重心對焦原鄉書寫,以一枝飽含感情的筆,與讀者分享她在蒙古觸動的強烈悲喜。
千里松漠重生
然而,第一次追尋母親魂牽夢縈的「千里松漠」(原始松林),得到的卻是令人傷心的殘酷現實:原本三百公里的森林,在未經節制的砍伐下,只剩一片淒冷荒漠。
「想不到他們連一棵樹都沒有留給我!看到當時那景象,真是傷心得不得了,」席慕蓉回憶往事仍不禁紅了眼眶。該年滿心遺憾寫下「松漠之國」一文抒懷,意外引起家鄉父老重視,開始積極植林,近年席慕蓉重遊故地,幼苗已蔚然成林。
此外,由於當地政府的覺醒,推行「封地育林」,幾處森林保育區復育成效漸顯。最令席慕蓉印象深刻的森林,是大興安嶺紅花爾基的沙地樟子松保護區,雖是人工維護的再生林,綿延一百二十公里的林帶,卻是一片欣欣向榮,滿溢生命的茁壯與喜悅。
「這個地方我已經去了三次,美得不可思議!」席慕蓉像回到森林般瞇著眼讚歎。「如果你恨誰,把他帶到那裡就對了,」看到眾人一臉疑惑,席慕蓉像頑皮的小孩般,眨了眨眼睛後大笑,「因為樹高,而且每棵樹幾乎一模一樣,沒有人帶,很容易『進去就出不來了!』」
廣闊的再生林讓席慕蓉產生另一層感悟,「原始林被砍伐殆盡時真是叫人生氣。可是後來想,這長了二十年的再生林,過幾年也就是原始林了。能有現在的規模,已經是得來不易,」情感豐富的席慕蓉再次哽咽,深吸了一口氣後有感而發,「當我進到森林會覺得很感謝,想人類做了這麼多壞事,毀了這麼多土地,但只要肯對大自然說一聲對不起,這世界還是可以恢復的。」
除了蓊鬱的森林,大片發亮的綠色草原也是席慕蓉思慕的心靈淨土。
「很奇怪,一到草原,就有一股走路的欲望,」自承在城市連走十字路口都嫌煩的席慕蓉,看到草原卻是「不走不快活」。
「我可以一直走、一直走,而且不會累,」席慕蓉興高采烈的攤開雙手,「因為感覺自由了。」
置身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人的心靈也隨之遠颺,席慕蓉認為,遊蒙古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人不再驕傲。
「站在遼闊的草原上,會深切體會人的渺小,漫步中卻能又真實感覺自己的存在,這就是蒙古,」席慕蓉感性地說,像在吟詠草原的詩歌。
好客是因為寂寞
「若你是陌生人,外灘沒有一扇門會為你打開,但是在蒙古,沒有一個蒙古包的門會對你關上,」席慕蓉曾以此做為上海與蒙古的差異註解。不過蒙古人的好客,並非送往迎來式的熱情,「我們蒙古人開始時不會跟你很親近,只會沈默的接待你,」席慕蓉不疾不徐的說,「但當他覺得與你投機,心就整個打開了。」
她回憶一次要從蒙古國前往庫蘇古泊,車程將近七小時,行前她建議蒙古朋友去雜貨店添購乾糧,朋友卻置若罔聞。
出發前席慕蓉自忖,「完蛋了,今天要餓七個鐘頭。」未料才行駛三個鐘頭,就遇到一對在草原上休憩的母子。一行人下車寒暄,不久蒙古婦人就邀席慕蓉等人「到家裡坐坐」,最後甚至下廚款待他們品嚐道地的羊肉麵。「原來7-ELEVEN在這裡!」回憶起這段難忘往事,率直的席慕蓉忍不住開懷大笑。
「我有一種感覺,蒙古人好客是因為寂寞,」席慕蓉斂容說,「草原上難得碰到人,若聊得投機真是格外快樂。」「那位太太看到我們,說不定也覺得『又有人可以來聊天了!』所以很開心,」席慕蓉俏皮的補充說明。
此外,成吉思汗立下「善待行旅」的傳統,更使蒙古人對待旅人的心意是自然孕生、不求回餽的。
席慕蓉回憶一次與朋友去蒙古騎駱駝,營區只有一對較沈默的母子,當一行人上車準備離開時,導遊解釋,此時節多數人已遷至另一營區,這位婦人由於先生住院,只能焦急地在此等待。眾人感到有些抱歉,回頭望卻看到遠方的婦人拿起一只小奶桶,用長木杓往車子離去方向撒三次牛奶。
「當時逆光,奶在光線照耀下像珍珠一般,導遊說,這代表『祝你一路順風』,」席慕蓉溫潤的聲音滿溢感動,「我們都要離去了,沒有人會下車和她道謝,但她還是對我們獻上祝福,不求回報。」
縱使大陸改革開放至今超過十年,蒙古的旅遊仍算是剛起步。「每個人到蒙古都會跟我說『沒有廁所』或是『洗澡不方便』,」談到蒙古總是眉飛色舞的席慕蓉,也不免對觀光客的要求有些無奈,「那麼大的地方,總不可能蓋個水泥廁所跟著你走吧!」
席慕蓉表示,在蒙古包或旅館無此疑慮,但深入曠野時需嘗試把心放開,在大自然解決。但如果真的很介意廁所問題,「那就去大興安嶺、呼倫貝爾,那兒有非常好的廁所,」席慕蓉啜了口茶,半開玩笑地說。
想必 在樺木與樟松的林間
還生長著我們曾經採摘過的香草與野菜
而如今在如卷渦般的白雲之上 那歌聲悠揚
是生命裡的不移不變
亙古綿延的喜悅與憂傷
如果我從千里而來 只是因為曾經擁有的許諾
今生絕不肯再錯過
席慕蓉在「紅山的許諾」一詩中,有著對原鄉的堅定誓言。她祈願以真摯的文字與影像,讓更多人樂意探訪蒼莽的塞外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