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漫漫長史,中國是如何成為現在的中國?清朝又是經過什麼樣的改革,成為現代中國?歷史留名的雍正皇帝,如何著手改革棘手的財政問題?本文摘自《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上冊)》,從他者的角度重新詮釋中國史。本書作者史景遷是一位出生於英國倫敦,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1965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
以下為摘文:
棘手的財政問題
雍正皇帝在位短短12年間殫精竭慮,欲解決當時政治的積習流弊,這些問題在今日也仍然重要,包括農村的官僚結構與財政問題,如何建立有效且可靠的訊息流通系統,以及強化朝廷中央的行政能力。而此三者實乃環環相扣,互為因果;假使能夠成功駕馭這三者,便能有效統治中國的廣土眾民。
雍正登基開始,對於如何著手進行似乎已有定見。雍正的父祖皆是沖齡即位,但他繼承大統時已是四十有五,既無監國大臣在旁橫加掣肘,又有豐富的政務經驗,親眼目睹康熙朝開始衰頹。基於本身的需要,雍正漸次擴大康熙朝初設的奏摺制度範圍,並正式確立了密摺制度。在日常庶務方面,地方一仍舊制,以奏摺上呈六部和大學士,但是各省督撫高官多以密摺遞呈雍正,報告地方的行政業務細節,也透露關於其他官員的事跡。終康熙一朝亦並未深究財政危機的弊端,雍正開始了解到府庫虧空到什麼地步,於是敦促群臣提出改革財政結構的建議,並在「戶部」之上另立一小型的財政稽核官署(譯注:「會考府」),由十三皇弟胤祥受命主掌。
財政危機千頭萬緒,即使在位者手握絕對大權,也無法靠一、兩則諭令就能解決。1723年朝廷的財政歲入約為白銀3500萬兩,其中約有600萬兩是來自各種商業稅,2900萬兩取自「地丁」稅,其中有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留歸各省地方事務之用,其餘悉數上繳中央;不過留歸地方的經費幾乎都被分配到一些全國性的計畫上,例如軍費或朝廷驛站的支出。結果僅有不到總額六分之一的稅錢是真正被地方官用在地方的政事上。或許有人會認為,只要提高「地丁」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就能紓解財政短絀的窘境;但是雍正為了克盡孝道,並未試圖變更康熙在1712年所定的稅額標準。況且,滿洲人也承襲了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輕徭薄賦才能造福天下蒼生,才是皇帝愛民的表現。改革的另一阻力來自戶部的官員,他們有自己的行政程序與執行方案,並且經常接受「冰敬炭敬」,他們當然不希望有所改變。
現行的稅制不僅固若磐石難以撼動,同時還充斥著形形色色的陋規惡習。上層階級通常就是富有的大地主,在康熙時代,富有的地主往往透過變造所有權人名、假借人頭戶、轉讓所有權、質押所有權等手段規避稅賦,所以很難稽查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況且,農村的經濟權力大都掌握在魚肉鄉民的一小撮地主手中。這些地主往往勾結省城裡的官吏,將稅賦轉嫁到貧農身上,讓貧農承擔不成比例的稅賦。面對如此惡劣的處境,農民幾乎沒有任何申訴的救濟管道,而實際上已被侵吞的錢兩則被視為是一種「拖欠」——亦即歸咎於農民拖欠,沒有按時納稅。
明查暗訪改革稅制
1725至1729年間,雍正一改康熙的寬仁作法,下定決心改革地稅,並打破處於中介之地方官僚的權力網絡。他決心擴張國家權力使之有效深入農村。誠如雍正在1725年的諭旨中所言:「以小民之膏血,為官府之補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
雍正通過地方上呈的奏摺,以及委派官吏——通常是較不可能受地方士紳影響的滿族或漢軍——分任各省巡撫、府庫要職明查暗訪,慢慢累積相關的正確資訊。之後,雍正建立一套官員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亦即「火耗」,按地丁稅的一定比例徵收,徵集而來的耗羨銀歸入省的藩庫,所有其他濫徵的規費和餽贈皆被視同非法。一省藩庫所徵集的稅銀依固定比例在省內重新分配。一部分用於提高地方官員的薪俸,稱之為「養廉銀」,部分稅銀則撥給州縣政府,用來興建灌溉溝渠、造橋鋪路、創辦學校,或者提列為不在戶部預算範圍之內的其他值得或必要的地方建設經費,包括補助在天災中損失的牲畜,改善獄政,製作政府公報,修繕下水道、公共墓地、闈場,以及購置寺廟的香燭。
譯注:根據清史學者孟森的注解,所謂「火耗」,指謂本色折銀,畸零散碎,經火鎔銷成錠,不無折耗,故取於正額之外,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每兩數錢,輕者錢餘。詳見王元化主編,《孟森學術論著:清史講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二○六。
若是仔細考察這些改革的成效,我們就能概略窺見當時中國各地區的差異不小。雍正的稅制改革,在北方省分如山西、河南、河北成效最為卓著。這些地區的農民多為獨立的自耕農,土地的登記較為容易,地方官的作為亦受到較嚴密的監視,而迫使他們必須改變陋習。除了居間勾結不法的地主與部分貪贓受賄的胥吏之外,每一個人都是改革的受惠者。比起過去盛行的橫徵暴斂歪風,現在以地稅為基準課徵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耗羨銀,對農民、甚至大地主而言,稅賦負擔也沒那麼沉重。此外,新制的實施也使官吏的固定收入比過去提高許多:以知縣為例,此時每年的薪俸為六百兩至一千兩不等,而不同於改革之前的每年四十五兩。所以,官吏更能安心推動政事,政務的運作更為流暢,地方官有了真正的自主權得以處理特定的計畫。
在南方、西南地區,改革就沒那麼順利。這些地區的基本稅額相當低,因為有許多新的移民,且人口稀疏;但官僚的員額卻居高不下,所以無法與同級的北方官吏享有相等的薪俸待遇。新稅制若要運行,就必須授權給地方官員向開墾礦產與控制鹽務的行商課稅,或在中國各地的通道、運河、河流設置關卡徵收過境稅。不過即使朝廷授予地方徵收這些稅目的權利,但因路途遙遠、所費不貲,許多地方官員也未能將耗羨轉交給省裡監管財政的衙署,反而懇請上司允許他們,在繳回剩餘的耗羨稅銀之前,先把他們根據薪俸新制應得的薪水與地方開銷所需經費從稅銀中扣除。可以預見,這會導致先前那種朋比分肥的陋習死灰復燃,妨礙有司依各地的真正需求全面而公平地分配稅銀。
在中部長江流域的省分,特別是江蘇、安徽、浙江與江西這幾省,新制實施寸步難行。在這些地區,住著許多已經告老還鄉但仍握有權勢的官員及其親族,這些人持有的土地根本就沒有確實登載,還仗著京城的人脈來恫嚇地方官吏。之前康熙對這些地方的縉紳特別寬容,以致到了雍正朝中央要加強控制,他們並不會逆來順受。由於阻力是如此之大,雍正不得不特別指派一名滿族要員,率領70名經驗豐富的稽核官吏,全面清查這些省分府庫裡的錢糧,確實丈量田地。
清查後發覺瀆職的情形遠遠超出想像,錯誤登載或重複登錄的案件極為複雜,恐怕永無釐清的一日。稽核官員發現某些案件,地主將土地登記在數百個人頭下,以為地方官吏不會細細追查每一位小地主所拖欠的丁點稅錢。假若稽查官員要赴現場查驗,地主就藉故拖延,百般刁難,或封路,或斷橋,甚至掀起騷動,以暴力橫加阻攔。在押待訊的人,也會被人所救。從稽核官員沒收的帳冊可看到,豪門富室得地方財政官員之助,幾乎不繳一文稅金。即使證據鑿鑿,稽核官員也難以讓這些貪官巨富被定罪,至於要收回千萬兩稅錢,更是難上加難。
這股抗拒改革的阻力正說明了稅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改革者認為,隨著稅制改革的持續推展,廉潔官員的戮力勉行,以及雍正的激勵支持,大清中央官僚體系的效能可臻至新的境界,便能在1644至1683年所奠下的統一宏圖和之後外交政策的成功上,建構一個真正長治久安、永續運行的政府體制。假若朝廷能控制、經營最繁華省分的資源,必能造福黎民,強固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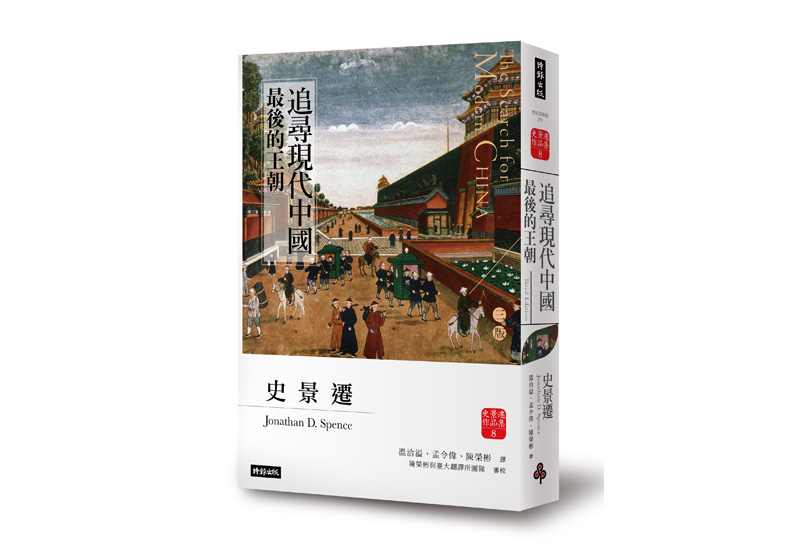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一書,史景遷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時報出版。
本文節錄自:《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一書,史景遷著,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