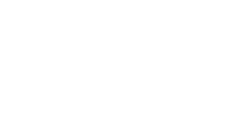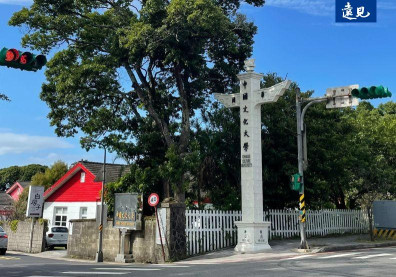想要活得清醒與明白,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因為面對生命中種種幽微的煩惱與困境,真實的人性更傾向於逃避與掩蓋。
在這個世界上,或許每個人都在逃,也許是逃避工作帶來的無力、逃避自己在感情中的卑微,也或許是在逃避自己真正想成為的樣貌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差別只在於,你知不知道自己正在逃?
有兩個人,他們都曾被台灣電影大師楊德昌點燃對電影創作的熱情。一個是電影導演王維明;一個是導演、演員戴立忍,那種熱情轉變到現在,變成是一種「志氣」,讓他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會有一種態度跟觀點,即使有很多受傷和不堪,一輩子都不會改變。
真實世界是衝突的,王維明曾經因親炙大師,參與製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一一》等重要作品,但也因與楊德昌之間的信任出現問題,讓他離開電影圈,甚至2 年沒有工作,產生自我懷疑。
現實世界的戴立忍,高中畢業在金門當兵,失去了當時的女友,也一度沉浸在絕望與傷痛中,痛得想逃。
但是,數10年後,兩個男人,不再逃了! 他們勇敢透過電影鏡頭,直視人生的真相,用剝洋葱般的手法理解每個狀態中的真實困境,如何還能活得清醒與明白。
王維明說,直視真實會帶來悔恨與痛苦,但是卻也能帶來重生的契機。從電影轉戰廣告的王維明成績斐然,但是隨著年齡增長,王維明開始意識到,其實他始終沒有好好面對過去那個一度失去自信的自己,在他內心深處,一直渴望透過作品關注社會,更加真實呈現自己的生命觀與探索過程。
而戴立忍被公認為是當今台灣最有魅力的男演員,即使是飾演反派,也能散發出令人又愛又恨的人格魅力,那種魅力來自於對複雜人性的深層理解,即使是最黑暗的角色,他也能展現出一絲令人動容的人性。
這種對生命的寬容與理解,是戴立忍這10 幾年的時間給自己的功課。即使身在深不見底的痛苦中,戴立忍卻始終用勇敢得近乎殘忍的方式直視傷口,他在《白色巨塔》裡飾演的邱慶成說:「我們必須學習跟自己最不堪的部分相處。」而這句台詞是戴立忍寫的。
王維明與戴立忍這對北藝大戲劇系的直屬學長弟,兩人不謀而合的價值觀就是不輕易服從權威,追求公平與正義。
王維明曾經在北藝大畢業時背對著鏡頭拍照,只為了抗議校園空間的權威性;而戴立忍的第一部作品《年少輕狂》則是他為了抗議學校不讓學生使用大劇場的副產品。他們心中都有自己的公平與真理,信仰電影應該關注真實的社會。由王維明執導、戴立忍參與演出的作品《寒蟬效應》,毫不避諱地探討了校園性侵與美麗灣抗爭等充滿爭議與風險的議題。
但是走過年少輕狂的歲月,曾經滿懷憤怒與衝動的兩人,開始學會真實並不像黑白一樣分明絕對,情欲與權力、環保與正義,身處在纏繞糾結的情境中,最終,兩個人試圖用電影帶領大家回頭去面對自己的心,誠實的做出回應。
學習與自己的不堪相處
「面對自己」說來簡單,卻是每個人窮盡一生都很難達到的目標。面對生命的困難,我們常常在當下選擇逃避或掩蓋,但是卻在日後某個瞬間被迫面對。學習與自己生命中最不堪的部分相處,才能獲得真正的平靜與快樂。
王維明(以下簡稱「王」):談到人性的探索,可以講得很形而上,但有時候是非常現實感的,其實就是我們碰到問題的時候怎麼面對自己?有些時候你會覺得好像是選擇,但是到了某一個年齡以後,你會發現那不是選擇的問題,其實是關於過去你面對很多困境沒有在當時好好思考,它回過頭來變成人性裡非常多的面向。在電影裡,每個角色都有一個面對跟轉折,都是從前的掩蓋、逃避,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在當下去理解過去逃避的自我。
其實每個人都在逃,只是你自己知不知道而已,有時候是掩蓋逃避,真相很痛,有些時候很殘酷,但是當你接受,才有機會在你的生命產生一些效果。你要往下還是往上?你要快樂還是悲傷?不會有人希望每天要恨、要邪惡、要黑暗,這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相處的時候非常重要的過程。
戴立忍(以下簡稱「戴」):我飾演的李教授是一個像我這個年紀的野百合世代核心分子,他曾經享受過群眾給他的注目跟焦點,可惜後來賈靜雯飾演的太太希望他能夠離開台北這個圈子,李教授當時同意了這件事情,但顯然他是有遺憾的。他順從了家庭要求,大概只有站在指揮台上的某一個小片刻,他才能夠享受到當初被眾人注視的狀態。他到中年了,其實他有一個遺憾,那個遺憾就是過去延伸下來沒有被解決、沒有好好真實坦誠面對,現在他用了一種傷害別人的方式,來填補那個部分。可是,另一方面,對李教授來講,他覺得正因為自己曾經失落過,所以在面對另一個年輕生命的時候,他說服自己,他認為自己是要幫助她。
面對外界,你可以有一個互動或是逃避的方式,可是我認為人應該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逃,你要學會跟自己的不堪相處。我們都有過不堪,不管別人知不知道,你自己要知道,留下來的不堪就是你在未來必須不斷面對的,如果沒有辦法彌平,你不能讓它影響你,必須要找到跟它和平相處的方式。
王: 我父親前年胃癌,整個人從樂觀變得極度沮喪,我跟他講:「爸,你人生不管後面能走多久,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可能改變胃癌的事實,它就是你的命跟身體,你要跟它相處。」因為我愛我的父親,所以我跟他說了這些話,但是回過頭來審視自己人生的困境,我有沒有這樣跟它相處?我做廣告這10年其實是逃離電影圈,當時我和楊德昌因為信任問題分開了,離開後有2年沒有工作,非常混亂與自我懷疑,還曾經想過去花蓮和朋友一起做泡水車,後來很幸運地接觸到廣告,也做得很好,讓我的自信慢慢的增長,另外一個想拍電影的心就出來了。決定要拍片時,大家都說「你不要再走回頭路,又去弄新電影!」但是我現在做出來了,大家也很替我開心。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面對由錢與權交織而成的巨大高牆,我們不應該放棄對公理與正義的追求,但是也不應該忘記,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試著去關注並理解,形成自己的觀點。
王:我們對不公不義的事情特別無法忍受,只是過去年輕的時候,你的勇氣可能是用錯的方式發揮,現在的人生學習會是用溫和的態度去表達很強烈的立場,但如果這種溫和被別人當成是狗屎的話,你就可以用更強烈的東西。
戴導是我的直屬學弟,他進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就很酷,年輕時喜歡跟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我的畢業照是在圖書館拍照,可是圖書館其實是在學校裡最遠的地方,每一個人都要向上爬,爬到最遠最累的狀態才能到,我很氣那種感覺,所以大家在拍照時,我就穿著學士服轉過身去,不管攝影師怎麼說都不理,校長就坐在前面。我對學校的建築動線設計有很多不滿,還在一堂通識課做過一個報告,從學校建築的採光、動線設計找了100個問題。
戴:台灣電影從新電影以來開始把關注的視角移到現實社會當中,我上過楊德昌導演的課,他上課時會找一件目前發生的時事來聊天,如果他現在還在的話,應該會講食安的油(笑)。他會去問每一個人的看法,最後他也會講自己的意見,後來我發現,他其實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在培養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你除了去聽別人的想法,更必須找到自己切入的角度,而且是對於當下的這個社會,他影響我關注現實社會,然後去蒐集資料,產生自己的觀點。
作為一個電影人,我們也可以選擇另外一種方向去服務電影,比如娛樂的面向,但是如果新電影以來關注社會的面向,在這現在這個多元化的電影時空中缺席,那不是很可惜嗎?這種很直接的社會關照跟社會對話,我覺得還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尤其事關公共利益的事情,還是要誠實,該怎麼拍就怎麼拍,沒有什麼好躲避,我相信如果是以溝通或分享為前提,即便在無可抗拒的情況下,也會找到一個出口。
王:電影不會立刻對社會或人生造成改變,它比較像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將創作者探索的過程一一的呈現出來,它能夠啟發、影響或是帶來更多關注。觀點需要探索,有探索才會有改變的力量。
前陣子詹宏志大哥寫到他在《牯嶺街殺人事件》背後做策畫行銷,版權資金問題翻來覆去,絕望又重生的過程,但是當他看完4小時的版本,他突然說不出話來,他意識到他在面對一個天才型的導演。
但是我們小時候跟著楊導時,並沒有像詹大哥那種分析的能力,我們沒有自覺自己正在面對一位大師。跟著楊導時,今天我們跟他講一個想法,他覺得完全不對;但有時候你忽然講了一個東西,他又覺得你好棒,他點燃我們做電影的熱情,那個熱情轉變到現在變成是一種「志氣」,讓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會有一個態度跟觀點,這是這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
在我們的社會裡,大家都太需要立刻得到答案,否則你就會失去很多舞台,所以你會看到藍綠的鬥爭,或是像美麗灣事件。我希望透過創作,找到一個方式去讓事情更好,讓大家在面對一個你無法直接對抗的巨大結構時,除了抗議,也能夠找到一個討論空間,讓大家願意把自己的觀點放進來,用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面對,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