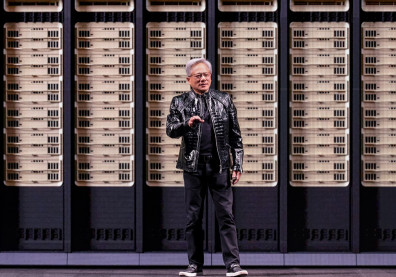何學用,38歲,我們都叫他小何,他出場時正是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家裏水管漏水、電路不靈,一塌糊塗。以前我們做家庭裝修的工頭老馬就介紹小何來打救。
荒年餓不死手藝人?
擅長水電的包工頭小何,是一位從農村來到城市務工的「農民工」。他長著南方人的矮小個頭,兩頰緋紅、眼睛亮亮,笑容羞澀,看上去好像還沒長大, 原來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我們要他開出工錢,他一直說:「是朋友介紹的關係, 不好說。」經過再三催促, 他想了又想才吐出「200」。令我們好生感歎,同樣的工作在海外不乘以20才怪。
後來又有幾次這裏壞那裏壞找他來修,他竟然死也不收工錢,說是朋友。其實他的光景並不好,找工難、討錢難一直困擾著他,有時給孩子交學費都有困難,但他從來都不向我們開口。我知道他是珍惜和我們的關係,在他眼裏我們是外國來的高級人,懂得他無法進入的電腦和英語。
從小何身上我看到生活在大陸底層的農民工驚人的吃苦耐勞, 尚且保存仁義道德的傳統品格,他們的生存環境有多惡劣,我們都不大忍心去問和看, 但是在他們卻已經習慣了。從小何們身上我看到「一無所有帶來的自由」,這是在資產鉸鏈上身不由己的人們的羡慕,而擁有夠用的物質又不被物質羈絆, 應該就是幸福了。我是從小何體會到我的幸福的。
小何是蘇北寶應縣附近農村人,文化程度初中畢業,當過一年鄉村教師, 算是一位眼界比較開闊的「秀才」。然而農村人的觀念是「荒年餓不死手藝人」,所以小何的爸爸執意要獨子學手藝, 托了關係把他送到揚州建築站學瓦工。「在中國找事做關係第一,不管什麼事先靠關係,然後努力幹!」小何總結道。
掙飯吃,農村成寡婦村
在建築站,小何看上技術含量更高的鋼筋工,卻又被他爸爸阻止,理由是「農村誰去用鋼筋造高樓?」後來他爸爸出於養兒防老的心理不讓兒子農轉非(就是改變農村戶籍),要他回鄉,「孝」字當頭的小何果然就回鄉學木工,木工工種牽涉到水電,他不想老是去麻煩水電工,就自學了《正常用電手冊》,然後學而用之,1995年,小何開始外出務工。
「蘇北經濟不如蘇南發達,我們那裏都是老鄉介紹,出去工作。」小何說。農民工自己有外出打工關係網,同鄉之間有照應,幾個常年合作的老鄉租住在附近,有活叫上。現在他的家鄉90%以上男人都出去了,農村成了「寡婦村」。
寶應除了出裝修工,還有澡堂裏的搓背工,搓背有祖傳的技術賺錢更多, 可是小何讀了點書比較清高,不想低三下四,加上受到他的師父也是一位兼職陰陽先生的影響,很講求思想品德、三綱五常、倫理道德這些。
從大陸百姓對各行各業的投訴來看,裝修業的投訴一直名列前茅,據青島市室內裝飾投訴站的資料,消費者投訴的物件主要是無牌經營的裝修游擊隊,也叫馬路游擊隊。「我就是馬路游擊隊!」小何說。提起馬路游擊隊,人們立刻想到的是一些人站在路邊或立交橋下,面前立一塊紙牌上寫「裝修」「包工」等,這個現象現在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是經過改頭換面的「轉正」游擊隊,也就是掛靠在一些有牌照的裝修公司門下;也有的用偽造的牌照開店接單,用低價吸引顧客,收了工程款後就人間蒸發。
無牌農工打馬路游擊戰
按規定,馬路游擊隊是不能承攬裝修的。大陸《住宅室內裝飾裝修管理法》規定業主如果將工程交給沒有資質的公司,如馬路游擊隊,將「被責令改正,並處以罰款」,但這條法規基本上是一紙空文,馬路游擊隊只要交保證金給物業部門,就可以與正規家裝公司同台競爭,在很多小區只要業主讓馬路游擊隊來他家裝修,小區物業部門收了押金,也會放行。至於大多數大陸消費者,貸款購房,資金緊張,在裝修上通常精打細算,能省則省,所以找收費便宜的馬路游擊隊還是大陸的國情。
「馬路游擊隊也有好處的!」小何說,他們的報價能比裝修公司少三成。其實很多裝修公司也是在馬路上找工人,一樣是馬路游擊隊,內行的客戶當然願意找同樣做工,但價錢便宜的。有裝修行業中人聽了小何的報價結構,就立刻把自己家的裝修交給他。
像小何這樣的農民工都是隨工作走的。小何最初跟老鄉到甘肅,後來到上海、無錫、常州、西安、蘭州、天水,2000年來到青島後喜歡上這裏的環境,不想走了,可是打工者能買上房子的沒有千分之一乃至萬分之一,青島一個房子要40~50萬,據《羊城晚報》報導,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整整十年中,大陸東南西北中的農民工工資都是原地踏步,小何這樣的包工頭也只能租住每月150元人民幣租金的拆遷房,自己弄一張床對付著睡覺,談不上淋浴設備,沒有供暖,冬天臉頰總是凍得紅紅。
掛面子,包工頭薪更低
小何年收入7000~8000元,不及普通裝修工可年入上萬,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在海外,包工頭是吃提成,賺大錢的。
一般的情況下,包工頭的工作是和客戶談單子,然後安排工人,小何也一樣。不同的是小何的工資只比工人高一點,而且小何自己也幹活。談單子壓價在大陸司空見慣,因為要保障工人每天50元的工資,小何就只有削薄自己的收入份額。做包工頭如此委屈,為什麼還要做? 小何說有兩層原因,一層是不得不生活,另一層是包工頭的虛榮:做包工頭有機會和客戶打交道,有一點經理人的意味。
小何就是一個特別在意心理滿足的包工頭, 待客戶很君子,倒像古代的俠客,可惜生在這個不合宜、誠信淪落的時代,老實人總是吃虧,我常常憐惜他,但是我知道他不要錢的心理因素,就遂了他,儘量採用朋友方式回報他。
如果工作地點偏遠,小何與他的游擊隊就會吃住在裝修的房子裏,工餘時間他們選擇很廉價的樂子,比如在夜市打一元一局的檯球,點一元一曲的卡拉OK來唱,錄影廳看通宵也才花四元,逛商店和書店都只看不買,或者到廣場看人家跳交際舞。上電影院、旅遊對農民工來說是高消費,不少農民工表示,他們在青島唯一的旅遊活動是「看海」。
根據《青島早報》的調查,民工最經常以看報紙、看電視打發時間,八成以上農民有讀報習慣,小何則有看報不買的習性,當然就不受經營者的歡迎啦!他們的月娛樂消費不足50元,大部分民工300元就夠開銷一個月。農民工捨得花錢的專案是買彩票,他們上話吧打電話都是用秒計算的,一看這一分鐘快過去了,就趕緊掛了,電話記錄上很多都是50多秒。
農民工是1000億債權人
一些農民工有自卑心理,坐公交車和逛街都很害怕,怕被人瞧不起。心理問題導致自殺、酗酒、打架等社會問題,但農民工去看心理醫生的絕少。
目前大陸的現狀都是包工頭拿到錢才開給工人工資,如果拿不到,工人也沒有,造成農民工工資被拖欠,這在今年隨著農民工採取極端手段討錢而成為社會問題。溫家寶總理前段時間去三峽考察民情時,幫一位農婦追討欠款,令這問題家喻戶曉。
據統計,大陸七成農民工遭遇拖欠工資,2003年大陸拖欠農民工工資達1000億,有的企業拖欠民工工資長達十年。然而小何不是這個做法,他拿到錢先給工人開工資,然後付自己,當客戶拖欠工資時,小何只好墊付,倘若討不回來,他自己就要貼錢,有一年他賠了上萬元血汗積蓄。
欠錢不還,為什麼不去告?所有農民工都會說「媽呀,打官司的成本多高啊? 我不就是沒有吃飯的錢了麼!」何況小何這樣不具備開公司資格的「裝修游擊隊」,哪來能力簽合同。在小何的經驗裏, 如果是自己找的客戶或是客戶介紹來的客戶,關係簡單直接,一般上錢都好拿。通過介紹人接單就不同,介紹人會先扣掉10%佣金,還要扣起3%~4%供日後維修,單子利潤已經像薄胎瓷那樣了,拿錢也要通過中間人,推、欠、賴的機會很大。小何和他的老鄉每年總要被扣押1~2萬,要錢要得急了,客戶就對裝修雞蛋裏挑骨頭,沒辦法,只有一點一點地討。小何幾年來做包工頭,都沒有存下錢。
人離鄉賤?悶虧全收!
出門在外還怕生病花錢,小病忍忍,捱幾天還不行就上藥店買點藥吃,不到緊急時刻不上醫院。2002年小何生過一場急病,忽然肚子痛得不行,到就近醫院住院,三天吊瓶花了醫藥費1300元,心疼欲絕,也沒檢查出是什麼毛病,押金快花光了,醫院就攆他出去。
小何一查藥單,發現上面莫名其妙有「吸氧專案」,和醫院鬧翻了,「醫院最黑了!」他恨恨地說。被坑了也沒有去爭取,一來花不起時間,他得立馬工作賺錢補償生病的損失;二來怕招惹麻煩,「我們農民工沒有地位,這個社會裏是不可能遵循法律的,再說人離鄉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想總有一天會報應在你頭上。」
遭遇了種種事情後,小何坦言自己對城市已經失去了興趣,青島還算好的,西北的地方可就出暴民,動不動拔出拳頭,事後找關係請你吃飯說聲對不起就算完。農民工沒有社會力量, 在外頭遇事都只能私人解決,被打傷了也不會去訴諸法律。不過這兩年環境好多了,以前農民工沒有暫住證還會被遣送回鄉,過程中有很多黑暗,現在遣送制度已經取消,理論上城鄉已經平等,農民工心情好多了。
只是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比如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上學, 儘管中央下達文件要求學校一視同仁,取消借讀費,實際上城市裏的學校以學額等種種理由還是沒對農民工子女開放。小何的兒女也只能在假期和母親來青島同住一陣。
小何太太是位手腳極為勤快的農婦,本想留在青島應徵做家政,掙一份錢補貼家用,但大男子主義的小何就是不批准媳婦到別人家裏當鐘點女工。我去幫小何太太說,也說不通。
農村流行讀書無用論
小何到城市打工前後已經15年,最羡慕城市工作者的是他們有養老保險,農村人只得養兒防老,要不然農村幹什麼非要生男孩。如今農民工地位提高了,找到固定工作也能參加保險, 這對小何的吸引力不小,他開始考慮脫離游擊隊,找一份可以領薪水的工作。
雖然如此,小何還是「真指望兒子養我老」,這也是農村的規矩。當然小何對兒子的前途還是很關心的, 他打算供兒子上學「到兒子能上的地步」, 實在考不上大學也要給他解決工作。和自己的父親一樣,小何也傾向讓兒子學手藝, 近年農村子弟流行讀技校,做灰領。「大學太難考,考上也太貴(目前在北京,一個大學生至少需要2萬5000元人民幣才能完成4年大學教育,而中國農民去年的人均收入只有2622元),我們農村流行讀書無用論,說中國這麼多的人口,只有一個國家主席,一個省長,機率這麼低,就是上了大學,也很難有這種機遇;不如去經商或做手藝,好過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沒飯吃。」
中國社科院李春玲博士最近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資料也顯示,中國十大階層之中領導幹部是最高階層,農民是第九階層,僅略勝於城鄉的失業者,只有0.2%農民成為幹部,也只有0.5%、0.8%和0.9%的農民轉變成為經理、私營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更多的農民只能轉變成為工人、店員和個體商業戶。
小何希望13歲的女兒將來能去讀外語,當翻譯,他拿60元錢支援女兒學電腦,可是卻不願意參加一年只交5元的醫保。
最後退路:自產自吃
其實農民工比城市下崗工人多了一條退路,就是農村。農民工在城市過不下去, 還可以回鄉休養生息――農村生活不需要花什麼錢,吃的是自己地裏的出產,住的是自家的瓦房, 有一種安全感。農民工外出務工也不一定為了發財,寶應有「在哪賺錢在哪遛」的俗語,說的是外出圖的是「掙個活錢」,生活方便,來來去去,又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相形之下,城市下崗工人就沒有這個自給自足的條件,所以城市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羡慕農民工的。
像小何,還能優游於農民和包工頭之間,兩不耽誤,若是包工頭的工作太忙,他就會去聘請種田「鐘點工」來搞定他家的責任田。畢竟農田是農民的根據地,近年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和國家鼓勵種田政策的出臺,大陸農民從田野中又看到了希望,而且今年大米的收購價由以往的每斤6角起到1.05元。6月份小何回家收割麥子,住了一個多月。「遠離了城市的喧囂,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有空聽聽音樂,感覺真舒服,心裏說還是農村好啊!」
大馬路通過家門口,道路交通越來越方便,也許不久以後當農民會成為時髦, 城市裏的人在鄉下買個房子,開車上班,吃自己種的有機蔬菜……田園牧歌雖好,只是短暫,小何還得出來賺錢。下一步他打算投奔另一位做了老闆的老鄉,到江陰碼頭做「物流」,也就是碼頭裝卸工作,去當一個領工資的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