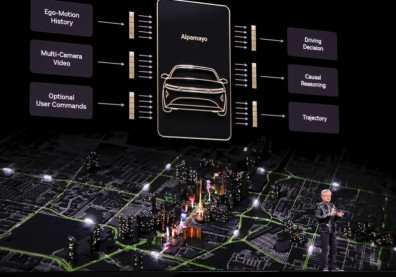2003年9月到2006年8月,在高鐵工程爭議最風風雨雨的三年間,殷琪十一度前往法鼓山向聖嚴法師請益;一路尋師訪道走來,讓我們窺見了另一個不一樣的殷琪。
殷琪:「企業界目前所形成的價值觀,讓我感到不安。」
殷琪:在台灣社會中,可能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很大影響。一般人對企業的認定,只在利潤追求。股東投資,企業的第一要務就是讓股東得到金錢回收,而且是立即利益,於是形成了社會的普遍價值觀。
曾經,浩然基金會舉辦研究所及大學生的活動,那次之後,我就不太想再辦了。因為在我跟學生接觸的過程中,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讓我感覺到,企業界所形成的價值觀,不能給人一種安定及真實性。比如有人說:「很崇拜企業界的某某人,因為他很成功!」我覺得人對追求成功已有定見,這無所謂對錯,但成功不是真正的靠山,並非如宗教是人的心靈靠山。
企業對社會的責任過去較單純,取之社會就回饋社會。現在我覺得企業界更有另一層責任,因為它已能形成社會的價值觀。但企業界目前所形成的價值觀,我感到不安,那麼在這個時刻,我們能做什麼?
聖嚴:從兩個方面思考,心就會安。
第一,先思考自己現處於什麼環境、站在什麼立場、做些什麼事情,不論是為了某一族群的利益、為了全人類福祉、為了全球化,自己若在當下的立足點上,朝向大目標而運行,就不會失去中心立場及大方向。妳現在是高鐵董事長,要為股東設想,要為台灣的交通建設設想,要為整體大環境設想,盡力於此,就可安心。
其次,社會功能分成三大區塊:一是政府,功能在於國家整體的決策面;二是企業,功能在於創造利益而不只自求;三是非營利事業組織,如法鼓山是其一,為了社會大眾的公共福祉而服務。每一區塊,有不同的性質分布和任務,但同樣朝向人類利益而努力。如此,就不會有煩惱。我有功能,妳也有功能,但都不在私人面,妳的公司是公眾的,妳的個人也是公眾的,我也是一樣。目標清楚,穩紮穩打,就能心胸開闊、具足前瞻性。
聖嚴:你在藏傳佛教裡,是不是有定期的修行?
殷琪:我的上師梭巴仁波切對出家弟子非常嚴格,很重視每天的功課,每一年也都會有修行的要求。但對在家弟子,他比較寬容,不過,每天也有一些功課,他覺得那是即使在車上都可以做。
他對所謂的「灌頂」,比較嚴格以待,弟子要接受灌頂,他通常要求有所承諾,第一,要守戒律;第二,進行一些閉關。上師讓我做的功課,基本上都偏向觀音法門。
我第一次的閉關,是在美國加州山裡的一個閉關中心,那是一個最基本的皈依關,共五天四夜,同行的還有另一名朋友。每天清晨天未亮,我們就要起身到一座小木屋,裡面只有一尊觀音,有一名比丘尼帶領我們。一天當中,上午有兩個段落的修行,下午、晚上各一個,而幾乎一半的時間都是大禮拜,過午不食。當時正值寒冬,晚上冷得不得了。
那次閉關並沒有上師開示法義,我自己覺得有所體驗,雖說不出具體的獲得,但就是感受不一樣。腰痠背痛的辛苦我不介意,每天做著同樣的事,什麼都不想,感覺在對治心境上產生了體驗。
殷琪:「我發現50歲上下的人,很多現在都在尋找自我。」
殷琪:我發現50歲上下的人,很多都在尋找自我。有一位朋友為人非常好,但向來對宗教不甚了解;前陣子他有機緣到一個寺廟去聽經。其他一些朋友,大概也在這個年紀,開始會有一些不同的體會。這滿有意思,不知是緣分到了,或是人在碰到生、老、病、死等無奈、又無法控制的情況時,比較會做深沉的思索?
聖嚴:生命的過程到了某一階段,會有不同的摸索和探求。年輕時,覺得自己不需宗教也可以過得很好,在西方社會,雖對宗教有不少爭議,但至少不反對宗教。然而在漢文化裡,宋明理學的讀書人比較不信仰宗教,比如現在,研究宗教、撰寫宗教、教授宗教、談論宗教的人,不一定皈依宗教。
殷琪:我們在考慮要建一個閉關中心。
聖嚴:閉關中心是一個精神中心,它需要有帶領的老師,沒有老師負起專責,閉關中心沒有領導中心,就沒有精神寄託。如果是讓修行者自己在那邊閉關,也很好,但不是最好。
殷琪:我們想的是,讓比較有修行基礎的人來。
聖嚴:在台灣已有很多佛教道場這樣做,南投埔里、台東、花蓮都有。閉關者需求的物質條件相當清簡,可能在山裡住上幾年也不下山,問題在於有沒有意義?過著隱士的生活,對他們自己當然是好,但對社會究竟有多大的用處?要考慮這個問題。
閉關可以採取階段性計畫,閉關一到三個月,或者半年,最多三年,就必須出關回到社會,如此對人群才有影響力。現今能夠住上三年的人,不簡單。有能力的大忙人,大概也沒有時間住上三年;至於懶人修行是修不成的。忙人修行比較容易得力,懶人修行只是浪費生命,即使在山裡閉關,也是閒著無作為。
內心的煩惱重,一入社會煩惱都來了。我們要練的禪修工夫,是進入社會不受煩惱所染,身心不受障礙所擾,這可以練成,但要有人指導,如果妳那想建閉關中心,未嘗不可,不過需找真正的禪修老師來指導。
殷琪:「最近我去印度聆聽達賴喇嘛的法會,體會到我們想太多、不知足。」
殷琪:最近我去了一次印度,聆聽達賴喇嘛的十輪金剛法會,有些寶貴的體驗。同時,有機會去經歷缺乏已然習慣的物質生活,這種經驗在修行上是有幫助的。相對而言,台灣環境好,我們對生活的方便習以為常,一按開關就有電,一開龍頭就有水,要是燈泡壞了、水小了,就起煩惱了。師父常說,不必想太多,好好修行就對,此行我的體會是,我們想的太多,擁有的卻不知珍惜,若能真正過些生活不便的日子,反而對於靈性修持有所助益。
聖嚴:富貴學道難,在物質生活富裕之下,煩惱多些,因為欲望永遠無法滿足。然而當物質生活貧乏,誘惑減少了,連希求方便的念頭也不易產生。如果富貴中人能覺知煩惱、感悟欲望讓自己痛苦,這是一種反省的智慧,由此能帶動學道的願心,追求解脫。
釋迦牟尼佛本是一國王子,足可盡享物質榮華,但由於他的反省,而求道成佛。佛陀的在家弟子中,頗有一些富甲天下的人,他們之所以追尋修行方法和觀念,是因為發現,當物質條件缺乏時生活不便,但物質條件具備時又永不滿足,那怎麼辦?唯有從內心調伏。
釋迦牟尼佛時代,有許多修苦行的人,他們覺得快樂。為什麼日子過得富貴卻不快樂,自討苦吃反而快樂?因為存乎道心。在台灣,生活環境容易形成干擾,物質條件是一種不得不要的束縛,所以,偶爾過一段修行生活,可以體驗從物質環境中解脫的自在。
殷琪:師父的意思是,在富貴中修行還是有其力量,只要自己具足反省的能力,每天都有修行功課。
聖嚴:修行功課一如晨起盥洗、飯後潄口、睡前沐浴等生活習慣,幫助我們身心安然。在家人公私兩忙,貴在時間安排,寺院裡同樣諸事繁多,但仍需修行打坐、早晚定課。
殷琪:「有一種苦,我非但無法處理,又經常製造更多的苦。」
殷琪:我第一次向師父請法時,曾經請教過佛教最核心的思想,師父提及「苦集滅道」。我覺得佛法的微妙,在於令人經常覺得有如剝香蕉樹皮般,一層更深一層。從過去以來,我始終覺得自己懂得什麼是苦,比如看到親人的生病、往生,人生中的無常、不確定感,因無知而產生的貪念、執著等,這樣的苦似乎容易理解。但還有另一種苦是,非但無法處理,我們又經常製造更多的苦,似乎完全無法控制。這兩種苦,是不是有不同的層面?
聖嚴:一是苦的現象,另一是苦的原因。我們凡夫通常只知道苦的現象,能夠體驗以及觀察;但對苦的原因,往往不去追究,也無法了解,因此叫做迷,叫做愚痴。明明知道在生命的過程中常常有苦有難,諸如親人老病、逝去,或者自己的財產、名譽、感情產生衝突與消長狀況時,就會覺得很苦。然而,人們往往不願面對或承受不了苦的事實,因而心理產生抗拒、怨恨、不平衡,當希求克服的心態出現時,就苦上加苦了。就在苦上加苦時,經常毫不自知、無法控制,因此叫做愚痴。知道苦的事實,但無法覺察苦的原因,又製造了加倍的苦因,那就苦不堪言,苦海無邊了。
如果能夠覺察這都是來自自己的愚痴,那就悟了,不會再被苦的事實所困擾,而從苦中得解脫。苦的事實同樣還在,親人的病、傷、亡,面對這種事實,要處理但不需要痛苦,那麼苦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