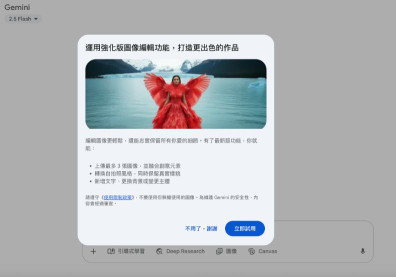自由的可能有多少?
但是,自由是什麼?終究,表面上自主的自由自在生活,其實是架構在斷裂的、身不由己的自由投稿人(free lancer)的、朝不保夕的、時好時壞的收入上。
更不要說,沒有一個固定的老闆為你投保勞保、健保。往往,當別人開始起算退休倒數時刻時,自由工作者發現,驀然回首,沒有一個可以退休的渴望目標。
所以,自由工作者的選擇愈發弔詭:有人逆向再回頭到一個機構上班;但是憑藉的是,自己永不退流行的、永遠有市場的專業。例如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執行長呂新科。
有人則發現,退休後開創第二專長才是真正的自由。在日本20年,《中國時報》前任東京特派員劉黎兒,在剛剛滿25年的今年五月初,就毅然辦理退休;從此跨入純文學寫作,不只要為公共電視寫一個劇本,還要首度嘗試長篇小說。
因為專業所以自由
另外一種自由工作者,是「過盡千帆皆不是」,他們也多次進入主流職場上班,還頗有小成,迄今被人記得;但是隨著總體經濟萎縮,主流的職缺越來越少,自己又只喜歡特定的工作,於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乾脆在家開工作室。例如前《中央日報》的主編陳昭如,目前就是成天在家的專業電視編劇,但她的專長應該是文化評論。「我只喜歡寫作,而文化評論的版面、媒體又這麼少」陳昭如說。
因為變動太大,經濟安全性常受影響,自由工作不是人人能做的,也因此,自由工作者的面貌越來越複雜;工作處境的優缺點,也越來越難辯證。是得?是失?越來越難清楚定義何謂個人真正的福祉?到最後,30歲世代有一天會憬然領悟:不斷強化自己的專業,恐怕才是自由工作者唯一不敗的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