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會研究運氣,但他們偶爾也會利用運氣。我們都聽說過人們偶然在實驗室的工作台上有了新發現的故事。我們不清楚這些事發生的頻率,以及它們是否真像聽起來那麼幸運。事實證明,牽涉其中的科學家往往得不到他們應得的聲譽。鮑伯.霍姆斯(Bob Holmes)告訴我們為什麼如此。
如果你想讓矮牽牛花變成深紫色,你只要額外添加一個色素基因,對吧?錯,因為額外的基因會讓花變白。這個讓人驚訝的發現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兩位植物生物學家各自發現的,一個是美國的理查.約根森(Richard Jorgensen),另一個是荷蘭的約瑟夫.莫爾(Joseph Mol)。他們都沒把這個發現視為錯誤,而是覺得自己有重大發現,而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們發現細胞用全新的方式調節基因表現,如今這種現象被稱為RNA干擾。自此之後,RNA干擾成為諾貝爾獎的主題,被用來拯救生命,而且還會持續拯救更多人命。
在科學界裡,這個發現絕不是好運的唯一例子。美國雷神公司的工程師珀西.斯賓塞(Percy Spencer),曾在1945年試驗一個雷達設備,並發現他口袋裡的糖果融化了;這次的發現,讓雷神公司在兩年後研發出第一台商用微波爐。1976年,化學家莎施康特.潘迪斯(Shashikant Phadnis)的教授,要他測試一種研發中的氯化糖化合物,這種化合物被打算用來當作殺蟲劑。當時,潘迪斯把教授告訴他的「測看看」(test it)誤聽成「吃看看」(taste it),因此發現該化合物極甜無比。不過,在實驗室裡,這種誤聽可能造成潛在的可怕錯誤。如今,我們知道這種甜味劑就是代糖。另外,人們在尚未發現威而剛具備有趣又很有市場價值的副作用之前,它其實是一種失敗的心臟病藥物。諸如此類的例子顯示,偶然性在科學的進步過程中,往往扮演了戲劇性的角色。然而,偶然性對科學的貢獻,我們又到底瞭解了多少呢?如果我們能夠更精確地定義好運,那麼它的影響力就更容易衡量了。它是否像買到贏錢的彩券,是個你我都可以做到的事,還是它像路易.巴斯德所說的「機會只會眷顧準備好的人」?最起碼,有位學者不但認為巴斯德是對的,而且現在我們甚至可以訓練大腦,讓它接收到偶然性的幽微訊號。
人們對於偶然在科學裡扮演的角色究竟有多重要,有很大的歧見。「我們沒有太多關於偶然性的故事。基本上,只有幾十個這類的故事,但在過去兩百年來,很多發現是從純粹的埋頭苦幹得來的。」位於以色列海爾茲利亞的舒立克商學院的創新研究員雅各.戈德伯格(Jacob Goldenberg)說。「如果你想評估因為偶然與非偶然因素而發現事物的比例,我會說只有不到1.5%的事件是偶然造成的結果。但是,我們都喜歡這些故事。」
有些人則認為,偶然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英國卡迪夫大學科學社會學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說,「身為一個社會科學家,每個我想到的美好想法,在我還沒研究它們之前,我都不知道它們是從何而來的,而且它們出現的方式也非我所能預期到的。」如果我們低估了好運,有部分原因和好運的影響力有關。「我覺得小驚喜蠻常見的,大驚喜則非常罕見。」位於夏洛蒂鎮的維吉尼亞大學社會心理學家麥可.高曼(Michael Gorman)如此說。
大家之所以意見分歧,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很難界定什麼叫做偶然。畢竟,生命就是走在一條分岔的道路上,每次我們來到岔路之前要選擇去向時,往往都是個偶然事件。例如,學校裡有個非常懂得啟發學生的科學老師,公司裡的同事剛好知道一則有用的消息,一個看起來不太可能成功的實驗正巧做得很好。所有這一切都和偶然有關,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發現的東西是出於偶然。例如,神經生物學最熱門的領域之一是光遺傳學,它讓研究人員可以精確地控制神經元組的行為。艾德.玻伊登(Ed Boyden)和他的同事在加州史丹福大學工作時,發現了這領域的一個關鍵技術,也就是可以用藻類的光敏蛋白來觸發神經元的放電活動。他和志同道合的同事(這是他第一個好運),多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用光來控制神經元,然後他們偶然間發現了藻類研究(更多的好運),並決定試將藻類基因插入小鼠的細胞裡。
「我們試了第一次就成功了。」目前人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玻伊登回憶說。「誰會知道那些來自藻類的分子是非常不同的生物體,可以在神經元中發揮作用?這也是偶然的。」後來他們才知道,他們比自己原先以為的更幸運,因為藻類蛋白需要另一種分子才能正常運作,而哺乳類動物的大腦恰恰由於不明原因會製造那種分子。
即使如此,偶然性在這個故事裡只占了一半的重要性。玻伊登和他的同事本來就非常關心如何控制神經元,因此用巴斯德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的頭腦已經「準備好了」。
也許,偶然性在科學裡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就是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青黴素。1928年,一個飄盪的真菌孢子落在倫敦聖瑪麗醫院實驗室的廢棄細菌培養基中。幾週過後,當弗萊明看著培養基時,注意到真菌盤據的周圍有個圈圈,有某個東西殺死了附近的細菌。那東西最後被確認為青黴素,也就是盤尼西林。
然而,弗萊明的發現並非憑空而來。
在上個世紀裡,包括巴斯德在內的其他科學家,都已注意到黴菌會抑制細菌生長,弗萊明本人則花了幾年的時間尋找可以殺死細菌的合成物,並且已經發現了一種溶菌酶;這種酶是他從某個罹患感冒的人的鼻涕裡分離出來的。弗萊明的大腦已經有所準備,因此能將這些事件連結在一起,但即使如此,人類還是又花了十年,才終於由其他研究人員—霍華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柴恩(Ernst Chain)—找到如何把黴菌研發成藥物的方法。
像這樣的發現通常被稱為「偽偶然性」,因為科學家已經知道自己在找什麼,只是在無意間找到了答案。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生動描述了這樣的發現:「搭上錯誤的船抵達正確的目的地」。如果我們極端一點,這種方法幾乎可以把偶然元素從各種發現中剔除。例如,發明家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在幫他的燈泡找到正確燈絲之前,曾測試過數百種材料;而製藥公司現在也會系統性地篩選數十萬種物質,以找到新藥。當我們用高曼所謂的「愛迪生式的方法篩選物質」而找到某種有用的東西時,這證明了努力還是勝過運氣,他說。
相反地,當研究人員偶然發現完全出乎意料的東西時,那才是真正的偶然,就像我們發現微波加熱或代糖。在這些案例裡,運氣扮演的角色更為明顯,雖然每個個案仍需靠警覺的觀察者注意到異常現象,而不把異常斥為錯誤,並且最終把它轉化成有用的結果。
不過,有些例子介於這兩者之間。就拿化工巨頭3M公司的科學家來說吧。當年他試著製作出黏性超強的東西,但最後做出來的效果卻很差。多年後,一位同事認為只有他研發的東西,可以讓他在教會使用詩歌本時,解決書籤掉出來的問題。正是這個靈感催生了便利貼的出現。
這類的意外在創新的歷史中,似乎十分常見。戈德伯格研究了兩百個重要發明的淵源之後發現,大約有一半的案例反證了那句古老的諺語:需要為發明之母。他說,「人們是先有了發明,然後才發現需要。」這讓最終的產品不完全是個偶然的發現,而更是善用你已擁有的發現之方法。
「幫既有的東西找到用處,比相反的情境來得容易,」戈德伯格說,「當一個東西真正存在時,人們便可以發揮很多創意。」他指出凡士林的例子,凡士林來自人們處理石油後的黑色爛泥。當化學家開始尋找如何應用凡士林時,他們才發現可以把這種純化的果膠用來治療燒傷。
運氣顯然有助於一些技術大放異彩,但它對更廣泛的科學發現究竟有哪些影響,目前還不清楚。的確,奇聞軼事確實存在,但毫無特殊之處的事情也常出現。似乎沒有人針對科學發現進行過有系統的研究,藉此衡量偶然出現的頻率如何。
的確,這樣的研究幾乎不可能做得很好,研究創造力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家迪恩.基斯.塞蒙頓(Dean Keith Simonton)說。一般來說,研究者不會在科學論文裡提到是什麼啟發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們很難重建偶然的作用。此外,偶然也許和努力密不可分,因此我們很難衡量兩者各自的貢獻為何。「即使我們接受牛頓發現蘋果落地的經驗是有幫助的,但是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Principia)又有多少該歸功於偶然性?」他問。
人們想直接將科學的偶然性加以量化的企圖,大約發生在二十年前。當時西班牙阿爾卡拉大學的胡安.米格爾.坎帕納里奧(Juan Miguel Campanario),研究了兩百零五個最常被引用的科學論文,發現其中占8.3%的十七篇論文,都提到有某種偶然導致研究者發現了研究成果。然而,這數字可能低估了偶然出現的實際頻率,因為不太可能每個作者都在論文裡提到他們遇到的好運。
即使我們很難確定在科學裡偶然性有多常見,但人們普遍認為,只要偶然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多原創性的發現,那麼自然多多益善。「如果你做的東西只需要你個人的聰明才智和努力,那麼很可能早已有人發現它了。」玻伊登說。因此,我們要常常做些刻意讓偶然出現的事。
現在,玻伊登讓大家找到能自己召喚出幸運女神的方法。他在麻省理工學院開設一門課,教大家培養偶然性。他要求每組學生有系統地徹底改變一個科學領域。「我想,我們現在已夠瞭解如何製造偶然性,所以我們該教會大家這件事,」他說。
玻伊登在研究裡表示,為自己量身打造好運的第一個規則是,列出所有可能的想法。他強調這規則聽起來有點蠢,但實際上不然。這裡的訣竅是,把可能性的範圍細分成非此即彼的選項,然後反覆做上一遍又一遍。舉例來說,假設你正在尋找一種用光學來繪製大腦圖的新方法,你可以選擇在大腦裡偵測光子,或是等光子離開大腦後,在大腦外偵測它們;如果你在大腦內做這件事,你可以用主動電子,或是使用被動探測器,諸如此類。他把這方法稱為「磁磚樹」(tiling tree),因為它的分支就像一棵樹,以此把整個「想法空間」鋪滿,就像地板上的地磚一樣。
實際上,這是愛迪生式的思想天羅地網。「你可以把它細分成更小的類別,如此你永遠不會失去任何可能的想法。在這些分支的最頂端,是你可以嘗試的事情,」玻伊登說。這一步正是偶然性可能出現的地方。
玻伊登的第二個訣竅是把範圍擴大。他自己的研究團隊包括工程師、物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等等,這種多樣性提高了人們想到出人意表概念的機率。同樣道理,一次處理多個事物比只做一件事好,這也提高了跨界刺激的可能性,而這就是愛迪生創造力的關鍵來源。塞蒙頓曾針對愛迪生歷來共一千零九十三件的專利進行研究,他發現愛迪生研究主題越多,他提出的專利也就越多。
有個比較有爭議的方法可以用來提高偶然性,這方法對於能開拓全新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來說尤其有效。這方法是單純去找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然後無限上綱地資助他們做研究。
這就是在諸如貝爾研究室這種知名研究中心所使用的方法,目前谷歌公司依然在相當程度上採用這個方法,比方說允許工程師用20%的時間研發業餘專案。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石油巨頭英國石油公司資助了一個沒有實用價值的研究計畫,目標是尋找最優秀的科學家,並且沒有任何條件地資助他們。「我在英國石油公司過了十三年的自由生活。」唐.布雷登(Don Braben)回憶說,當時他執行該計畫,而他目前在倫敦大學學院副院長辦公室做研究。「當時有一萬個人申請,而我只挑了三十七人。」他說,其中有十四人取得重大的突破。
這是贊助機構至今仍然必須留意的一個課題,柯林斯說。「想擁有一個懂得鼓勵意外發現的政策並不容易,」他說,「但要有一個會妨礙人們手腳的政策並非難事。」今天,想要拿到研究獎金是件非常競爭的事,在許多案例中,只有10%的申請人可以得到贊助,所以研究人員必須小心行事,去做他們知道可以達成結果的研究。比較冒險的提案可能有嶄新的結果,卻可能會因為冒的風險太大,而無法得到贊助。
從本質上來說,如今的系統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它不相信偶然,所以我們就很少發現偶然了。然而,當我們在思想上擁有一些啟迪,再加上一點點運氣,狀況就可以逆轉。
善用幸運女神
—19世紀的化學家威廉.珀金(William Perkin)曾試圖從煤焦油中合成出無色的抗瘧藥物奎寧,結果他得到了一種亮紫色的化合物,這種化合物成為世界上第一種合成有機染料。
—發明家喬治.麥斯楚(George de Mestral)在一次健行時,被沾黏在他褲管上的毛刺所啟發,因此發明了魔鬼氈(Velcro)。
—羅伊.普朗克特是杜邦公司的化學家,他在研究一種新的氯氟烴冷卻劑時,發現了留下在容器上的滑溜塗層。目前,人們已廣泛使用這種塗層,並稱它鐵氟龍(Teflon)。
— 20世紀30年代,貝爾實驗室一位工程師叫做卡爾.央斯基(Karl Jansky),當時他正在研究橫越大西洋的無線電傳輸,發現靜電來自空中特定個方向。這個觀察讓無線電天文學從此誕生。
—巴奈特.羅森堡(Barnett Rosenberg)1960年代研究電對細菌的影響,他發現有些細胞喪失分裂的能力,其中的罪魁禍首原來是白金電極的副產物。我們現在都知道那是順鉑,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抗癌藥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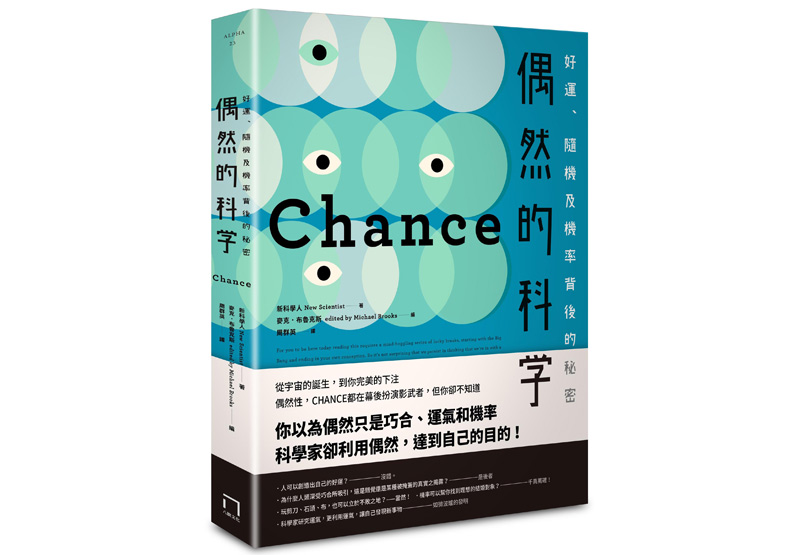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偶然的科學:好運、隨機及機率背後的秘密》一書,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著,周群英譯,麥克.布魯克斯(Michael Brooks)編,八旗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akuta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