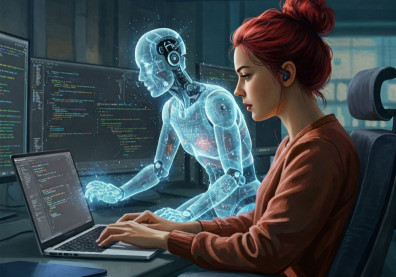下北澤
東京作為一個大都會,好就好在它有不同的表情:既有新宿、澀谷的現代繁華,又有上野、日暮里的古風質樸;既有赤坂、銀座的紙醉金迷,又有御徒町、新橋的平民氣質;有六本木、表參道的洋派,有日本橋、淺草的和風,有秋葉原、原宿的後現代,有神田、神保町的書卷氣……而在這諸多表情中,不能不提下北澤。
(首圖圖說:下北澤是一個袖珍街區,彈丸之地分布著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店鋪。)
下北澤的氣質,一言以蔽之,就是──好文藝!到底文藝在哪兒呢?這麼說吧:下北澤是演劇街,小劇場、電影院林立,一出車站,到處可見設計風格前衛的舞台劇、音樂劇海報,時而還能碰見扛著道具,戲妝都來不及卸的演劇青年、美少女;下北澤是音樂街,彈丸之地,竟有數十家爵士酒吧,身背木吉他、中提琴的藝青碰鼻子碰眼;下北澤是青春的街,幽會「熱穴」(Hot Spot),連空氣中都充滿了荷爾蒙的味道。從時尚雜貨店,到兼營舊書、舊唱片的咖啡屋,從古董店、二手服裝店,到居酒屋、路邊的地攤兒,幾乎一水兒是青年人在運營、消費。不到下北澤,不知青春為何物。到了下北澤,才能體會青春不再的痛感。
凡青年人紮堆兒的地界,必是交通便捷之所。道理簡單:因為年輕人沒錢,窮忙,對效率有近乎嚴苛的要求,而下北澤再合適不過。車站月台的正上方,能看見小田急線與京王井之頭線呈「X」型交叉,前者連結新宿與小田原,後者連結澀谷與吉祥寺。到新宿七分鐘,到澀谷只需四分鐘,在地理上,下北澤可以說是都心的中核。與池袋、新宿等超大型「城中城」不同,下北澤是一個袖珍街區。以世田谷區北澤二丁目為界,充其量只有方圓一里地(華里),借用日語的表達,是「貓額」大的地界,但卻是一塊超小資的飛地。除了車站南口旁邊,有一幢容納了本多劇場和世田谷區一座公立小禮堂的十二層樓宇外,絕大多數建築只有二到三層。走在街頭,覺得天際線好開闊。整個街區是步行者天國,除了偶爾有自行車叮鈴駛過,連紅綠燈都見不到。窄窄的馬路上,到處是閒逛的男女。人們呈「之」字形,隨意地穿行其間,似乎要將道路兩側的店鋪「一網打盡」。不過,彈丸之地分布著大大小小一千五百餘家各具特色的店鋪,「一網打盡」談何容易!
說到下北澤的店鋪,不能不提「雜貨屋」。說是雜貨,但卻不同於通常的雜貨鋪,實際上是精品店。首先是明亮。也不知是何種燈具,使店鋪中的任何位置,都能得到均勻且極亮的照明,全無死角。其次是商品擺放率性而為,愛誰誰,完全無厘頭。譬如,燭台和木質小皿的旁邊,是女性圍巾、手套。上方的貨櫃上擺著幾種口袋本書籍,書籍邊上是唱片,而唱片的後面,立著幾只木吉他……店中完全不辨方位,密集的貨架中間,闢有窄窄的通道,勉強僅夠兩個人側身通過,卻沒一條是直的,乃至收銀和出口在什麼位置,都需要抬頭看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指示牌確認。顧客在琳琅滿目的商品中穿行,耳邊傳來節奏高亢、分貝卻不高的流行音樂,哪怕店中只有三名顧客,也會有種擁擠、嘈雜的感覺。這實際上是一種稱為「Noise」(中文中似無相對應詞彙,姑且稱之為「雜遝」文化)的後現代文化。
幾年前,著名文化學者宮澤章夫在東京大學授課,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後出了本大部頭著作《Noise文化論》(註一)。他借用社會學者宮台真司的著作《夢幻的郊外》(註二)中的兩個概念──「安靜的房間」和「雜遝的靜謐」,認為「雜遝」的感覺,其實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裡,連清嗓子的一聲輕咳都會有「雜遝」感,但在周圍充滿噪音的環境中,即使很大的動靜也不會使人感到「雜遝」,即所謂「雜遝的靜謐」。前者是歐美的城市,後者是亞洲城市的感覺。因此,「雜遝」之令人感到「雜遝」,首先意味著感受者內心「理應排除」的下意識。相反,某種乍看上去不無凌亂的樣態,但當它成為某種背景時,卻反而使人內心有種「靜」的感覺。原來,所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居然與後現代文化是相通的!
店鋪如此,整個街區亦如此。稍往深處走,過了茶澤通,便是大片高級住宅區,鬧中取靜,優雅整飭。如果算上東條英機的話,此地曾先後住過三位首相(另兩位是佐藤榮作和竹下登)。下北澤之為「小資重鎮」,由來已久,歷史可追溯至戰前。因此間街道狹窄,洋風的酒吧、咖啡屋集中,整個地區有種大沙龍的氛圍。店鋪多,野貓就多,荻原朔太郎曾在小說《貓町》中描繪過這裡的風景。當然,如此沙龍,有多少野貓,便有多少文人騷客──不,後者也許更多──坂口安吾、橫光利一、室生犀星、井上靖、田村泰次郎、一色次郎等,是這裡的常客。坂口安吾年輕時曾在附近的代澤小學短暫任教,後在隨筆《風與光與二十歲的我》中追述過下北澤的青春放浪。
戰後初期,物資短缺,下北澤一度黑市化。上世紀五○年代初,一些店鋪開始經營舶來品,並逐漸做大,形成了一種摩登的西洋範,成了該地區的文化標籤。這種符號很吸引年輕人,於是,從七○年代初開始,大批藝青進駐,搖滾、爵士、布魯斯等各類主題音樂酒吧先後登場。一九七九年,舉辦了首屆「下北澤音樂祭」,遂固定化,下北澤成了音樂街。一九八二年,名演員本多一夫在車站南口創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本多劇場,帶動了周邊地區的迷你劇場熱,下北澤又成了演劇街。
女作家松原一枝在其著作《文人的私生活──昭和文壇交友錄》中,描繪過一群「下北澤的文人們」。小說家森茉莉是明治期文豪森鷗外的長女,戰後寓居下北澤,是地方的聞人。她每天早晨必到一家叫愛麗絲的咖啡館「報到」,且永遠坐在靠近博文堂書店一側的一張固定的檯子前看報紙,《朝日》、《讀賣》、《每日》等,逐一翻過。讀完一份,並不摺疊復位,接著打開另一份。女招待面無慍色,每每邊拾掇報紙,邊嘟囔「又得給茉莉女士擦屁股」。茉莉作家完全充耳不聞,讀得專心。彼時,茉莉剛與山田珠樹離婚,跟長子爵同居。據知情者透露,作家「與爵像戀人般地生活」。茉莉作為長女,幼時備受鷗外的嬌寵、溺愛,性格純真,童心未泯,終生處於世間第一「卡娃伊」女的自我幻覺中,不願自拔。其父親的著作權過期之後,她全靠寫作為生,當時尚未出版《父親的帽子》、《戀人們的森林》等成名作,生活之捉襟見肘可想而知。偶有爵的朋友來訪,禁不住茉莉的勸誘,在茉莉家中過夜。人鑽進被窩後,見天花板上貼著一張字條,上寫「一泊X X元,早餐X X元」,宿客大吃一驚。想起來到外面去,卻聽見茉莉在紙拉門外的過道上行走的聲音,馬上縮回去,背對著過道,待茉莉走過……後茉莉不止一次問松原一枝:「妳說那男的是不是對我有點那個意思呀?」令松原哭笑不得。
二○一二年初冬的一天,空氣溼潤。向晚時分,天上飄起了薄雪花,雪花落在雨傘上變成小冰凌,然後又變成了雨滴。背著沉重的提包,逛了半天,多少有些累,便折進街角一家看上去特時尚的咖啡屋,找了個靠窗的座位。落座後發現,這是一爿咖啡兼精品兼舊書店。店中只有一位中年老闆娘兼女侍在忙活,頭上紮著手絹,胸前繫著圍裙,風姿綽約。店中精品多係擺設,只有少數幾件繫著價籤的小物件可出售,但舊書都是商品,且品味不俗,當然價格也不菲。我惦記著晚間在新宿的約會,有些心不在焉。品完一小杯Espresso,挑了三本舊書,兩本梅棹忠夫,一本柳田國男,便埋單離去了。
出得店來,天完全黑了,路燈感覺比東京的其它地方昏暗,乃至燈下的街景有種影影綽綽的感覺。雖然下著細雪,路邊的跳蚤市場卻未收攤,幾個頭上裹著白毛巾、繫圍裙的青年在一面巨大的遮陽傘下吆喝著舊衣、舊唱片和古董。地攤斜對過,是一家居酒屋,房簷下掛著一串印有店幌的紅燈籠,透著暖意。我突然發現,這家居酒屋有些特別:比一般店家多了一圈緣廊,就像普通的民居一樣。緣廊上,也零星擺放著幾張炬燵(註三)。靠近屋角的那張炬燵旁,坐著一對青年男女,像是情侶。男著鐵灰色和服,女則一副O L裝扮,上身穿職業西裝,腿在布團裡,看不見──大概穿著裙子吧。但見身穿短和服的男侍者端著托板,從屋裡出來,掀開暖簾,走在緣廊上。雪白的和式襪套踩在原木地板上,發出「咚、咚、咚」的聲響。然後情侶端起生啤酒杯,一句「乾杯」,輕輕一撞,深飲一口。
我剛好從緣廊外經過,薄雪中看到這一幕,內心熱流上湧,一時間幾乎忘了所處的時空方位,眼前彷彿是一幅竹久夢二絹本著色的立軸〈時雨的炬燵〉,又像極了小津安二郎作品中低機位拍攝的長鏡頭。費了好大勁兒,我才讓自己相信這是在世田谷區的下北澤。接著便朝車站大步走去。
註一:宮沢章夫《東京大学「ノイズ文化論」講義》(白夜書房,二○○七)。
註二: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成熟社会を生きる若者たちの行方》(朝日新聞社,二○○○)。
註三:日式小炕桌,桌面下裝有取暖的熱能燈,四周有布團,可蓋住雙腿以保暖。



(圖說:「後現代共和國」下北澤。)

本文節錄自:《東京文藝散策(增訂版)》一書,劉檸著,遠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