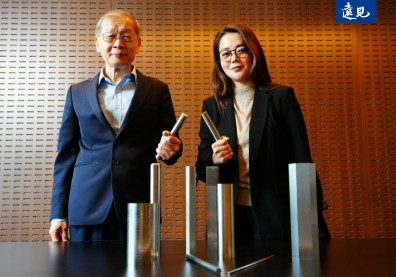二○一三年七月十六日
永別的時刻不遠了。他的丈夫命在旦夕,只要在漫漫長夜聽到有人輕敲房門,就是永別的時刻,但新婚才五天的吉姆・歐柏格斐不願去想喪禮。在如此晴朗的七月早晨,辛辛那提市的天氣酷熱難耐,丈夫約翰・亞瑟從臀部到腳趾的痙攣奇蹟似地消失後,終於可以在病榻上坐起身來。
(圖說:罹患漸凍人症的約翰為了保障另外一半的權益,搭乘醫療專機赴往合法州締結婚約。)
約翰沒有辦法戴上婚戒,手指會因為戒指的重量而發疼。他赤身躺在電毯下,避免衣物造成皮膚發燙。他現在只剩下說話的能力,卻也常常喘不過氣來而沙啞,因此必須聚精會神,深吸幾口氣,才能勉強發出幾個音節和聲音。吉姆還得彎下腰來,才能聽到他的聲音。一個曾能發出宏亮笑聲的人,如今只能用氣音說話,每每都讓吉姆感到無比打擊。但是這五天以來,約翰卻能奮力地說出一個完美的詞。
老公。
晚安,老公。早安,老公。我愛你,老公。
疾病來得突然,就在兩年前約翰四十五歲生日過後,他的左腳變得難以行動,彷彿拖著四、五公斤的重量。自此,他們所知的一切開始崩塌、改變。漸凍人症的診斷結果似乎將他判了死刑:這種神經疾病會攻擊大腦和脊髓的神經細胞,最後奪走全身肌肉的運動能力,包括幫助空氣進入肺臟的橫隔膜。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會讓患者窒息而死。
吉姆看著約翰,看著兩人曾經共枕眠的臥房。在這漆成淡黃色的房間裡,擺了一張因為約翰重量而下沉變大的病床。吉姆早已搬到客房去睡,但是今天早上,他在約翰床邊的椅子已經坐了數個小時。他一直看著電視新聞,聲音大到足以蓋過氧氣機持續發出的咻咻聲。一條管線繞過約翰的耳朵,插進他的鼻孔灌入氧氣。他的房間坐西朝東,吉姆拉開了百葉窗簾,讓約翰可以照到太陽。
這一天,他們正在等候一位訪客。
吉姆非常緊張,因為即將來訪的是一位三十年來常與辛辛那提市打官司的民權律師。下午兩點過後不久,艾爾・葛哈斯坦來到他們位於市區的公寓、輕敲家門。他面帶善意的笑容,雙頰殘留一點灰色的鬍碴,感覺像是匆匆忙忙趕過來。他調整了一下細框眼鏡,伸出手來與吉姆握手,友善地緊緊抱住對方。
艾爾一路跟著吉姆,沿著走廊走到臥房,約翰此時正靠著枕頭等待。艾爾把公事包放到地上,幾乎沒有去看那張笨重的病床。葛哈斯坦家共有六個孩子,艾爾的妹妹罹患了多發性硬化症。每到週六早上,艾爾都會坐在她的床邊喝著咖啡,等候妹妹的看護人員。
他彎下腰,輕輕搭著約翰的肩膀,對著他說:「和我說說你們的婚禮吧。」
「說出『與你結為連理』是我這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吉姆說,看向約翰覆在毛毯下的虛弱身體,腦中想起以前笑容滿面、一頭蓬鬆金髮的修長男子。
他們在辛辛那提市同居二十餘年,這個地方橫跨俄亥俄河谷,遍布山地與丘陵。他們從未想過在此結婚,因為俄亥俄州選民不贊成同性婚姻,即便州政府允許同性婚姻,聯邦政府也不予以承認。然而,就在三週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同志族群捎來了重要的一勝,認定依照州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享有完整的聯邦權益,包括醫療、社會安全福利、榮民服務、住宅和稅務,於是吉姆和約翰特地飛到馬里蘭州結婚。私人專機上,約翰脆弱的身體時時刻刻都接著醫療器材。
「他受了很多苦。」吉姆告訴艾爾,「你愛的人必須經歷一番折磨和不適,才能做到數百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一想到就覺得挫折又難過。」
「我希望受到公平的對待。」約翰奮力而緩緩地說出每一個字,「我希望在我死後,法律可以照顧吉姆。」
艾爾專心聆聽而不做筆記。二十年前,他才四十出頭,一邊照顧三個孩子,一邊靠著微薄的勝訴抽成執業。當時,辛辛那提市的選民更改了市憲章,永遠明文禁止為了保障同志族群不受居住和就業等歧視政策立法。對艾爾來說,這是一個專斷且充滿仇恨的條文,為此,他在聯邦法院提出訴訟。他有將近五年的時間義務訴訟;官司結束時,他更對這座城市、法院和法律的適用性心生質疑。他還曾考慮關掉律師事務所,舉家搬離辛辛那提市、改行去教書。
他懷疑自己是否還有能力接下另一個重大的同志人權官司,但是在六月二十六日,「美國訴溫莎案」的判決宣告《捍衛婚姻法(Defense of Marriage Act)》的某項關鍵條文違憲,讓十五多年來「婚姻為一男一女結合」的唯一定義走入歷史。聯邦最高法院的安東尼・甘迺迪大法官在判決書中寫道,該法是在告訴同志伴侶:「他們有效締結的婚姻不值得獲得聯邦政府的承認。」
艾爾的事務所積滿灰塵,樓下設有公車站牌,且可俯瞰聯邦法院。門廊貼著蘿莎・帕克斯的海報,茶水間公告欄上釘著恐嚇信件。艾爾每天深夜就在這裡研究俄亥俄州於二○○四年由多數選民表決通過的同性婚姻禁令。他發現了一項重大的法律邏輯不一之處。
俄亥俄州禁止堂(表)兄弟姊妹和未成年者結婚,但若這樁婚姻是在他州締結,則會予以承認。這種「儀式地」的規定來自一個由來已久的法律原則—「契約締結地法」,此由拉丁文書寫的法律詞彙,意思是「締結契約時所在地的法律」。然而這種原則在俄亥俄州並未一體適用,在他州締結的同性婚姻將排除在外。艾爾心想,溫莎案判決後,如果聯邦法院必須比照異性婚姻、公平承認同性婚姻的話,那麼像俄亥俄州這種地方不是也得承認同性婚姻嗎?
可是這項發現過於虛無縹緲,直到一位共同朋友向艾爾介紹了約翰和吉姆,分享他們飛到馬里蘭州結婚的故事。艾爾下意識地衝到文件櫃,找出之前案件留下來的死亡證明。他從俄亥俄州衛生局掃描這份文件後,立刻發現他要的東西。「就是這個。」他喃喃自語。三天後,他前去拜訪約翰和吉姆。
吉姆起身離開倒水,艾爾跟著他走進飯廳,拿出那份死亡證明。「你一定沒想過這個吧,畢竟誰會一結婚就去想死亡證明。」
艾爾指到欄位十:婚姻狀況。
艾爾指到欄位十一:未亡配偶。
吉姆從未仔細看過死亡證明,於是跟著艾爾的手指看了又看。艾爾解釋,他們的婚姻在俄亥俄州根本不存在,約翰死後會被視為未婚,而吉姆自認會填上自己姓名的未亡配偶欄也會留白。死後,他們將是陌生人。
「約翰生平最後一張官方文件會是錯的。」艾爾輕輕地說。
一想到約翰不顧骨頭疼痛、皮膚發燙,也要飛到八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結婚,吉姆開始覺得頭疼。「我不相信。」他邊說邊用手背拭去淚水,「我真的無法相信這種事。」
全國的律師和同運倡議團體都把重心放在更大的目標,推動全美五十州承認同性婚姻,但是艾爾看到的是更小、更急迫且切身相關的需求,一個美國法院從未完整探討的需求。他問吉姆:「你想不想為了自己和約翰,談談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為俄亥俄州的所有同志朋友做出改變?」
吉姆不確定他們的餘生能不能打完一場聯邦訴訟,但是當他回到走廊看著約翰、看著床頭櫃上的婚戒,他心裡再也沒有猶豫。他不曉得這場官司會如何發展、結果會是如何,但是他在約翰的同意下,接過艾爾拿出來的文件,簽下自己和約翰的名字。在黃色臥房的昏暗燈光下,吉姆與丈夫對俄亥俄州三百三十萬選民所同意納入州憲法的同性婚姻禁令,發起了史無前例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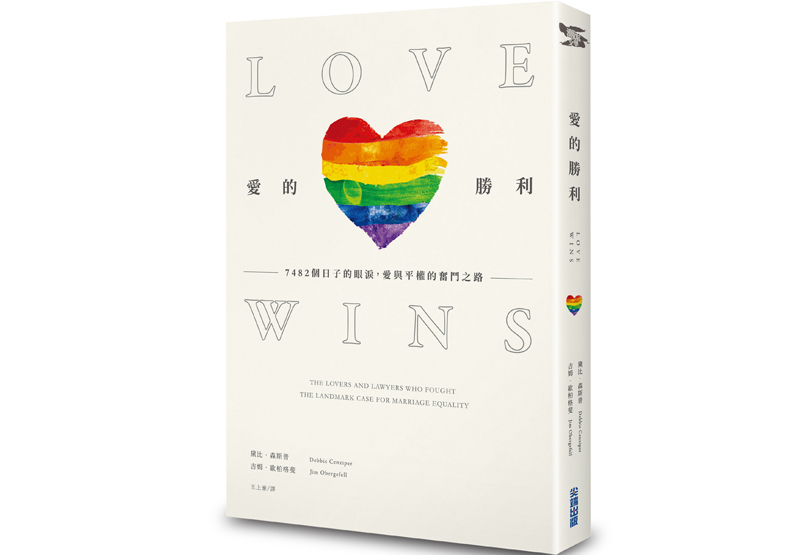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愛的勝利:7482個日子的眼淚,愛與平權的奮鬥之路》一書,黛比‧森斯普(Debbie Cenziper)、吉姆‧歐柏格斐(Jim Obergefell)著,王上豪譯,尖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