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的火車不斷把人帶回過去。回到一個充滿鋼鐵和塵埃、瀰漫機油臭味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飽經風霜的憔悴老人提著帆布購物袋在街上行走,衣衫破爛的乞丐和叫賣小販彷彿來自停格在共產主義年代早期那種孑然的貧困,即使廉價航空已經大舉進占國內空運市場。在這個世界裡,老舊建築獲得翻修整建的情況不多,通常是直接拆除蓋成新大樓。
這次我的旅行路線是從布加勒斯特往東直奔康斯坦察。展開在車窗外的是一個沒有任何山丘或其他凹凸、完美得宛如函數線條的地表,整齊劃分成穀麥田。遼闊大地盡情向天際伸展,旅人若懂得引領細看,彷彿便要窺入無垠蒼穹未知境地。世上或許唯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能在不同帝國版圖交割疊置之處,提供如此豐饒而開闊的進出路徑。每回通過瓦拉幾亞這片地景,我總是一而再地感到椎心的淒楚。
在瓦拉幾亞東部,原本由西往東流的多瑙河陡然轉向北方,並分叉成兩條主要水道。我在費特什蒂(Fetești)邂逅了第一條河道。周遭風景用灰槁的暗藍色澤隱約昭告另一種地形就此鋪陳,對面河岸出現沼澤區橡樹及樺樹林的形影。不久後,第二條河道悄然現身,那又是一片以駭人的靜默慢速往前推進的水域。
火車在切爾納沃德(Cernavodă)靠站時,我想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的另一趟火車之旅。我從布加勒斯特當日往返,到這個地方觀察一座核電廠的興建工程。當年所見是一片沒有柏油路的地景,置身其中彷彿失去方位。我對此地的印象就像一張黑白照片。儘管天氣酷寒,渾身汙垢、表情絕望的工人只穿了單薄衣物,他們剛換班出來,在冰冷的冬季空氣中排隊購買早已失去新鮮度的麵包以及少得可憐的其他食材。李子白蘭地的氣味與體臭交融。我似乎又看到喬治烏─德治和西奧塞古時代的古拉格:數十萬獄囚被送到這裡當苦力,建造規模宏大的多瑙河─黑海運河。那是另一個時空的事;我離開以色列還不到一個星期,就已經強烈感覺到主流媒體報導錯過了人類真正在製造歷史的地方。
過了切爾納沃德繼續往東行進,雕塑般的低矮山丘映入眼簾,彷彿大地在伸展四肢,為空寂平野勾勒造型。這裡是別稱「小斯基台」的多布羅加:歷史上韃靼及保加爾各部族陸續進入這個地區游牧,拜占庭、鄂圖曼、俄羅斯大軍也時時壓境而來。多布羅加曾是蓋塔人(一支與達基亞人接近的色雷斯民族)的故鄉,具伊朗血緣的斯基台人也曾在這裡當家。擁有簡單火箭造型宣禮塔的土耳其清真寺與東正教教堂的銀色圓頂共同點綴這片大地風景。鄂圖曼帝國於一四一七至一八七八年大體統治該地區,更早以前則是保加爾人及拜占庭人來回進出,對其進行直接統治。
在康斯坦察,我同時感覺到某種略帶陰鬱的感性及一種能激盪靈感的混雜特質,這是數十年間我走訪其他黑海沿岸港都時的熟悉感受。保加利亞的瓦爾納(Varna)、土耳其的特拉布宗(Trabzon)、喬治亞的巴統(Batumi),這些地方都具有一種繁華落幕的陳舊優雅,在凌駕四方的俄羅斯與形勢多變的近東相互擠壓下騷動不安的板塊上悠然航行。康斯坦察令人想到羅馬尼亞在地理上相對接近土耳其、阿拉伯、波斯、阿富汗所構成的西亞世界,因此正如伊里耶斯古所言,這個港都就地緣政治而言對美國非常有用。的確,在九一一(註一)發生之後那十年,羅馬尼亞曾經多次成為美國軍事行動的中轉站(以及美國中情局的拘留中心,「黑色場站」[black site]所在地)。羅馬尼亞的領導人內心無法完全信任北約組織,因此為與俄國勢力抗衡,羅馬尼亞必須與美國另行建立特殊安全關係,以求自保。
康斯坦察是羅馬尼亞的發展樞紐。二○一三年秋天,這個城市同時處在破壞、荒廢及大規模都市更新的狀態,因而呈現某種戰爭片場景般的效果,只是機關槍掃射聲由鑽孔機及切割機的噪音取代。建設工程導致市中心街道阻滯難行,一層厚厚的灰塵籠罩一切,尤其是在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註二)的著名雕像四周。奧維德是在西元八年被奧古斯都皇帝流放到這裡,當時這座港都稱為托密斯(Tomis)。由於市中心許多地方被圍籬封起,能夠聚集或用餐的地方很少。不過這個城市確實在進步。外海的豐富能源蘊藏、大型的現代化港埠設施、興建中的世界貿易中心,以及歐盟挹注的巨額發展資金,這一切都使這座重生中的躍動城市必須投入瘋狂建設,而我知道,不消幾年,康斯坦察就會展現出我不再認得的新風貌。
在這片塵土飛揚的巨型建築工地上,土耳其及韃靼清真寺的宣禮塔和希臘及羅馬尼亞東正教教堂的閃亮銀色圓頂昂然伸向天空,其中尤以大清真寺的身影在天際線上特別突出。這座以澆注水泥建成的清真寺擁有埃及─拜占庭風格,於一九一三年由卡羅爾一世獻給穆斯林社群。沒錯,在歷史上,康斯坦察一直是個由多元少數族群組成的國際化港都,儼然是迷你版的亞歷山大港或士麥拿。
舉例而言,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結束後,羅馬尼亞接收北多布羅加,做為和平方案的一部分。羅馬尼亞韃靼人民主聯盟主席傑里爾.埃塞格普(Gelil Eserghep)指出,當時這個地區的人口有百分之五十五是土耳其人或韃靼人。目前羅馬尼亞只剩下四萬五千名韃靼人,這支民族發源自蒙古東北部,是成吉思汗透過金帳汗國延續至今的直屬後裔。某天晚間,我在康斯坦察跟埃塞格普見了面,他擁有相當典型的少數民族外形,包括膚色較深的圓臉,以及略帶蒙古風情的五官。我興致勃勃地聽他訴說這個城市在十九世紀乃至二次大戰以前的情形,當時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德國人、保加利亞人以及許許多多像他這樣的少數民族共同生活在這裡,其中大部分後來都已經離去:保加利亞人在一九四○年,南多布羅加從羅馬尼亞易主至保加利亞時進行的人口交換作業中遷出,德國人在二次大戰後離開,碩果僅存的猶太人則在共產統治期間紛紛求去,其他族裔的情形也類似。不過埃塞格普預言,目前暫時使這座城市變得不甚宜居的都更工程最終將促使這裡重新出現一種富裕的多元文化生活型態。當然不可能像一百年前那麼多元,但康斯坦察必然會在相當程度上重新朝那個方向發展。
土耳其社群的一名領袖瑟琳.土耳科格魯(Serin Turkoglu)告訴我類似的故事:共產主義摧毀多布羅加三萬兩千名土耳其裔人民的社群生活,並將教授土耳其文或公開教授伊斯蘭宗教視為犯罪行為。目前情況已經改善,學校課程每星期可以包括數小時的伊斯蘭教或土耳其語文教學。不過她認為目前有個危險現象:由於土耳其文化在康斯坦察可以非常公開地自由表達,年輕一代不再有她在整個冷戰期間對自身文化懷抱的那種強烈記憶與情感。「他們對傳統的興趣不及對全球文化的興趣,全球文化這種東西雖然能提供一切,但同時它也會減損一切。」
我搭計程車前往靠近保加利亞國界的黑海岸城鎮曼加利亞(Mangalia),這又是一個四十多年共產統治所遺留的巨大建築毒瘤。整座城裡只有一棟漂亮的建築物:埃斯瑪罕蘇丹清真寺(Esmahan Sultan Mosque),由土耳其蘇丹蘇萊曼大帝的一名孫女於一五七三年所建。宣禮塔及內部立柱均以切割細緻的石材砌造,屋頂是用鵝卵石鑲成,木料作工精巧美觀,地面鋪設潔淨無瑕的紅寶石色地毯。清真寺四周是一座大得令人心驚的墓園。整棟建築物在幾年前才經過翻新,它的規模不算大,稱不上令人嘆為觀止,但它擁有屬於它的完美。大約二十名說土耳其語的年輕人聚在外邊,準備進入清真寺做午禱。
我不禁心想,倘若羅馬尼亞擁有美好未來,它必將透過這種真純道地的生活美學開花結果。美麗與自由呼應,醜惡則伴隨壓制而來。我已經開始期盼在幾年以後回到黑海之濱,重返康斯坦察現場。
註一:即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這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於美國的一系列自殺式恐怖攻擊,根據美國政府的說法,係由蓋達組織(Al-Qaeda)所為。當天上午,十九名恐怖分子分別劫持四架民航客機,其中兩架衝撞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造成飛機上所有人及大樓中許多人死亡,兩座建築在兩小時內先後倒塌。第三架飛機撞擊華府附近的美國國防部大樓五角大廈。第四架飛機原本飛向華府,後因部分乘客及機組人員試圖奪回飛機控制權,最終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這系列事件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本土首次遭受空中攻擊,也是珍珠港事件後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發動重大攻擊,共造成約三千人死亡或失蹤(超過珍珠港事件)、六千人以上受傷。事件後美國發動反恐戰爭,於十月初以蓋達組織及塔利班政權為目標入侵阿富汗。
註二:普布利烏斯.奧維修斯.納索(Publius Ovidius Naso,西元前四三至西元一七/一八年),古羅馬著名詩人。奧維德(Ovid)為其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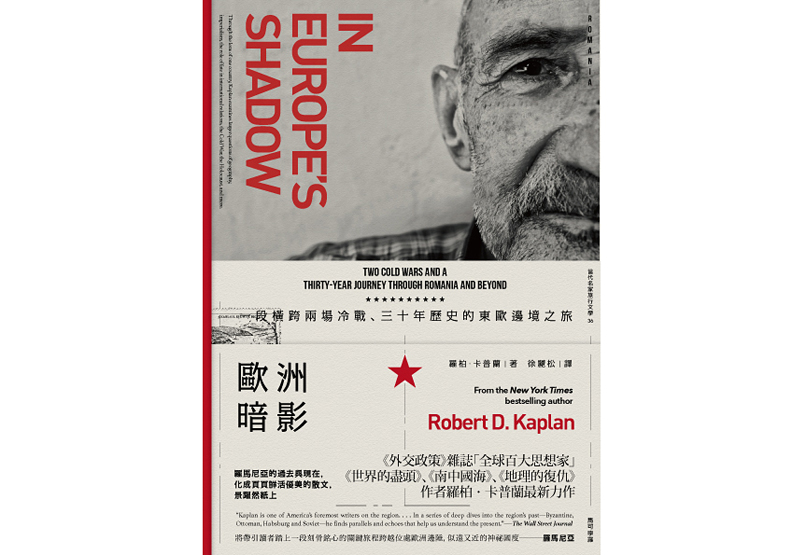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歐洲暗影:一段橫跨兩場冷戰、三十年歷史的東歐邊境之旅》一書,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徐麗松譯,馬可孛羅出版。
圖片來源:f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