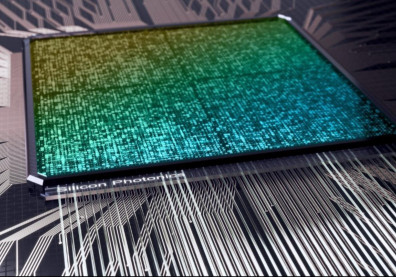像中國這樣因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有出超的國家,可對外投資(藉金融和直接投資)來抵銷這些剩餘。英國在19世紀便是如此,民間企業和英國政府在全世界各地投資英鎊。當今德國也是如此,大舉放款給歐元區其他國家(尤其南歐國家)。麥金農(Ronald McKinnon)和施納布爾(Gunther Schnabl)把英、德稱為「成熟」債權國,這麼定義是因為兩國用自己的貨幣來放款。成熟債權國將外流的資本和對外國的債權用自己的貨幣來計價,債務須以此貨幣來償還,債權人也可避免匯率風險。
中國雖有龐大的貿易順差,但人民幣兌換受限制,意味中國使用人民幣在國際上放款也同樣有限制,對外債權都以美元計價。這些年來,中國必須對外國人建立流動性高的美元債權(以美元計價的貨幣或金融資產)來抵銷貿易順差,近年來還漸漸實施流動性低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包括用於設廠和其他實體基礎設施,也包括投入政府主辦的援助計畫和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投資)。這種形式的放款,是未成熟債權人的代表特色,中國就是個例子。
這種放款模式,反映了人民幣內在且自我強加的限制。資本帳的限制和匯率不對稱的風險,都意味著央行就只能投資外國金融資產,卻得冒險堆積持有外國人的美元債權並累積美國公債。即使中國的商業銀行可以自由對外投資,他們仍得在人民幣存款和對外美元和其他外匯債權之間,面對外匯不對稱的風險。
未成熟的貨幣會產生大量的成本,而成熟的貨幣卻會有極可觀的益處。首先,很多貨幣未成熟的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常常受制於這個「原罪」而無法對外以本國貨幣借貸。他們可用美元在內的強勢貨幣借貸,如此有意願的債權人不會既有匯率風險又有違約風險(往往為此要求較高溢酬)。與發展完全的國際成熟貨幣能以自己的貨幣借貸不同,未成熟的貨幣在國內貨幣產生的收入和國際貨幣計價的負債之間形成了不對稱,就好比說有一個國內專案產生的人民幣收入,卻在國際上用美元來籌資。一旦國內貨幣因違約風險上升而貶值,就會對未成熟貨幣國形成融資成本上更大壓力。
其次,若不冒外匯風險,未成熟貨幣國家很難分散國內的信用風險。這對擁有長期負債的退休金和保險公司問題更大。就成熟債權國的情況來說,外國企業和主權實體可以發行債權人國家貨幣計價的證券。這有助於成熟債權國的金融業者分散風險。譬如,一個美國退休基金可以決定投資由一家總公司在法國的大型製造業者發行的美元計價債券。在這種情況,投資人可以進出於外國市場而不必冒匯率的風險,就連付息也用美元。
第三,成熟貨幣國家可擴大對其他國家的官方債權以本國貨幣計價,如此可降低匯率整體的風險,但未成熟貨幣國家無此選擇。中國正擴大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援助行動,也不斷在冒險,尤其就像在第二章所說,中國的債務國不乏經濟差而治理也差的國家。比方我在第二章提到的委內瑞拉,雖有龐大的石油資源,多年來經濟卻遲遲無法上軌道。即使支持委內瑞拉招致極大風險,中國依然承諾提供貸款和補助給這個拉美國家。但是油價持續低迷,使中國陷於逾期甚至倒債的莫大風險。
若中國能以人民幣計價提供放款,排除匯率風險,中國便能大幅減輕相對於委內瑞拉(其他相同處境的借債國)的風險,換句話說,中國縱使面臨債務國違約的風險,也不致多一層人民幣信用價值降低的風險。

本文節錄自:《人民幣的底牌》一書,蘇巴慈(Paola Subacchi)著,劉忠勇譯,大寫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