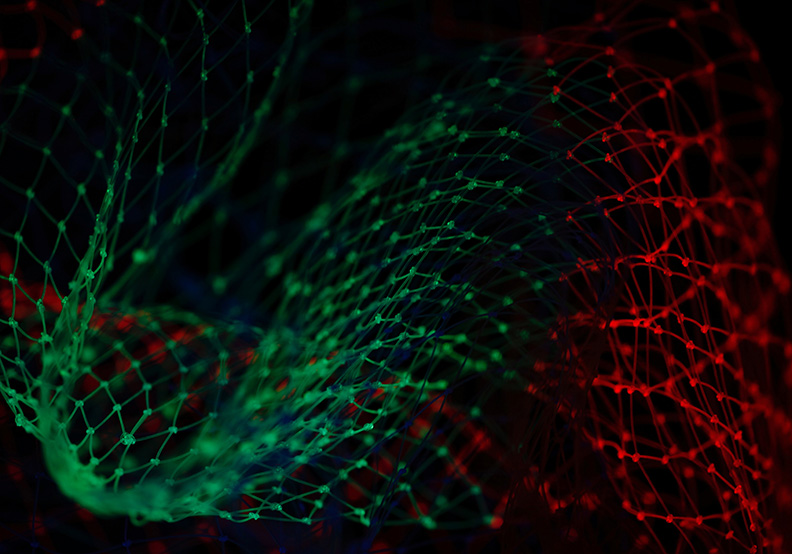2015 年,在中國「兩會」上,身為政協委員,我提出設立「中國大腦計劃」—由國家投入專項資金主導,盡快搭建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工智慧基礎資源和公共服務平台,如建立一個擁有幾十萬台伺服器的大型人工智慧平台,支援各項計劃參與方的數據調用、模型調試和應用開發,高效連結全社會的智力、數據、技術和計算資源,依託統一平台,實現資源共享,促進研發創新,這將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助推器。基礎研究的成果,應該讓更多中國企業受益,包括語音辨識、圖像辨識、自然語言的理解、多語種的翻譯,甚至無人駕駛汽車、無人駕駛飛機、智慧製造方面的機器人,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進行各式各樣的創新和實踐。
這件事如果只是百度來做,可能就只能提供幾萬台伺服器;如果由國家主導投入,那就是幾十萬台伺服器。只要平台大了,就可以降低成本,鼓勵更多創新。國家持續、穩定地大規模投入,讓一大批企業成長起來,隨之而來的就是愈來愈多的創新,進而奠定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全球創新領域的地位。我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我不在乎華爾街怎麼看,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成。」
然而,任何一項超級工程,都可能面對爭議。2016年9月,一場高能物理界的事件,意外掀起了輿論颶風,「超大粒子對撞機之爭」從學界延伸至社會,普通民眾都開始關注起「粒子對撞機」這個深奧的物理名詞。
粒子研究的重要性,在科幻小說《三體》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外星智慧生物為了阻止地球科技進步,利用量子糾纏原理,創造出擁有11D 形態的「智子」,發射到地球上。
以光速運動的智子,能夠同時干擾人類的所有粒子對撞機,精確破壞粒子對撞結果,鎖死人類的基礎物理研究,將人類科技禁錮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
「超大粒子對撞機之爭」從兩位局外人—美國數學家丘成桐和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王孟源的論戰開始,歷時三個月,還驚動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面對中國要不要建造超大型粒子對撞機的爭論,反對者指出:建造對撞機需要耗資數千億美元,電能消耗堪比一座大城市,但收獲的結果卻極為不確定,可能淪為一部物理學者的「大玩具」。美國擱置了類似計劃,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的成果寥寥,中國為什麼要建造?
支持者則認為,研究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非常重要,這將解開「宇宙如何誕生?」的天問。美國和歐洲的放棄和無為,正好為中國提供了機會窗口。中國是崛起中的大國,理應承擔理論物理先驅研究的責任。
最後,這場爭論以超大粒子對撞機未獲得中國「十三五」規劃審批而暫告段落。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從不缺乏大計劃,從改革開放初期的「863 計劃」中第一次提到「智能計算機」一詞至今,中國科學家花了四十年的時間,逐漸追上先進國家的步伐。鮮有人知的是,在沒有超級電腦、沒有大數據的年代,中國人工智慧是從大學實驗室錄製音庫起步的。正是前輩科學家的堅持,以及中國經濟實力與科技實力的與日俱增,互聯網企業才能在風調雨順的土地上突飛猛進、集涓成流,浩然成勢。
現今,在百度建立於中美兩國的人工智慧研究室裡,超過1,300 名不同族裔和國籍的研究人員,正夜以繼日地處理數百項相關專案,他們的成果都將匯入百度大腦中。這些研發者就像是當年美國在二戰期間研發、製造原子彈的工程「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中的一千多位科學家,也像是今天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三千多位科研人員,努力執行著超前於時代、暫時不為人理解的工作。改進演算法、建模升級和分析處理,百度大腦的研究人員正如粒子加速器中飛奔的粒子一樣,醞釀著一場AI 革命。
中國大腦計劃不同於超大型粒子對撞機,後者占地龐大、能耗驚人(歐洲的粒子對撞機運行需要1,200 萬千瓦電力),開發中國大腦卻是一項從下而上、水到渠成的工程,國家無須豁出血本,需要的僅是方向與決心。
「規模經濟」是中國產業成功的基本要素,在這個擁有超過13 億人口、7 億網民和數以千萬計工程師及科學家的國家,海量的資料、充沛的人才、豐富的企業案例、各式各樣的應用場景,像流水一樣奔騰。如果不能物盡其用,錯過這一波AI 浪潮,將科技制高點乃至國家安全拱手相讓,才是真正的「浪費」。
正如互聯網海量資料催生了Hadoop(由Apache 基金會開發的分散式系統基礎架構)、Spark(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AMP 實驗室所開放原始碼、類Hadoop Map Reduce 的通用平行計算框架)等巨量資料串流處理技術一樣,人工智慧已經在中國各地分散發展,猶如一個個神經節點,以其腦波促進中國大腦的到來,這是時代的召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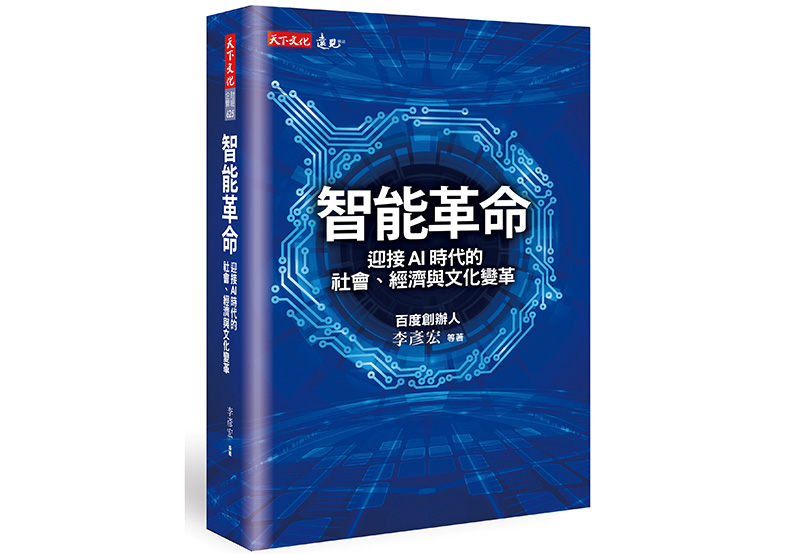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智能革命:迎接AI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一書,李彥宏著,天下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Pietro J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