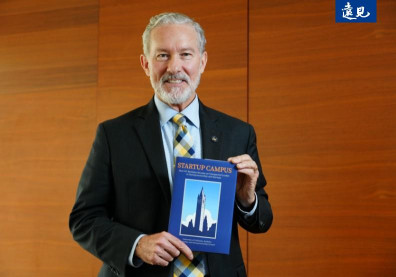如果要選出台灣善心人士最中意的援「外」之地,泰北華裔難民村絕對名列前茅。
從基督教到佛教,從扶輪社到獅子會,從大明星到無名氏,再加上帶官方色彩的「中國災胞救助總會」,有人捐錢捐衣,有人醫病教書,台灣各方慈善團體的旗幟,在泰北山區中交錯飛揚。
中華民國孤軍當年剛撤退至泰緬邊境時,每戶平均收入是零的艱難處境,曾讓不少中國人心中隱隱作痛。不過,根據救總統計,台灣各界對泰北難民村的援助,曾在八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接下來便「走下坡」了。今日每戶平均年收入仍只有泰幣兩千餘銖的泰北孤軍及眷屬,愈來愈少台灣人記得。
就在宇宙光雜誌社所創造的「動詞」--「送炭到泰北」即將成為歷史名詞時,漸弱的炭火今年由慈濟功德會再度點燃。
「我實在想不出國內還有哪個民間團體能比慈濟更讓人放心了。」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章孝嚴,一年多前眼見經費減縮的救總泰北難民工作團預定裁撤,當地僑胞即將乏人照顧,便往花蓮求見釋證嚴法師,期望較有國際援助經驗的本土慈善團體「慈濟功德會」,今後能接下救總的火把。
聚集今日台灣善款最多的慈濟功德會,於是派遣專人在台北、泰北之間飛來飛去,探訪無數難民村,發現當地生活窮困又無一技之長的人依然占大多數。證嚴法師答應了。
助人自助
歷經年餘前置作業,慈濟「泰北扶困計畫訪問團」一行近三十人(包括前美容院修指甲師傅及現任百貨公司董事長),捧著台灣數十萬捐款人的慈悲心,終於在今年六月間前往泰北難民村。
早上酷熱、中午豪雨、下午悶熱,慈濟三天活動期間正逢泰國雨季,在這片面積約台灣一倍、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大地,眾師父、師兄及師姐每天以五、六個小時乘吉普車在山間土路蜿蜒奔馳,從舉行慈濟村啟用典禮、慰問榮民之家到訪視貧戶,估計有緣相見的泰北人約達五百名。
每天晚上趕回旅館之後,慈濟人還得先把沾滿泥巴的白色工作褲送洗,再繼續召開「心得分享會」直至深夜。「我累得好充實。」負責活動策畫、教唱「慈濟歌」的中年婦女范春梅啞著嗓子說,來自台東的她,為了能有足夠體力從事慈濟志業,每天晨泳一千公尺,從不間斷。
「我還會再回來。」今年初起即不定期派駐該地、暫時置藥房生意不顧的梁安順則說。晒得黝黑、個頭兒不高的他,離家期間就靠同是慈濟委員的太太照顧生意及小孩,接下來的三年,亦將如此。
「希望我們能教當地人「釣魚」。」慈濟功德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表示。先以濟貧為要的慈善志業只是該會扶困泰北的第一階段,其他如醫療、文化及教育等志業,應該會在今後三年陸續出現當地。
三年之後呢?王端正說明,屆時該會將仔細評估,如果還有必要,他們會考慮留下來。慈濟功德會為民間機構,對泰北人的菩薩心腸已無處可議--濟助對象延伸至近年來與漢人大量通婚的泰北山區少數民族。
望著來自滿嘎拉村內各個小角落、穿上家中最隆重禮服的少數民族,每一位慈濟人都笑了,笑得比村民還燦爛。數位老婦執起小鑼,在擁擠的小學教室裡又跳又唱,答謝遠道之客蓋水泥房給她們全家住。雖然沒人聽得懂她們在說什麼、也沒人辨得出她們是哪一族,當婦人們愈唱愈起勁、甚至搶下慈濟帶來的麥克風繼續時,全體台灣人笑得更開心了。
另一座慈濟村--回賀現場,則讓台灣人溼濡眼睛。在章孝嚴乘直升機親臨主持啟用儀式、每戶頒發五百銖泰幣慰問金之後,村中少女盛裝粉墨登場,從山地民謠表演到「採茶歌」。當普通話的歌聲傳來,全場靜默,「她會唱我們的歌耶!」一位女士紅著眼眶輕聲說。
然而,在眾生歡喜落淚之餘,正如慈濟精神導師、也是台灣人道象徵的釋證嚴法師所言:「慈悲要有智慧。」回溯歷年台灣人在泰北累積數億元的慈善活動,到底給了孤軍及其後裔「釣竿」還是「魚」?
拿現況與六0年代相較,以多數捐款組成、救總主導進行的硬體建設直接施惠泰北難民村,說是天「降」甘霖並不誇張。十四年前搭直升機而來的救總泰北工作團團長龔承業說,當時連有幾個難民村都沒人搞得清楚。如今泰北難民村民隨手一指,都是台灣人鋪的路、造的橋。
在施與受之間
有些地區除了吃魚,現在釣竿也拿得穩。例如首富之鄉美斯樂,新訪客不會覺得它是「難民村」。沿著救總鋪設的柏油馬路望去,滿街都是商家旅館,略帶神秘色彩的軍事重鎮美斯樂,早已蛻變為泰國最熱門的觀光勝地之一,「櫻花滿山開的時候,停車位都找不到。」一位擺飲料攤的村婦形容。這些櫻花,也都是由救總帶著村民一株株種下,現在可換來了一銖銖泰幣。
關於如何「釣魚」,「荔枝」可以說明一切。一位慈濟委員曾在二十多年前造訪當地,那時候一顆荔枝都沒有,「現在村民拿來招待章委員長的自種荔枝,是又大又甜的「皇太后種」。」他仔細觀察。救總派駐在當地十年的農業輔導專家林阿田補充,現在經濟狀況稍好的家庭,多以種植高經濟價值作物為業,「桃子、李子、梅子和台灣烏龍茶,都是從前沒有的。」
然而,並不是每位泰北同胞都能分到「魚」或「釣竿」。窮怕了的昌龍村長眼巴巴地送走再度來訪的慈濟功德會,不擅言詞的他上一次也申請了住戶改建計畫,但是因為產權問題等因素而陰錯陽差,期待這回能不負村民眾望。斜對門死了丈夫、患了風濕的楊小四,現在只靠著弟弟偶爾送米過活,面對殷殷詢問她需求的慈濟師兄師姐,一時也答不上話來。
其實,最怕的是自己不想「拿釣竿」。「從前教他們種櫻花,他們還嫌不能吃呢!」一九四九年亦曾駐守泰緬邊境的龔承業說,許多退役官兵從槍桿子換拿鋤頭之後,觀念老是改不過來,免費的果樹種苗也沒人珍惜。後來領取種苗需付極低的工本費,村民才開始認真起來。
直到現在,還有些泰北同胞的確拿習慣了,一有困難就先開口,東西不新還不要,養成依賴心強的受方心態。有個村莊向台灣來的考察團開口要兩百萬泰銖補助經費,並決定將剛起步的農場承包出去,不再自行耕種。
反過來說,有些台灣人何嘗不是給習慣了?不少國人以撒錢模式對待泰北同胞,援助方式有時未能配合當地需求,強以台灣人的思維模式加諸泰北人,養成施恩心重的授方心態。
跑過泰北無數次的宇宙光送炭團團長林治平感慨:「凡是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他坦白,「最重要的是「我在」,是陪在當地人身邊的感覺。」該雜誌社所屬教會至今仍有宣教士派駐當地,也算是台灣「孤軍」了。
如今,慈濟人也願意來陪陪不分種族的泰北人。該會以濟貧為先的慈善志業正逐漸施展,無論如何,新一代泰北人和其父兄輩所面臨的問題不盡相同,如何能在「給魚」之外還「給釣竿」,在在考驗人類慈悲的智慧--光有好心腸不一定夠。
有人說,行善最大的收穫是施者自己。「送炭到泰北」的重點也許不在國人能幫泰北同胞什麼忙,而在他們改變了台灣人什麼心態。當台灣來的慈濟人也離開泰北的那一天,施與受之間其實沒有界線。
住慈濟屋的人
就在今年兩季之前.滿嘎拉村內全是無水無電的茅草房,雖然趕工的水泥屋已剪綵入昔,二十來歲的村民高忠ㄧㄡ(第三字他忘了怎麼寫)家裡,除了鍋碗瓢盆依然一片空蕩。不過,他和全家人仍小心翼翼地脫鞋入內,雖然雨下得讓室內室外都一樣泥濘不堪。
從前住緬甸的高先生,現在住的是泰北滿嘎拉村編號00一的慈濟屋。他在門牌邊貼上家中最搶張的裝飾品--春聯,用雲南話吆喝他那生產沒多久的傜族「婆娘」(妻子)和「小娃兒」們,快來和挨家挨戶頒發住屋證書及鑰匙的慈濟功德會師父照相。
提到慈濟「最大」的證嚴師父,高先生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樣向她說謝謝。提到明天,他望苦還在讀小學的長子高發明,靦腆地說:「希望他多讀點書,不要像他老子一樣以能種點包穀自己吃。」高發明正和弟弟們打開慈濟送的香港書包和日本文具盒。
「現在學中文,不像以前是完全免費。」高先生偶爾進帳的採茶工資,還算能勉強支付兒子的中文補習費,和自己二十銖泰幣一百支的紙菸錢。
一照完像,高先生馬上跑到屋後空地抽水菸,路過的慈濟委員們見上就勸「吸菸有礙健康」,高先生只是笑笑地望著她們,沒說什麼話。
高先生的固定軍收入是零,但他屬於泰北難民村區有工作能力者(五七%)的那一群。
(馬萱人)
蓋慈濟屋的人
小貨卡一段泥巴路、一段水泥路地彈彈跳跳往上爬.海拔約一千四百公尺高的明利村燈火遠遠在望,「這時候如果得會車,下坡的一定要讓往上衝的才行。」開車的明利村村長李開明堅決地說。
「到了!」他迅速跳下車,一邊搬貨一邊說,「這就是我開的小旅館,法國人來的最多。」帶著西部牛仔帽的李開明向來客介紹。慈濟功德會在今年初資助改建的滿嘎拉村,就是由他承包工程。
小旅館?數十幢觸間觸棟的渡假小木屋,實在不大像小旅館,也很難想像它的周圍仍是「難民村」。除了「老李小館」,李開明的名片上還印有海鷗茶廠和海鷗行銷公司等企業。
茶工廠就在村的另一頭,幾乎全村的人都是員工。曼谷有合夥人幫忙經銷茶葉,芳縣(在山下往清邁的半路上)的總茶行由太太掌管,沒印在名片上的卡拉OK則交小姨子經營。
「也許留在山上的人是傻瓜吧!」已經拿到泰國公民證的李開明自嘲。他一直留在山區發展,除了將九歲大的長女送至清邁住讀私立教會學校。
「這些得來一點也不僥倖。」李開明回億。當年他的父親離開游擊隊,帶著家人往山的最深處走,決意不開墾出一片天就不出來。這個決定,在那還有老虎出沒的時代卻苦了李家小孩,他們得走路或騎馬兩三天去美斯樂上中文學校,一學期才能回一次家。就連最需要的電力,也是直到今年四月間才接好,從前都是李家自己想法發電到十點。
望著一列列整齊的台灣種烏龍茶,李開明記得從前要採大野茶還得爬樹上下,然後用大象運下山來賣,現在只要輕輕鬆鬆放上貨卡就行了。四十來歲的他更年輕時曾專程到台灣楊梅學農,現在還開始承包工程,成績除了滿嘎拉村及「小旅館」,還包括他在芳縣興建的公寓和自住的數百坪別墅。
有些台灣人很好奇他如何起家,李開明覺得他只是看準時機、大膽去做;救總補助的部份硬體建設也幫了不少忙,「當然,父親早期打下的基礎也很重要。」他謙虛地說。不過,如果李開明只是守成,現在還有可能在那兒上上下下摘野茶。
最近,他忙著解決該村水泥路的問題,「到時候,歡迎台灣同胞到「老李小館」來玩!」李村長自信滿滿。
(馬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