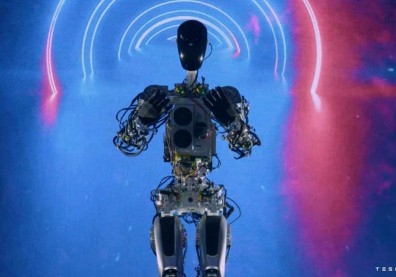他鄉遇故知
北國。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素有「北方雅典」之名,因其稟承與復興希臘啟蒙精神的緣故。但它也是世界最大的文化藝術節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Festivals)所在地,有藝術氣質,美術館琳琅,大部分免費向公眾開放。
最喜歡那裡的蘇格蘭當代美術館(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館子前身是所孤兒院,由蘇格蘭著名建築師威廉.伯恩(William Burn)設計(註一),位於流水潺潺的Dean Village,地方空曠,清朗有靈氣。周圍環繞骨董店、畫廊和咖啡館,足流連整天。
幾年前偶然走進那裡的一家法式餐廳,見到一種我在上海時慣稱「蝴蝶酥」的甜品;剛好想家,又驚又喜,面對店員語無倫次,索性給她一個帶著熱淚的擁抱。在我 ──和許多上海人──的認識中,蝴蝶酥是上海土產,是上海國際飯店的金牌點心,是酥鬆緊密的鄉愁,是層層細細的回憶。對方也驚訝:這是典型的法國甜品,為什麼會被一個中國女孩認為是她故鄉的特色?
這則資訊猶如青天霹靂,一時仍不承認蝴蝶酥居然不是上海本土貨、至少是上海人在租界時期改良某種法式甜點而來。但回去網上一查,果然,原版的法國蝴蝶酥(palmier)就是我記憶中的樣子,上海人並沒有進行多大改良,更別說是發明。悵然失落。
全球化的今天,在東方吃到法國甜品並不稀奇;稀奇的是把它認作自家特產。雖然知道它的名字應該是palmier,我依然稱它為蝴蝶酥。
後來在英國的那幾年,凡是見到麵包店有蝴蝶酥,總會叫一份。有不少甜品店都做得出色,比如法國傳奇大廚布朗克(Raymond Blanc)在牛津開設的咖啡館Maison Blanc;但在我心中,我記憶中上海國際飯店的蝴蝶酥始終獨占鰲頭,無可替代,哪怕我已經忘了它現實中的滋味。
蝴蝶酥的關鍵詞
palmier是法語「棕櫚樹」的意思,因為它兩頭捲曲舒展的樣子,像棕櫚樹末端樹冠打開的形狀。儘管有個法文名字,許多人認為它發明於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認識蝴蝶酥,可以從以下幾個關鍵詞入手:
關鍵詞之一:千層麵團(Laminated dough)
蝴蝶酥由多層酥皮(filo)壓緊多層黃油烘烤,刷上焦糖,點綴白糖,濃郁香甜,有緊緻而酥脆的特別口感。這種多層壓緊的麵團叫laminated dough,有些可以包括八十層之多。麵團開始只用麵粉和水混合,塗上黃油後用麵團刮刀(pastry scraper)摺疊、再用擀麵杖(rolling pin)擀得扁平,再摺疊,重複多次。在千層酥皮上刷一層清水,待酥皮表面產生黏性後撒粗粒白砂糖。沿著長邊,將千層酥皮從兩邊向中心線捲起來,切成厚度為半公分左右的小片,排入烤盤。烘烤時麵團中的水分受高溫迅速蒸發,在麵層壓力下形成酥脆的層次。可頌麵包、丹麥卷等酥皮點心使用這種千層麵團,只是製作方法稍有不同,譬如蝴蝶酥不發酵,因此與可頌蓬鬆的口感不同。它的緊緻好像是香甜的任性。
關鍵詞之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雖然誕生在歐洲,也總是與法式烘焙聯繫在一起,但這種酥皮點心的源頭其實與阿拉伯文化有關。與其相似的中東酥皮點心有baklava,源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由酥皮、果仁、蜜糖製成,小巧香甜,中文常譯作果仁酥、果仁蜜餅等。這種點心的關鍵用料也是千層酥皮,其製法也源自土耳其。在中世紀的土耳其牧民中,多層麵包(當時被稱為tutmac)是常見的主食,一說是因為免於發酵而省了時間,又能捲起來攜帶,適應游牧生活。十一世紀的突厥語中曾記錄yuygha這個詞,指摺疊層次的麵包,在現代土耳其語中yufka一詞相連,意為「單層文件」。在中亞,這類千層酥甜品層出不窮,譬如阿塞拜疆就有一種叫Baki pakhlavasi的甜品,用上五十層左右的酥皮。
據說這種酥皮實發明於如今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匹皇宮(Topkapı Palace)的御用廚房內。相傳蘇丹親兵(Janissaries)(註二)在伊斯坦堡駐紮時也曾排隊討要baklava,然後再行軍,而他們行軍的列隊也被稱為果仁酥列隊(baklava psrocession)。每到開齋節領軍餉的時候,皇宮也會向蘇丹親兵分發這種果仁酥。
關鍵詞之三:摩爾人
那麼,這種傳奇的中東甜品是怎麼被帶到歐洲的呢?中世紀早期,來自北非的穆斯林擴張至歐洲的時候將他們的甜品帶到了伊比利半島。《牛津糖果甜食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Sugar and Sweets)記錄到,摩爾人於八世紀起占領西班牙和九世紀占領西西里時,將穆斯林世界對甜味的喜好帶到了歐洲(包括甘蔗)。十三世紀的一位無名摩爾廚師留下一則食譜,其中記載了酥皮的製法,用的是阿拉伯名字muwarraqa以及西班牙文folyatil,兩者都是葉片狀的意思。也就是說,在歐洲流行的酥皮點心共通基督教歐洲和穆斯林文化的淵源。
另一方面,一四三三年勃艮地間諜及朝聖者貝特朗東(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 1400-1459)在土耳其南部的山中受到禮遇,對方提供給他的食物中就包括優酪乳、乳酪、葡萄和千層酥。他們製作千層之神速令貝特朗東咋舌,他說道:「他們做兩枚『蛋糕』的速度比我們的華夫餅師傅攤一枚華夫餅都快。」
儘管許多記載中都對蝴蝶酥的源頭不由一是,但因為現代法國的千層酥甜品(pâte feuilletée)出名(比如填滿奶油的拿破崙〔mille-feuille〕),蝴蝶酥被認為是源自法國的甜品也不足為奇。這段酥皮的香甜歷史,提醒我們歷史的全球性:哪怕今天看似在意識形態上正逢相對的兩種文化,也曾經交融貫通,甚至留下甜蜜的註腳。
註一:威廉.伯恩曾師從大英博物館的設計師羅伯特.斯默克爵士(Sir Robert Smirke);在他的設計下,現代美術館呈新古典主義風格。
註二:蘇丹親兵,又稱耶尼切里軍團、土耳其禁衛軍等,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常備軍隊與蘇丹侍衛的統稱,繼羅馬帝國滅亡後在該地區建立的第一支正式常備軍。士兵選自被征服的巴爾幹斯拉夫人,使其改信伊斯蘭教並學習土耳其語。到了塞利姆二世時代,幾乎成為定制,職位傳子,紀律敗壞。到了穆拉德三世時代,為了慶祝王子的割禮,人人皆可參軍,至此完全喪失戰鬥力,在一六八三年穆罕默德四世時期允許土耳其突厥穆斯林也可參軍。到十九世紀,由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在一八二六年發動兵變廢棄此制度。

本文節錄自:《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一書,胡川安、郭婷、郭忠豪著,聯經出版。